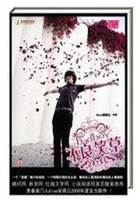“错为君,误此生,付鸩酒”,或许这就是你一生的“缘”。
误入凡尘,秋日的傍晚,金色的余晖洒下来,摇曳的梧桐,沉静的金井,笼在其中。白天的细雨,丝丝的愁绪融在了秋的寒意里。的确,人间有亲情,但无论自己对情谊寄予了多大的希望,水中游动的锦鳞总是知道“九曲寒波不溯流”,有些事是无可挽回的,哀叹天不如人愿又有何用?
或许,你只是仙界美丽的星辰,陨落人间,深陷尘网,到了你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你不该做的事业,误此一生。
毕竟,一片落叶是无法决定自己将飘向何处的……
吴国天祚二年,春风拂过江南大地,满树的杨花随风飘舞零落,如白雪一般纷纷扬扬,飘逸柔美。连绵的春雨滋润着枝头,粉红的花瓣在雨中绽开,染满了整株李树,幽幽芳香散入雨中,朵朵李花融在雨里,点染出一幅烟雨朦胧的山水画卷。
在这生机盎然的季节里,一个四十五六岁左右的清俊男子站在院中,看着满院开得正盛的李花出神。一名婢女前来禀告“大人,周大人来访。”看花那人回过神来,说道:“周大人来了,还不快快有请。”那婢女应了一声,便去迎客。不过多时,便听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一边走过来,一边问道:“徐大人,从这李花中看出什么门道吗?”看花那人忙笑道:“周大人光临,当真是有失远迎了,快请屋里坐吧。”说完拉着那来访的男子走进厅中,吩咐下人沏来茶水。
原来那看花的徐大人,名徐知诰,任尚父、太师、大丞相、天下兵马大元帅,进封齐王,以、润等十州之地为齐国,是当时吴国权倾朝野的高官。而来访的周大人,名周宗,是徐知诰的心腹官员。
徐知诰请周宗在厅中坐下,便听周宗问道:“徐大人好雅兴啊,竟有闲情在院中赏花。却不知是否看出什么问题来?”徐知诰笑道:“哪里哪里,不过闲来无事随便看看罢了,怎会看出什么问题?”周宗笑道:“是么?我却觉得今年这花有几分奇怪。”徐知诰笑道:“哦?不妨说来听听。”周宗道:“现下春意正浓,而杨花却在此时纷纷凋落,只有那李花仍开放正盛。”
徐知诰听了这话脸色微变,他心里明白:吴国现任皇帝正是姓这“杨花”的“杨”字,而“徐”字不过是养父的姓,自己本应姓李。但徐知诰脸上却不动声色,说道:“那又如何?”周宗见他还在卖关子,压低声音说道:“现在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江北杨花作雪飞,江南李树玉团枝。李花结子可怜在,不似杨花无了期。’难道其中之意还要我解释么?”徐知诰摇了摇头,说道:“大人的意思我自然明白,只是……”沉吟半晌,又道:“这事我心里有数。”
周宗当然明白他的言下之意。其实,徐知诰的长孙名李弘冀,正是由“有一真人在冀川,开口持弓向外边。”这句话而来,冀即指冀川,弘则是左边一个弓字,右边是一个没有封闭的口字。其中的含义自是不言而喻。周宗笑道:“徐大人,即是如此,那在下告辞了。”徐知诰也微笑相答,道:“周大人走好。”说完又吩咐下人送客。
天祚三年正月,徐知诰建齐国,立宗庙、社稷,改金陵府为江宁府,牙城称宫城,厅堂称殿,百官多如天子之制,设骑兵八军,步兵九军,其制度如国中之国。
二月吴正式册封徐知诰为齐国王。
三月,徐知诰为与养父徐温诸子相区别,改名徐诰。
事情进展还算顺利,可是徐诰心里明白,自己这么多年来勤于政务,体恤臣民,虽深得群臣支持、百姓爱戴,但改朝换代毕竟是一件大事,自己也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如何名正言顺的昭告天下?如何使四境臣民心服口服?都还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夜晚,徐诰靠在桌边细细思索着,心中也有几分犹豫了,不知该不该为这已经到手的大权再冒一次险。想着想着,竟伏在桌上睡着了。
睡梦中,一座座宫阙如梦幻般美丽,灿然生辉的金色发出耀眼的光彩,而自己身着龙袍,那无尽的灿烂吸引着自己,一步步朝那象征着最高权力的金殿走去。哪知正当他要跨入顺天门时,脚下一个踉跄,竟然摔倒在地,金色的光辉更加刺眼,几乎要化作一片空白。忽然,眼前强光一闪,自己不由微微闭了一下眼,再一睁眼,眼前的一切都骤然消失。
徐诰惊得醒了过来,手足无措间竟将桌上茶碗打落在地。茶水洒落在地,滚动的水珠里,反射出来刺眼的阳光,似乎还能映出梦中那可怕的情景。徐诰惊魂未定,心道:难道是上天在警告我不可贪权忘本?我若再一意孤行,岂非要落得个身败名裂?不由越想越是心惊,盯着地上的茶水,怔怔出神,冷汗直冒。
正在这时,一名婢女闻声赶来,问道:“大人,怎么了?”徐诰这才惊觉,稍稍平静,道:“没什么,不过是不小心打翻了茶碗。”那婢女问道:“大人,要不要准备早膳?”徐诰这才意识到,天色已经大明,可是现在他哪里有心情吃早饭,便道:“不必了,备车,寡人要去一趟周府。”那婢女应道:“是。”说完退出殿去。
徐诰来到周宗府邸,周宗也是刚刚起床,见到徐诰,一惊,问道:“徐大人怎么亲自光临啊?”徐诰沉着脸,道:“周大人,我有要事想与你商谈。”周宗见他神色有异,知必有要事,忙请他到客厅。
徐诰在厅中坐下,周宗吩咐下人们守在门外,不得打扰。徐诰这才说道:“周大人,你觉得我们的计划是不是有些不稳妥啊?”周宗不解,奇道:“怎么讲?”徐诰道:“我总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周宗道:“怎么会呢?如今杨花凋零,李花盛开,正是上天的指示。”徐诰道:“话是这样说,可是我昨晚却做了一个不祥之梦。”周宗笑道:“哦,是么?但依我看来梦祥与不祥全在解梦之人如何解了。徐大人不妨说出来,我来帮你解解。”
当下,徐诰便将昨晚的梦讲给了周宗。周宗听罢,哈哈大笑,说道:“徐大人,这是吉兆啊。”徐诰一怔,问道:“怎么讲?”周宗道:“大人在顺天门前摔倒,正是因为有人要将你扶起,并辅佐你更进一步啊。”徐诰其实心里也明白,周宗这样解梦无非是想坚定自己夺取大权的信心,听来难免有几分牵强。
周宗见徐诰面露不以为然之色,说道:“大人觉得我解得如何?”徐诰摇了摇头,道:“有些牵强。”周宗见状,担心徐诰有所动摇,问道:“那大人以为如何?难道为了一个梦,就放弃么?”周宗的话正好问到徐诰心中所想。其实徐诰也并非平庸之辈,在去周府的途中,心情已经平静下来,再回想昨晚情景,也不过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罢了,没有必要如此惶恐。再加周宗一句提点,更是直切要害,分明是提点出这不是可以犹豫的事,如果犹豫就只有放弃这一条路,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徐诰沉吟半晌,说道:“周大人的话当然在理,不过是一个梦而已,如何想便可以如何解。”周宗听了,放下心来,说道:“既然如此,大人又何必有此一问?”徐诰不答,周宗继续道:“如今,进则君临天下,退则功败垂成。”徐诰微微颔首,沉声道:“今吴气数已尽,四境之内皆归服于寡人,若能身登九五,自是造福百姓,天下归心;若仍举棋不定,必会天下动荡,殃及百姓。改朝换代,非不忠也,是救民兴邦也。”
周宗听了,拍手赞道:“好,好。大人既能这样想,下官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接着又将手搭在徐诰肩上,说道:“你看这杨花凋谢,李花烂漫,不正是此意么?”徐诰也暗下决心:寡人若登基,必要使江南如这李花般繁盛不衰,使百姓如这李花般安享春色。徐诰接着对周宗道:“我不欲兴兵祸,现下时机未到。”周宗躬身道:“下官惟命是从。”徐诰不再多言,只道:“今日之事只你知我知。”周宗道:“这个自然。”徐诰微笑点头,转身离去。
徐诰回到府中,一个在院中练剑的少年,见到徐诰,忙跑过来,说道:“爷爷,你再指点孙儿几招剑术吧。”这个少年正是徐诰的长孙,李景通的长子李弘冀,今年已经十二岁了。徐诰笑道:“你的剑法不是很好了么?”李弘冀听到赞赏,心下甚喜,道:“可是二弟的武功进展也很快啊,我可不想他超过我。”李弘冀口中的二弟,是李景通的次子,名李弘茂,比李弘冀小两岁。
徐诰听了这话微感不悦,说道:“弘茂天资聪慧,文武双修,你应当向他学习才是。”李弘冀听了,不满意地撇撇嘴,道:“现在是乱世,自当习武平定天下,为何总在故纸堆里找理论。”徐诰笑道:“习武平定天下?你的志向还不小啊!”李弘冀听了这话更加自豪,道:“孙儿要辅佐爷爷,创建千秋霸业。”徐诰笑道:“你现在还小。须知可以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天下?以武固能取胜,但以德才能服人。”
李弘冀不再言语,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总有一个建功立业梦,他想名留青史。但是他也知道,爷爷是权臣不是帝王,这个梦或许会给家人带来麻烦,他只得将梦深埋心底,并为之暗暗努力。因而他自幼沉默寡言,家人只认为他冷淡刚严,对他的关心也就不自觉地少了几分,而李弘冀,却因家人的遗忘,更加明确自己想要什么。
徐诰看着李弘冀沉思时,眼中流露出欲望。其实随着李弘冀年龄的增长,徐诰早已隐隐察觉到了这种野心,心下既有几分赞赏,又有几分不以为然。当下,徐诰只是微微摇了摇头,轻轻叹息一声,转身离去。李弘冀望着徐诰离去的背影,握紧了拳头。
天祚三年八月,吴主杨溥终于下诏禅位于徐诰。
十月,徐诰即位称帝,以金陵为都,所辖疆域达三十五州之大。并恢复姓李,改名李,改元昇元,并自认是唐太宗之子李恪的后人,因而改国号为“唐”。又追尊其养父徐温为武皇帝,庙号义祖,立其长子李景通为太子,李景通之妻钟氏为太子妃,封李弘冀为东平郡公,李弘茂为乐安郡公。
李出生民间,又曾从军作战,深知百姓疾苦,登基之后,更是勤政爱民,轻徭减赋;修好邻国,少兴战事,是以百姓安居,生活富庶,国力强盛,成为当时最为繁华昌盛的大国。
正在唐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之时,又有奇幻而令人欣喜之事降临。
昇元五年的七夕之夜,一弯新月挂在天空,璨璨的明星映照着深蓝的天幕,丝带般的轻云,在星月间飘舞,如鹊鸟所搭的天桥横亘银河。这奇美的夜色,似乎预示着要有什么好事发生。李正在宫中仰望天际,感叹道:“今年的七夕美得奇幻啊。”
正在这时,一个宫婢满脸喜气,向李跪拜行礼,道:“皇上,大喜啊!太子妃又生了个皇孙。而且大家都说小皇孙相貌奇异,一定不凡。”这虽已是李的第六个孙子了,但其余诸子除弘冀、弘茂外都不幸早亡,因而李听了这个消息,自是喜不自胜,心道:今日这如此美好的夜空不正是预示此事么?在心中便对这个刚降生的皇孙,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忙问:“怎么个奇异法?”那宫婢道:“奴婢也不知道。”李道:“好,快带朕去瞧瞧。”那宫婢应道:“是。”站起身来,在前引路。
李跟那宫婢走进太子宫,太子李景通正在院中等候李,见他亲来忙上前行礼:“儿臣参见父皇。”李笑道:“皇儿免礼,太子妃还好吧?”李景通道:“母子平安,多谢父皇关心。”李道:“跟朕去看看太子妃和小皇孙吧。”李景通道:“是。”说完跟在李身后走进太子妃钟氏的房中。
钟氏欲从床上坐起,李忙道:“太子妃不必多礼,好好休息吧。”钟氏听罢,无力地躺在床上。这时一个宫婢抱起床边的小皇孙,道:“官家,您看小皇孙多可爱啊。”李走近,却见小皇孙生的清秀可爱,甚是惹人喜爱。再一细看更觉惊奇,只见他一只澄澈的眼眸中竟有两个瞳仁,显得甚是深邃灵动。李大喜,笑道:“这大概就是史书上说的重瞳吧。这可是难得的帝王之相,皇儿你可真有福气啊。”李景通大惊,心道:我现在也不过是一个太子,而小皇孙不过是我的第六子,这样说实在不妥。忙道:“父皇年富力强,一个刚刚降生的皇子那里是什么帝王之相!”李心下甚喜,自己也不知为何对这个小皇孙说不出的喜爱,竟丝毫不以为意,笑道:“大舜和项羽皆有此貌,如何不是帝王之相?皇儿无需太过谨慎,咱们都是皇室,何必这样忌讳?”李景通不敢再说,不再接话。
而正在他们说话间,皇孙李弘冀和李弘茂正站在门口窥视。李弘冀听了李的话不由得心怦怦乱跳,他知道自己离多年的梦越来越近了,而这个皇孙的传奇降生,可能会彻底打破他的梦。想到这,深深的恨意已埋在心中。李弘茂站在他身侧,感到他的身子在颤抖,也是心惊,生怕他什么也不顾冲进屋去,便伸手拉住了他的手臂。李弘冀却用力甩开李弘茂,拂袖而去,只留李弘茂一人怔怔站在屋外。
房中,李仍是抱着六皇孙谈笑。钟氏看出李对皇孙的喜爱,笑道:“父皇既然这样喜欢皇孙就给他起个名字吧。”李道:“嗯,朕看如今国泰民安,又逢佳节,不如就起名‘从嘉’;此子生于七夕,必能光辉万重,照耀人间,且有一目重瞳子,便取字‘重光’吧。”李景通听李如此称赞皇孙,知他万分喜悦,而自己也是心下甚喜,笑道:“这个名字好。事事从意,嘉运连连。儿臣代重光谢父皇赐名。”李笑道:“朕正是此意。”接着又看了看小皇孙,心里因一种说不出的喜爱而隐隐感到几分不安,于是叹道:“这个孩子出生竟这样传奇,不但生于七夕而且还有着一目重瞳的奇貌,却不知是福是祸啊。”钟氏和李景通也均惊叹此事奇异,暗自摇头。
明星闪耀,月辉映夜,又是一个浪漫的七夕夜。这日宫里都在欢天喜地的宴饮,庆祝从嘉周岁。
按照礼仪从嘉周岁的时候,应该举行抓周,来估测他将来志向。于是,晚宴上,李摆了些物品,供从嘉抓取。而这物品中竟有一个赫然便是唐国国玺。李景通见状,起身劝道:“父皇,儿臣知您疼爱重光,只是……只是……”李却不以为然,不等他说完,便笑道:“皇儿无需在意,只是抓周仪式罢了,作不得真的。况且又不知重光便会取了此物,何必太过在意?”李景通见劝说无效,也就不再多言,叹了口气坐回席中。
而坐在李景通身边的李弘冀却暗自握紧了拳头,注视着国玺。他见家里所有人都对这个一目重瞳子的弟弟万分疼爱,而自己却似乎更显得被遗忘了,嫉妒和厌恶深深地埋在了心里,见到今日情景,心下恼怒之意更胜。
仪式开始,大家都关注着从嘉要取何物。却见从嘉稚嫩的小手试探地伸了出来,犹犹豫豫间,竟真的触到了身旁那个众人瞩目的物饰——国玺。在场所有人都大惊,李弘冀手中的茶杯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只是当时人们都看着从嘉,谁都没有在意。李景通站起身来,颤声道:“父皇,这……这……”心中又惊又惧,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李知他惶恐,却哈哈大笑,道:“皇儿不必紧张,这正合朕意。你现在是一国储君,难道重光的举动不是个好兆头么?”李景通听了更惧,又惊叹于父皇竟对一个刚出生一年的皇孙从嘉如此的疼爱,道:“父皇,对重光太过溺爱,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李却笑道:“无妨,无妨。”
就在大家惊异之时,却见从嘉将国玺把玩一阵之后,就放回席上,拿起了身旁的一支笔端详。李景通轻轻舒了口气,而李弘冀却仍狠狠地盯着从嘉。李先是一怔,似乎甚是失望,但随即笑道:“看来重光亦好诗赋之道,想来将来必有造诣。”转头对李景通笑道:“皇儿,重光跟你倒是同道中人啊。你要好好指点他啊!”李景通应道:“儿臣遵旨。”李又吩咐道:“来人,传召,封六皇孙为安定郡王。”李景通更是大惊,一个刚满周岁的皇孙竟被封为郡王,这在南唐时是前所未有的,更见李对从嘉的喜爱之甚。李弘冀更是嫉妒,站起身来,对李道:“皇上,臣忽感不适,先行告退,还请见谅。”说完转身离去。李何等聪明,当然知他心思,只是心下甚喜,也并未在意。
宴会散后,众朝臣皇室都在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各怀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