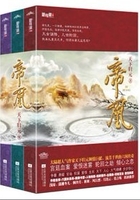流浪水
孩子跟随老师到海边去,回来后用了一夜的时间,告诉我海边的事。
他们到海边后去看海、吃鱼丸、坐渡轮,他说:“渡轮上有一个像电扇一样旋转的东西,一直噗噗噗打着海水,海水被打到后面去,渡轮只好前进了。”
他说:“老师叫我们蹲着,伸手去摸海水,海水好冰喔,比我们家水龙头的水还冰。”他说:“海好大好大,有好多的鱼、虾、螃蟹都可以在里面生活,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游遍整个海,因为太大了嘛!对不对?”…… 我问孩子:“那么,你对海,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
他说:“是流浪水。”
“流浪水?”
“是呀!流浪水就是一下子打到海边上又退回去,隔一下子又打到海边上的那种水。许多鱼呀虾呀都跟着流浪水,流上来呀,又流下去。它们一生下来就在流浪水里,长大了在流浪水里,最后死了也在流浪水里。老师说,有很多鱼虾长在海底,那里的水不是流来流去,很可能它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生在流浪水里……”
我对孩子说:“那不叫流浪水,那是海浪。”
“流浪水不就是海浪吗?”孩子用天真的眼睛看着我。
“对,流浪水就是海浪。”我说。
孩子才安心地去睡觉了。
深夜里,我思考着孩子的话,所有的海中动物是生长在流浪水里,它们一生都在海里流浪着,当然从来没有一只海中的动物可以游遍整个海。有很多深海里的动物,从来不知道海是一波一波地流浪着,然后它们在无波的深海里,平静地死去。
流浪水是多么美丽的海之印象呀!
海的动物是生活在流浪水里,我们陆上的众生何尝不是生活在流浪水里呢?我们的流浪水是时间,一个白天一个黑夜规律地循环,不正如打在岸上又退去的流浪水吗?从小的角度看,当然每个白天和黑夜都不同,可是从大的观点看,白天黑夜不正是我们看海浪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吗?
可叹的是,很少有人警觉到时间的流浪水,他们就会在没有观照的景况下度过一生。
警觉到时间的流浪水仍然不够,其实每一个人有了觉醒之后,心性就会像大海一样,看着潮涨潮落,知悉心海的浪循环之周期,这些海浪再汹涌,在海底最深的地方,是宁静而安适的。因为深刻地观照了流浪,便不会被流浪水所转,不会在拍岸时欢喜,也不会在退落时悲哀,胸怀广大,涵容了整个大海。
自性心水的流露正像这样,因此在生命中觉悟而进入深海里的人,与从来不知道流浪水的人是不一样的,前者无惧于生死的流浪,后者则对生死流浪因无知而恐惧,或者因愚昧而纵情欢乐。
生命的化妆
我认识一位化妆师,她是真正懂得化妆,而又以化妆闻名的。
对于这生活在与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使我增添了几分好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化妆再有学问,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
因此,我忍不住问她:“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
对于这样的问题,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她说:“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化妆术,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次级的化妆是把人突显出来,让她醒目,引起众人的注意。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她化了很浓的妆,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最坏的一种化妆,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又失去了五官的谐调,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
没想到,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竟是自然,这可使我刮目相看了。
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继续说:“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吸引了人的视线,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最好的文章,是作家自然的流露,他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而是在读一个生命。”
多么有智慧的人呀!可是,“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呀!”我感叹地说。
“不对的,”化妆师说,“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睡眠充足、注意运动与营养,这样她的皮肤改善、精神充足,比化妆有效得多。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多读书、多欣赏艺术、多思考、对生活乐观、对生命有信心、心地善良、关怀别人、自爱而有尊严,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
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这样,你懂化妆了吗?”
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深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
告别了化妆师,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表,有了这样深刻的体悟:这个世界一切的表相都不是独立自存的,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相最好的方法,不是在表相下工夫,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
可惜,在表相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
横过十字街口
黄昏走到了尾端,光明正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自大地撤离,我坐在车里等红绿灯,希望能在黑夜来临前赶回家。
在匆忙地通过斑马线的人群里,我们通常不会去注意行人的姿势,更不用说能看见行人的脸了,我们只是想着,如何在绿灯亮起时,从人群前面呼啸过去。
就在行人的绿灯闪动,黄灯即将亮起的一刻,从斑马线的开头出现了一个特别的人影,打破了一整个匆忙的画面。那是一个中年的极为苍白细瘦的妇人,她得了什么病我并不知道,但那种病偶尔我们会在街角的某一处见到,就是全身关节全部扭曲,脸部五官通通变形,而不管走路或停止的时候,全身都在甩动的那一种病。
那个妇人的不同是,她病得更重,她全身扭成很多褶,就好像我们把一张硬纸揉皱丢在垃圾桶,捡起来再拉平的那个样子。她抖得非常厉害,如同冬天里在冰冷的水塘捞起来的猫抽动着全身。
当她走起来的时候,我的眼泪不能自已地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落泪,但我宁可在眼前的这个妇人不要走路,她每走一步就往不同的方向倾倒过去,很像要一头栽到地上,而又勉力地抖动绞扭着站起,再往另一边倾倒过去,她全身的每一根骨头、每一条筋肉都不能平安地留在应该在的地方,而她的每一举步之艰难,就仿佛她的全身都要碎裂在人行道上。她走的每一步,都使我的心全部碎裂又重新组合,我从来没有在一个陌生人的身上,体验过那种重大的无可比拟的心酸。
那妇人,她的手上还努力地抓住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条老狗的颈上,狗比她还瘦,每一根肋骨都从松扁的肚皮上凸了出来,而狗的右后脚折断了,吊在腿上,狗走的时候,那条断脚悬在虚空中摇晃。但狗非常安静有耐心地跟着主人,缓缓移动,这是多么令人惊吓的景象,仿佛把全世界的酸楚与苦痛都在一刹那间,凝聚在病妇与跛狗的身上。
他们一步步踩着我的心走过,我闭起眼睛,也不能阻住从身上每一处血脉所涌出的泪。
我这条路上的绿灯亮了,但没有一个驾驶人启动车子,甚至没有人按喇叭,这是极少有的景况,在沉寂里,我听见了虚空无数的叹息与悲悯,我相信面对这幅景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忍心按下喇叭。
妇人和狗的路上红灯亮了,使她显得更加惊慌,她更着急地想横越马路,但她的着急只能从她的艰难和急切的抖动中看出来,因为不管她多么努力,她的速度也没有增加。从她的脸上也看不出什么,因为她的五官没有一个在正确的位置上,她一着急,口水竟从嘴角涎落了下来。
我们足足等了一个新的红绿灯,直到她跨上对街的红砖道,才有人踩下油门,继续奔赴到目的地去,一时之间,众车怒吼,呼啸通过。这巨大的响声,使我想起刚刚那一刻,在和平西路的这一个路口,世界是全然静寂无声的,人心的喧闹在当时当地,被苦难的景象压迫到一个无法动弹的角落。
我刚过那个路口不久,天色就整个黯淡下来,阳光已飘忽到不可知的所在,回到家,我脸上的泪痕还未完全干去。坐在饭桌前面,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心里全是一个人牵着一条狗从路口一步一步,倾斜颠踬地走过。
这个世界的苦难,总是不时地从我们四周跑出来,我们意识到苦难,却反而感知了自己的渺小、感知了自己的无力,我们心心念念想着,要拯救这个世界的心灵,要使人心和平清净,希望众生都能从苦痛的深渊超拔出来,走向光明与幸福,然而,面对着这样瘦小变形的妇人与她的老弱跛足的狗时,我们能做什么呢?世界能为她做什么呢?
我感觉,在无边的黑暗里,我们只是寻索着一点点光明,如果我们不紧紧踩着光明前进,马上就会被黑暗淹没。我想起《楞严经》里的一段,佛陀问他的弟子阿难:“眼盲的人和明眼的人处在黑暗里,有什么不同呢?”
阿难说:“没有什么不同。”
佛陀说:“不同,眼盲的人在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但明眼的人在黑暗里看见了黑暗,他看见光明或黑暗都是看见,他的能见之性并没有减损。”
我看见了,但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帮不上一点黑暗的忙,这是使我落泪的原因。
夜里,我一点也不能进入定境,好像自己正扭动颤抖地横过十字街口,心潮澎湃难以静止,我没有再落泪,泪在全身的血脉中奔流。
百年与十分钟
在日本东京的银座街头,有好几家卖古董照相机的店,那些古董相机的性能都还非常好,外表经过整修也和新的一样。
卖古董相机的店员都会对人保证,那相机可以拍出和现代相机效果相当的作品。
“但是,”有一位店员这样说,“要注意这些保存了一百多年的相机,它的曝光时间就要十分钟,现代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静止十分钟让人拍照,只有拿来拍风景和静物了。”
店员说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买了一架古董相机,试图用那部相机帮人拍照。他要拍人之前,就告诉那个被拍的人说:“这是一百年前的照相机,曝光就要十分钟,你可以十分钟坐着不动吗?”每一个被拍的人都拍胸脯对他保证:“没问题,一百年前的人不都是这样拍照的吗?”可叹的是,他拍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坐着十分钟不动。
最后,拍照的人气了,心想:“难道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坐着十分钟不动吗?为什么古代看成是最自然的事,现在没有人能做到呢?”他找到一个朋友帮他按快门,他自己接受拍照,结果连他自己也不能面对镜头静坐十分钟。
他只好把相机还给卖古董相机的老板。
店员指着橱窗说:“他退回的照相机就是那一部,要买回去试试吗?”他对每个人都这样说,可是那部相机再没有卖出过,因为每一个现代人都深知,在生活的周围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十分钟坐着不动的人。
这个故事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古代人和现代人对时间的观念是大不相同的,古人一天可能很专注地做一件事情,现代人一天却要做几十件事;古人坐个十分钟是绝对没问题的,现代人却很少有耐心能坐十分钟。拍过照的人都知道,叫一个现代人八分之一秒不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十分钟的价值与意义,经过一百年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也使我们知道为什么在现代修习禅定不容易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在体质里,已经失去了深沉、长恒、有耐心的特性。
对于某些盲目地忙着,忙到没有时间痛哭一场的现代人,恐怕很难想象,古人拍一张照片要曝光十分钟,现在,到大规模的快速冲洗店,十卷底片全部洗好,也只要十分钟的时间呢!
戴勋章逛街的人
在街上遇到一个奇特的人,他戴着一顶黑帽子,帽檐上都是勋章。
他身穿一套藏青色的中山装,熨烫得非常齐整,他的胸前左右都挂满了勋章。
但他的腿断了一肢,裤管处打了一个结,他撑着支架,一步步走得很慢,即使是那样慢,我们也可以明确知道他曾是个极有威仪的人,从他的帽子、衣服,一直到只有一只也擦得雪亮的皮鞋,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威严。
这曾是一位指挥着大军的将军吧!我心里想着,因为具有如此威猛壮肃的精神者,在街上我们是很少见到的。
靠近一看,他的勋章真是美,绝对不是普通的单薄纪念章,而是厚实的、精致的,如同我们在电影上看见将军所垂挂的一般,有星星的光泽,掉在地上必然会发出金属一样响脆的声音。那时候他站在百货公司贩卖宝石的橱窗前面,我正站在橱窗的这边,隔着晶亮的玻璃,正视着他。他的勋章,比橱窗里的宝石更引人注目。
我忍不住脱帽向他致意,他露出和煦的微笑,然后我们在人潮里错身而过,没有任何交谈。回到家里,我心里老是惦记这位戴着勋章逛街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要戴着明亮的勋章在人群里行走呢?他的勋章怎么来的?他的腿又是如何失去的?
我找不到任何答案。
隔了一个多月,我又在仁爱路的红砖道上看见他,从背影,我就认出了那在百货公司曾与我见过一面的人,我跟着他的背影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直到在复兴南路等红灯时,我们才并肩站在一起。
“先生,您好。”我说。
没想到这位胸前仍然挂满勋章的人说:“呀!我们在百货公司曾见过一面。”然后他礼貌地伸手与我相握,他的手非常有力而温暖。
“您的勋章真是美!”我说。
他很高兴地笑了,说:“难得有人看见我的勋章。”
我们就一边散步,一边谈起一排排勋章的故事,与我想象的非常接近,他果然是身经百战的军人,胸前的每一枚勋章都是在烽火中的奖赏。唯一与我的推测不同的是,他并非将军,只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他胸前最后的一枚勋章,是失去他的左腿而获得的。
为什么每天戴满勋章到街上来呢?
他说:“这是有点疯狂的行为,不过,像我这样的人,年纪又大,又断了左腿,一般人对我都不会太礼貌,有一次我试着戴勋章出来,才得到了一些尊重,遭到的白眼比较少了。”他以一种极严肃的口气说:“其实,我的左腿才是我最大的勋章,但是一般人总是最轻视它。”
当我们在下一个路口分手的时候,我特别感叹,通常最大的勋章是最难被看见的,何况是没有戴出来的,放在心里的勋章呢?
我虽然从不戴勋章出门,我也没有任何勋章,不过,我总是把每一个人都当成是有勋章的人,如果不能怀抱着敬重的心,不只看不到别人的勋章,自己的勋章也会失去。
即使是最平凡的母亲带着孩子,我也看见母亲的勋章是无尽的爱,而孩子的勋章是毫不矫饰的天真,那时我感觉自己,也可以把那母亲的爱与孩子的天真,佩在我空白的胸前。
天地间最美丽的勋章不是别的,正是对一切都抱着尊重与包容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