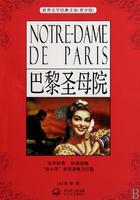六点钟的太阳依然炙热,白色的连衣裙在行驶中飘扬。车流人流如梭来往,路面蒸腾的热气扑面而来。殷都桥下的柳青河波光粼粼,沿河公园到处是乘凉的老人孩子。人流如潮让我不得不放慢速度。一个沙哑的男人声音传过来:小钟你好,这是去哪里?我一看,是那个让我下决心离开殷都晚报的人称黄鼠狼的记者部副主任黄书良。如果不是色迷迷的眼神,黄鼠狼应该算个男子汉,个子不高但很匀称,四方脸黝黑却端正有形。我对他冷淡地施了一个冷笑,嘴里哼了一声然后飘然而去,搞了他一个大大的无趣。
黄鼠狼,你还有脸跟我说话。我心里不由生出一股怒气,自然想起了他令人恶心的充满烟味的口臭和满嘴的脏话。这么龌龊的一个流氓,竟然也敢打本姑娘的主意。
我去报社报到那天,跟着人事部主任来到记者部,黄鼠狼一听人事部主任说我是新来的学生,就指着记者部的刘主任说,这是咱记者部刘主任,还兼任社会主义经济办公室主任,简称社经办主任。我正奇怪报社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机构,却看见另外几个人吃吃地偷笑,忽一下明白了那个简称的谐音——射精办。我心想,报社是文明的地方,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下流?跟这样的人做同事真让人难受。
更令我不安的是,试用期让他带我。虽然心里不高兴,我还得装作高兴的样子虚心地向他学习。谁知道这个黄鼠狼对我真没安好心。一个晚上,他在带我去郊区采访回来的路上,与我并排坐在公交车上的时候,把手伸向了我的裙子,还把嘴凑到我的脸上。我毫不客气地打掉他放在我腿上的手,躲开他散发着口臭的嘴,恶声恶气地说,黄主任请你自重。他却涎着脸说,啥叫自重?男女不就那回事,装啥清纯。他说着手再次伸向我的大腿,我忍无可忍,呼地站起来走到车前边门口,没打招呼提前下了车,然后打的回家。
我虽然给黄鼠狼留着面子,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照样跟他出去采访,他却对我的冷漠恼羞成怒。不光让我把一个稿子反复写很多遍(我学的是美术要达到写好稿子的标准当然需要个过程),态度更让人无法忍受。他除了动不动对我大声训斥,还不干不净地骂我笨蛋,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词经常从他的口中喷出。为了息事宁人,顺利度过试用期,我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但我绝不会让他吃我的豆腐占我的便宜。
一次,我爸爸开车送我上班,被黄鼠狼遇见。到了办公室,他大声对所有的同志说,现在这年轻女人要想有个好归宿,要么有个好爹,不缺钱,要么有个好脸蛋好身材,找个有钱有权的老公。像咱报社有个小妮,还不是有个好爹,靠给报社广告球啥都不会照样被安排到记者部。他说完还拿眼睛瞟了我一眼。他奶奶的真是流氓,无赖。我再也受不了他对我的侮辱,把一茶杯水摔到他身上,说黄鼠狼你他娘的算个什么鸟,本姑娘不干了。然后扬长而去。一茶杯水让黄鼠狼胸前的衣服湿透,他被我的行为惊呆。等他回过神来,我已经走出好远,身后传来了他长舌妇一样的谩骂。这个黄鼠狼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真让我恨之入骨,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
回到家我跟爸爸大吵了一架,毅然决然结束了我短暂的记者生涯。
我一袭白色长裙穿过咖啡厅的大厅,在众多男性顾客暧昧的眼光中走向那个我与马文浩约会的紫罗兰房间。我知道自己穿白色连衣裙的效果,高瘦的身材虽然被宽松的连衣裙遮住了凸胸翘臀,却显出一副高贵的典雅。男人们除了对性感的装束垂涎三尺外,更会被具有高贵气质的女人所倾倒。当然我穿白色连衣裙不是为了显得高贵,而是为了欧阳平那个混蛋。他尽管这么不争气地自杀,但我还是为他的死穿上了爸爸擅自为我买的这套裙子。而平素我喜欢穿短小瘦身之类的黑色衣服,那不但可以凸显我的苗条,还能让我较为安分的胸和臀更加突出一点。
此时我没有心情欣赏众多男人对我意味深长的目光,径直走向紫罗兰。马文浩已经为我点了草莓味的珍珠奶茶,他面前是一杯不收费的栀子水。今天他神情有点忧郁,这使他显得更加深沉而有内涵;他的穿着依然整齐而讲究,白色半截袖金利来衬衫扎在墨蓝色梦特娇软料西裤里,配上金黄色苹果牌的皮带扣的黑色腰带,整个人显得严谨而庄重。我知道,他作为一个教师工资不算高,却总是穿国际名牌,这是他少而精的穿衣理念产生的结果——整个夏季,他除了在家里穿的休闲体恤与短裤,只有三套可以替换的出门衣服(三种颜色的金利来衬衫配着三种颜色的梦特娇裤子)。我很欣赏他这一点,靠自己的缜密计划,用有限的薪水换来了贵族般的精致生活。
她走了?我坐在马文浩对面的沙发上说,她很可怜。
这不是你的错,都是我的错。马文浩说。他专注地看着我,眼里流露出对我的无限爱怜和幽幽的无助,我一下子被他感动,扑在他怀里泪流满面,说文浩我爱你。
他抱着我也泪流满面,说:小君,自从我们走到一起,我内心一直都很内疚。我是个有家的人,我应该对家庭负责,张玉把她的青春给了我,还为我生孩子,她去省城,也是为了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她没有错,是我背叛了她。我想过离开她,可她也是快四十岁的人了,我把她撂在半路上,今后的路她怎么走下去啊?但不离开她我更对不起你,我比你大那么多,你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了我,如果不能给你一个结果,我会一辈子于心不安……
别说了老公,我不要结果。我紧紧地抱住马文浩,这时候我感觉世界上他是最好的人。
05
我一连在家呆了三天没出门,躲在自己房间里看电视睡觉,躺在床上回忆往事。与欧阳平在一起的枝枝节节占据了我大脑的几乎全部内存。有时候,我会在那个跟随我七八年的箱子里翻来翻去,那里边装满了我初中毕业以来要好的同学送给我的礼物。这天中午,我在箱子的角落里翻出了一个小巧的泥制猪八戒,以黑色为主辅以白色条块的猪八戒,双臂环抱在肚子上,夸张的头部,大耳大嘴,两眼圆瞪, 憨态可掬。更有趣的是小猪八戒头顶有一个小孔,可以吹出呜呜的响声——这正是闻名遐尔、造型古朴生动、乡土气息浓郁的浚县泥咕咕。我把这个可爱的猪八戒擦拭干净,摆在了我的床头。
我看着猪八戒,想起了那个送我这件礼物的男同学杨云。我属猪,杨云能送我这样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一定是处心积虑、苦思冥想的结果。这之前,我送给他的,是一百九十颗我亲手折叠的幸运星,还有作为他报名考试费用的三百元钱。
想起杨云,我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高中还是大学,谈恋爱都是不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时期谈恋爱的少男少女们最终能够走向婚姻的少之又少,反而品尝了恋爱带来的苦涩。当然我从来不后悔自己曾经的爱情,虽然没有结果,但那毕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纯真的情感。
杨云自从分别就杳无音讯,五年多过去了他像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进入我的视野。我曾经无数次地骂他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但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欧阳平替代了他在我心中的位置,我几乎把他忘得了无痕迹。
如今,杨云在哪里?他过得怎么样?我与泥制猪八戒对视的时候,心里禁不住涌出这样的问题。那个可怜的人,他是否实现了读完大学的目标?是否走出了经济拮据的困境?
门响了一下,我想是妈妈下班了,传来的却是爸爸的声音,君君,有个事我跟你商量一下,我们公司准备在郑州设个办事处,你现在也没事,要不先去那呆着,等你什么时候找好工作想走就走,怎么样?
我说你不用考虑,我坚决不会在你的公司混饭。
你眼下不是没事嘛,我怕你闲着没事干情绪不好。爸爸中午很少回家吃饭,今天回来应该是为了我的事情,但我从心里抵触依靠他的影响力安身立命。上了大学我一直在父母面前叫嚣靠自己努力实现人生价值,肯定不会委身于他们。
老爸你是不是嫌我在家吃闲饭了?我明天就去郑州,但不是去你的办事处,我要去设计公司找份活干,总能养活自己吧?
看你这话说的,谁能嫌你吃闲饭?你要是不想工作就在家呆着,去郑州了我先给你点经费。爸爸对我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让我听话,只好听之任之。本来去郑州是我随便说的一句玩话,这时候我突然决定去郑州,就说,老爸,你先借我五千块钱的经费,半年后还你,我去郑州闯闯,好吧?
爸爸说好吧,你要想去就去吧,下午我给你卡上打一万。
我把去郑州的想法告诉马文浩,他有点猝不及防。是因为我吗?他问。
我说跟你没关系,我不能老呆在家里闲着。再说了,我一个学艺术设计的学士,到郑州还怕找不到一份工作。他说你走前我们见个面吧。
这些天也许是我们的心情都不好,就没有约会。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对我们之间销魂的游戏感到寡淡无味,马文浩也不再显得那么魅力无穷。之前,隔一天不见他我心里就空落落的,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那时候我想我怎么都离不开他。几天的变故下来,我对马文浩的那种入心入肺的爱恋不知不觉变淡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这能算是爱吗?如果是爱,又怎么如此脆弱,经历这么一点波折就烟消云散?我在心里反复地问自己,却找不到令自己信服的答案。
在我去郑州的前天下午,我与马文浩的见面再次选择了咖啡厅,还是那个紫罗兰包间。我没有点自己喜欢的草莓味珍珠奶茶,而是点了一杯冰咖啡和一杯热咖啡。马文浩点了一杯铁观音茶。
我说夏天应该喝绿茶,毛尖或者龙井,要么碧螺春,干么喝乌龙茶?
他说我更喜欢乌龙茶。然后他一边吹拂着茶杯上边的茶叶,一边啜饮热气腾腾的茶汤。
你要走,是要离开我吗?他忧郁的眼神充满了无奈,为什么非要离开殷都?你完全不必在意你的工作是如何得来的。
不,我没有离开你的意思。文浩,在殷都市,我时时刻刻都生活在父母的阴影下。在殷都晨报,一个厚颜无耻的流氓都可以取笑我;在学校教书,本来我挺满意的,可时不时就会听到,这是殷铝公司钟总家的小姐,这是市一小廖主任家的姑娘,我一个堂堂的文学学士,他们不看我的工作能力,老是拿我的父母说事,你能受得了吗?我义无反顾地辞职,没有余地。
说起回到殷都市的感受,我激动不已。我受不了我周围那些因为我父母对我献媚的眼神或不屑的轻蔑,他们的眼光总是盯在我父母的身上而忽视了我。
这的确是个问题,但你可以用能力来证明自己啊。再说了,你不能拿自己喜欢的工作赌气吧?马文浩凝视着我的眼睛,说,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文浩,你不处在这个地方,永远难以理解我的感受。我说,工作可以再找到,而处在那个环境中无穷无尽的折磨我必须摆脱,不然我会疯掉。
也许这就是八零后与六零后的差别。马文浩说,他好像被我说服了。他按了一下服务灯,让服务员为茶杯续水,又问我,集邮公司的工作不是你自己找的嘛,怎么也辞了?
让一个学艺术的学士去干小学生都会干的加减乘除,天天报销售额库存量,这是浪费青春。说起这份工作我仍然怒气难消,殷都市邮政局人事科的人不知道是否看了我的档案,随便把一份工作安排给我,我找人事科长要求调换工作他竟然说邮政局硕士博士有的是,不想干就辞职其他工作没有。本姑娘一气之下想都没想就炒了他鱿鱼。
看来,我还是没有读懂你。马文浩从裤袋里拿出一盒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然后点燃,吐出一团烟雾。
烟都抽上了,给我一支。我把手伸到横在我们中间的玻璃台面茶几上方,马文浩在把烟与打火机递给我的一瞬间,又把手缩回去,然后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在我嘴上,再打着打火机,另一只手捂着火苗送过来,我嘴叼着烟伸向火苗,烟丝因了我的抽吸在火苗下引燃。看着他这么悉心地为我点烟,我的眼禁不住一热,说老公我不离开你。我把他的手贴在脸上,久久地不松开。
这也是我第一次。我说,以前我排斥香烟,曾经极力反对好友席娟抽烟。我再次用力吸了一口,烟雾在我的呼吸道里曲折迂回,冲撞得我咳嗽不止。
是我把你带坏了。马文浩幽幽地说,别抽了乖乖,我也是憋闷得不行才抽几支。
嗯,不抽了老公。我擦擦眼泪,说,以后我到了郑州,星期天没事就回来看你,你去郑州看孩子,也能抽时间找我。
毕竟不能像现在这样常见面了。马文浩说,你走了,我的生日你还能回来陪我过吗?我答应给你的礼物一定会给你。
老公你生日我一定回来陪你过。我笑笑,故作轻松地说。
马文浩突然抽泣起来。看着他像孩子一样抽泣不止,我心里说,这个成熟的男人对我是动了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