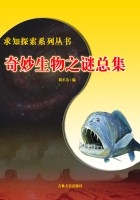01
那个消息像一只被箭射中的鸟跌落在地上一样砸在我的心上。刚刚还在胸中一汪一汪地撞击着的性爱热浪瞬间化成冰块。我一丝不挂地坐在床上,双手抱膝成一尊雕塑,任长发飞流直下遮住我的脸,眼睛里涌出一汪一汪的透明液体,随之而来的是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欧阳平你个混蛋……
马文浩被我的尖叫吓得目瞪口呆,他惊慌失措地穿好衣服从窗帘一角窥视窗外是否有人注意屋内的动静。怎么了乖乖?告诉我。
老公,平死了,他个混蛋,他自杀了。我扑在马文浩怀里不停地耸动肩膀,眼里的液体沾湿了他的肩膀。
马文浩捋捋我的头发,拍拍我的后背,说:那是他的错,谁也没办法。穿衣服吧乖,我马上得去上课了。
我默默地穿着衣服,眼睛一直在不停地分泌泪水。自从毕业在火车站挥泪分别,我以为我与欧阳平已经结束了,就是在回到家后一直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我的意识里也是把他不再当男朋友了。但他死的消息对我的冲击力证明,这个混蛋仍然赖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别太难过宝贝,这是他的命。马文浩把我揽在怀里,捧起我的脸吻去眼下的泪珠说,好了,你先回家呆会,我放学了给你打电话,咱一起吃晚饭,好吧?
我点点头,整理了一下头发,拧开水龙头洗了一把脸,说老公再见,你好好上课,然后凄惨地一笑,戴上太阳镜,走出马文浩的家,一晃身跨出角门来到河堤上。半下午的阳光像火一样挥洒着热情,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有点头晕,站在树荫下望着柳青河发呆。河里的水在这里变成一根细细的绳子,汩汩地流淌着。
站在河堤上良久,我开始迈动脚步行走,但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不想回家,就顺着河堤一直走。我拿出手机再次阅读那条炸弹一样的信息:小君: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欧阳平自杀,用一条boss牌腰带吊在办公室门框上。你们虽然已经结束,但你肯定会悲伤。你要挺住,挺住!娟。
我拨通了远在上海的席娟的手机。娟,是真的吗?怎么会这样?你说,他这是怎么了?我啜泣的声音如一只孤雁在寂静的河堤上飘荡。席娟话里与我一样夹杂着伤感的呜咽,他怎么这么脆弱?有多大的委屈能让他放弃生命?啊?真想不通……你节哀吧君,再哭他也回不来了。
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悲伤,坐在河堤斜面上一个台阶,像一只被夺去孩子的母狼发出嚎叫。欧阳平,你这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家伙!让我快乐过痛苦过如今令我悲痛欲绝的家伙!
我的脑海里闪出那条boss牌腰带。曾经,我听说女士给男士送腰带、领带是“拴”的意思,就是要拴住男朋友的心不移情别恋。临毕业送boss牌腰带给欧阳平,我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让他移情别恋,永远爱我,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确定分手;再就是让他艰苦创业,有朝一日他能成为一个boss(老板)。
我现在才知道,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送腰带给他,尤其是boss牌腰带。这条腰带,不但拴住他的心不移情别恋,还把他拴在门框上成为一道阴森的风景。
你个混蛋,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是要告诉我你还爱着我?还是为了报复我表示对boss的轻蔑?是告诉我你当初分手的选择是错误的?还是表示对我们过去的留恋与怀念?但无论你要表示什么,都不应该选择结束。你这样做之前,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是想用这腰带把我拴在内疚与忏悔的十字架上吗?……
什么样的假设都不能让我释怀。我在心里呼唤了一千次欧阳平的名字,又在心里骂了一千次混蛋,那个高高瘦瘦、清秀温和的男生,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我的大脑中抹去。
我不得不承认,我还爱着他。
在大学里,我们宿舍的四个女生中我谈恋爱是最晚的一个,这并不说明我是个晚熟的小女生。大一的时候因为我心里装着另外一个人,加上大家不熟悉,没看准目标,没有心情也不敢轻易下水;大二的时候大家熟悉了,我也放下了那个令我咬牙切齿的人,可当我开始策划谈恋爱的时候才发现优秀的男生差不多都被别人捷足先登占领了,我只好观望;大三的时候看着别人成双成对甜甜蜜蜜蠢蠢欲动,终于在后半学期春暖花开的时候抓住了欧阳平,暗暗得意自己运气好而陶醉在爱的氤氲之中;大四的时候我与欧阳平一起流着眼泪看校园小说《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而我却执着地认为毕业后分手失恋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
毕业前的几个月时间,我和欧阳平在校外租了一个带厨房卫生间的标准间同居,同吃同住同学习出双入对。我仍然是同宿舍最后一个搬出宿舍与男朋友一起住的好学生。我很早就知道室友席娟、斐燕与男朋友的幸福生活和痛苦人流。而我一直安然无恙,这当然不是因为我是不毛之地,更不是欧阳平无能为力,是他不敢耕耘。
在有了马文浩之后,我才知道欧阳平真是个有理智的男人。他那么年轻竟然能克制住自己不与天天躺在他身边的我发生关系,一对学艺术专业的恋人在一年半的热恋中能守身如玉,现在想来真有点不可思议。上初中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现在要想找处女到小学都不保险,得到幼儿园。我对此说法虽然不以为然,但也了解一些中学生小小年纪就初涉性爱江湖,早早把自己变成女人。
我与欧阳平一直没有越过最后的雷池,也是我意想不到的。刚开始,在宿舍或公园,我们拥抱接吻,他总是小心翼翼。很多时候我都渴望他勇敢点,跨出实质性的一步,可他除了用嘴和手在我身上探索之外,再不敢有深层次的开发。
我问他,你不想吗?他说想,但不敢。我问你怕啥?他说我怕你怀孕。我说怀孕了去医院打掉就行了,怕啥?他脸一红,说我可不敢跟你去打胎,叫谁知道了还怎么见人。我说你还怪脸皮薄呢,还是个男人不是?白长了一米八的个子。
那时候我因为没有享受过性爱的销魂,他能忍住我也不太迫切,不知不觉就那么过来了。我们搬到校外的第一天晚上,我做好了把自己变成一个成熟女人的心理准备。吃过晚饭,早早地,我把自己洗得干净净的,弄得香喷喷的,躺在被窝里等他。他显然是在克制,故意慢慢腾腾地收拾东西。
平,快过来。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千娇百媚,声音里充满了水。身体里一汪一汪的热浪桀骜不驯。他嗯了一声,却不敢抬眼看我,我说洗洗睡吧。他走到洗手间,在水池前久久地洗手。我说厨房有热水,你冲个澡。他又嗯了一声。
我在渴盼中关掉大灯,打开了床头的粉红罩台灯,整个房间充满了温馨与神秘。冲完澡的他穿戴整齐地站在床边,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心神不定。
我说:脱睡!他说还脱吗?我有点恼火,说你平时都穿着衣服睡?他害羞地笑笑,说不是你在嘛。我一把把他拽过来,一边用嘴堵住他的嘴,一边扯他的衣服。他上宽下窄的脸颊,安分的鼻子,浓浓的眉毛,小小的眼睛,黝黑的皮肤,坚实的胸膛,修长的双臂,魁伟的身材,在我的眼里,他简直就是一个标准的男模。
他在我的面前笨拙地开始行动。当他颤抖着身体就要突破的时候,扭曲着呻吟着的我嘴里突然喊道:疼啊!他好像一惊,胳膊一软伏在我身上,便鸣金收兵了。
之后,我总是在他即将突破的时候喊疼,他一听到我喊疼就停车罢手,我们也就一次一次地错过对性爱的实践,成为非常珍稀的走出校园还保持纯洁的大学生。
我看上欧阳平,纯粹是偶然。他是个普普通通说不上帅也说不上丑的男生,除了个子高,学习努力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太引人瞩目的地方。他又不油腔滑调,更没有赶谈恋爱潮流的进攻意识,加之年龄比一般同学小一两岁,还不善言谈,所以这么久他都没有引起众多女生的关注,与我一样形单影只。后来我以我的慧眼发现了这块被朴实掩盖的玉:在一次周末的班级舞会上,我与他连续跳过几曲交谊舞,近距离长时间地端详过他的那双小眼睛之后,突然发现这个平时很少看一眼的甘肃男生也有几分可爱与魅力,那一刻我决定把他据为己有。我也是个普通女生,但长相还算有几分姿色,他对我当然没啥挑剔,就顺水推舟乖乖地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我们的关系突飞猛进,几次约会之后很快就由地下转向公开,并成为艺术系最般配的金童玉女。
我们的交往与小说里写的大学生谈恋爱没有什么两样,平淡而充满浪漫与温情。看起来老老实实的欧阳平,与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会妙语连珠,出口成章。
小君小君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小君我饿了,让我吃一口。他经常像一个撒娇的孩子一样在我耳边吟诵歌词。我满足地嫣然一笑,奖励他一个侧吻,说继续。他歪着头作沉思状,如果不在校园,他会说我背你行进三百米,作为对你给我奖励的回报,如何?我说不稀罕,你又不是马骑着不舒服,算了,还是本姑娘自力更生吧。他双手分开,耸肩做无奈状,说不能为你效劳,深表遗憾。我忍俊不住,手一挥说,去去去,别在那拽文了,给你个机会,跑步给本姑娘买个随变去。
随变是我喜欢吃的一种冰糕,而且我不分春夏秋冬,什么时候想吃就吃,哪怕是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来例假肚子痛得实在受不了,跑到医院看医生。医生是个色迷迷的老头,他问经血是什么颜色,我说当然是红色。医生问是不是发黑,我说好像有点发黑。他说吃凉东西了吧?我说上午吃了九块雪糕。他说你要是吃十八块雪糕肚子就不痛了。我说真的?我一会就到冷饮店坐那一口气吃十块。医生哈哈大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来月经还敢吃雪糕,不是找事嘛。我说不吃雪糕就不痛了?他说会好点。但过后我总是抵不住随变的诱惑,把痛经忘到九霄云外,照样在例假的红灯下吃雪糕。
领命买雪糕时候的欧阳平最可爱,他两腿一并,打个立正,敬个近乎专业军人般标准的军礼,然后跑步去冷饮店买回随变,再跑步来到我面前,又一个立正,双手捧着随变递到我手里,说请首长慢用,小心冰牙。
我噗嗤一笑,说帮我撕开。他熟练地撕开,让雪糕从包装袋里露出半截,再把撕开的包装袋缠在雪糕把上。这时候我感觉我真幸福。这个在同学们眼中寡淡无味的小男人竟这般有情趣,也算我的福气。
席娟与斐燕曾经问我,你那个平儿少言寡语的跟你在一起有啥意思?我笑笑说别用传统眼光看人,我的平儿是别具风味,绝对不比你们的帅哥差。她们问有什么特别风味,我说不告诉你们,怕你们知道了挖墙脚。她们把我压倒在床上,用手在我身上乱摸,说你心里这么阴暗,老实交代,是不是想挖我们的墙角?我在她们的折磨下手足乱舞,说谁稀罕挖你们的帅哥,我守住平儿就满足了。
眼看着毕业一天天临近,我问他,你准备去哪里?他说我想留在兰州,要是留不到兰州就回老家县城。我说你想没想过跟我回郑州?他说没想过,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我不能离他们太远。我说想过让我跟你留下来吗?他说想过,但你老爸不是不同意你留在兰州吗?我说你别说我老爸,你愿意让我跟你一块留下来吗?他说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留下来,哪敢奢望你能跟我一起。我说你留在兰州我回郑州我们以后怎么办?他突然神情黯淡,说我不敢想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
我失望地看着他沮丧得在我面前不敢抬眼,心里一片茫然。我们真的要面对毕业就失业失恋的现实?多少次,我默默地扑在他怀里黯然神伤,我说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清楚那话不光是安慰他,也是安慰我自己。
02
我在河堤上一直坐到马文浩的电话打过来。这个比我大十五岁的有妇之夫如今被我称作老公,而且对我很尽力地履行着老公对老婆的爱抚与亲热。曾经他是我高中母校的政治老师,在三年的高中课堂上为我传道授业,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当年,不高不低不胖不瘦眉清目秀的马老师在女生的眼中是成熟英俊,能言善辩,风流倜傥,他的办公室经常有一些大胆的漂亮女生去请教哲学或人生观问题。我当然不在此中间,因为我在我们02届文三班平常得就像一只白兔子放到白兔群一样没有特色,学习成绩也是和尚的帽子平平坦坦。
到了高三,我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面临的严峻形势。以我的成绩,恐怕只能上个高职高专,我当然不是看不起高职高专,问题是我想在不提高文化科目成绩的前提下能上个更好的大学,这样我就跟风学起了美术,开始走艺术考生的路子。最后的结果证明我的选择非常英明,尽管我并不喜欢美术。没费太大的劲,当年高考文化课分数连高职高专都勉强的我考上了兰州一个二本大学的艺术系。
因为要学习画画,我每到周六周日就到校外的美术辅导班去上课。而美术辅导班的老师是马文浩的同学,大部分学美术的学生都是通过马文浩报的名。这才让我这个普通的女生有机会接触马文浩并熟悉起来。但我敢保证,那时候我对马文浩绝对没有非分之想。这其中的原因,一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发育成熟还不知道仰慕英俊潇洒的男性;二是我没有恋父情结,不喜欢与比我年长太多的男性交往;三是不懂得欣赏男性的成熟之美,更喜欢个性张扬的同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