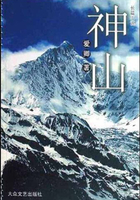几天后,白玫瑰因公事到地委顺便找到我。在我的住处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们都忘记了时间,等她说要走的时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我只有安排她住下。吃过饭,我独自回到自己的住室,想着灿烂如花的白玫瑰,心里一片混乱。她与一位女同事住在一个屋,夜里她还会不会来跟我说会话?我如果对她有亲密举动,她会不会同意?这样想的时候,我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一个地委组织部长,是不应该犯这种错误的。对,一定要克制自己,坚决不能冲动。她就是来了,只能说说话,最多握握手。这样劝着自己,却又禁不住老想她的身体。下午,我们一起说话的时候,我多次瞟过她的胸部。春末夏初,外罩里她只穿了一件紫、青竖条相间的棉布衬衣,而外罩没有系扣,紧致的衬衣下小山丘一样圆润的乳房显得有些不安分,而裸露的一段雪白的脖颈,更让我过目难忘。与她几个小时的独处中,我禁不住心猿意马,意乱情迷,甚至有几次神情恍惚,心里早已伸出去一只手,在她的脸上,脖颈,胸脯,后背,大腿,臀部,细密地抚摸了无数次。那一刻,我体会到,与她独处是快乐的,也是痛苦的。
我在想白玫瑰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小蔓菁。这个令我昼思夜想的小女人,好像在一旁注视着我,当我对白玫瑰有非分之想的时候,我仿佛听到小蔓菁在对我说,吴仁,俺在家等着你,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对俺好……
我双手在脸上做了几次洗脸的动作,摇摇头,苦苦地笑了笑,对自己说,别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即使她来敲门也不能开。
刚洗完脚,就听到敲门的声音,接着是女人充满水的声音:吴部长,是我,闻世香。
刚才还确定她敲门也不开的我,突然有点手忙脚乱,动作麻利地打开门,嘴里竟有些语无伦次,坐,坐,我当是谁呢,坐吧,坐吧。
白玫瑰站在门口并不进屋,笑吟吟地看着我,吴部长,咱一起出去走走?
我怔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好好好,咱出去走走。在白玫瑰这个迷人的姑娘面前,我早已把自己的身份忘到九霄云外。
出了地委院子就是野外,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农忙路走向田野,温热的风一阵阵吹来,吹在我发热的脸上。麦穗已经灌满浆,沙地低矮稀疏的麦子在夜里也有了一些气势;近处村庄里飘来一阵阵的洋槐花香;远处的小河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蛙声。
我们并肩走着的时候,白玫瑰离我特别近,有几次她的胸脯都偎到了我身上。走到一棵枝繁叶茂的棠梨树下,我们相对而站,我可以听到她的呼吸,甚至脸上可以感到她呼出的香气。我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什么,也不记得我的手怎么就捉住了她的手,她没有一点扭捏,我看见她的眼神在氤氲的夜里格外明亮,她凝视着我的眼睛,任我的手握住她的手不停地摩挲。她的大胆鼓励了我,我一用力把她拉到怀里,两手开始在她的身上搜索。我吻住她的嘴唇的时候,脑海里闪了一下小蔓菁的泪眼。
接下来我们久久地抱在一起。倘若不是小蔓菁一次次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也许我们会进展得更快。
时间在慢慢地流逝,麦香,槐花香,蛙声,都渐渐地被我们遗忘,我们只记得对方的身体,对方的气味。在如梦如幻的纠缠中,我们终于爆发,不顾地上满是尘土或砖头坷垃,我们发疯般滚在一起,浑身沾满了无论如何拍打都不掉的土。
就这样我们堕入情网,在她的石榴裙下,我忘记了党的纪律,把小蔓菁也抛到脑后,制造了一起沸沸扬扬的绯闻。
党组织对我的绯闻与行为当然不会置之不理,为了让我与白玫瑰分开,也是为了防止我犯更大的错误,把我调到豫北地委,仍担任组织部长。
如果到此为止,喜欢女人让我付出的代价会大大降低,在以后的革命道路上,我即使对党做不出杰出贡献,也会成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
也许是命中注定,不停地有一个又一个的女人来诱惑我。要命的是,我喜欢的女人也都喜欢我。她们喜欢我,排除我身居高官的因素,跟我的长相与素养也不无关系——高高瘦瘦、身上洋溢着书生气的我,打扮得体,温文尔雅,谈吐不凡。这为我与自己喜欢的女人来往奠定了基础。
在因为与白玫瑰的绯闻调动工作之后,我与小蔓菁的关系也陷入僵局,又一个令我着迷的女人沈君兰进入我的视野。她是地区抗日救国总会的妇女部长,工作中我们一见如故,这位情窦初开的沈君兰很快与我缠绵在一起,超越了同志关系,把工作做到了床上。有了这层关系,我们经常借助工作的名义,频繁接触。我发疯般地与她相好,置好言相劝与流言蜚语于不顾,沉陷到男欢女爱之中。
我们的行为再次被党组织关注,地委书记王武亲自找我谈话,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我不得不接受批评,暂时从甜蜜的爱情之中回过神来。这时候我对自己说,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因为男女关系事件已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该收收心,不能再执迷不悟了。
04
说到这里,我有些沉痛。假如,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变故,也许我会沿着共产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当然,这种假设是虚无的,是飘渺的。
我之所以提到这次变故,决不是想为自己开脱或辩解。这次变故,对我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也是这次变故,让我多年来对党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与怀疑。
地委书记王武对我进行过批评之后,准备把我与沈君兰调开。这当儿,一向以极左著称的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余谦到豫北地委巡视工作。他了解到我与沈君兰的绯闻之后,当即责令地委机关召开党支部大会,对我进行公开批评,并给予很重的处分:撤销职务,停止现职工作,留职察看,分别到接敌区柳青县和相邻的长垣县开辟新区,以观后效。
我的自尊心遭到极大伤害,情绪低落,牢骚满腹,甚至万念俱灰。到了这一步,我还顾忌什么?已经撤了职,停止了我的工作,再处分我还能怎么样?我回到柳青县城东南的一个小集镇岳村集,开始筹备成立柳青县联合救国会。这时候,我已经抱定破罐破摔的思想,继续与沈君兰联系,把已经调到长垣县工作的沈君兰叫到岳村集同居。
小蔓菁知道了我与白玫瑰的事情后,大闹过一场,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和她的那个家。等到我与沈君兰的事情传到她耳朵里,她再也无法忍受我的背叛,悬梁自尽。小蔓菁的死让我痛苦了好多年,每每想起她,我都会羞愧得无地自容,这个痴情的女人,把她全部的爱都倾注在我身上,我却辜负了她。
岳村集是王泰恭的据点,他与我一样,地主出身,师范毕业,教过书,会玩枪,文武双全,当过联保主任。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关系不错。1938年,日军占领柳青县,联保散伙,王泰恭凭借几杆枪拉起一小股游击队,在柳青县城东南的乡村里活动。
我受处分后,开始与王泰恭及附近的土匪联络,在一起吃喝玩乐,还让自己的警卫员和助手在王泰恭的队伍里兼职。说句心里话,那时候我没有一点叛党的念头,我与他们接触,不仅仅是消遣,也想把王泰恭争取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阵营中,将功补过。
然而,接下来豫北地区开展的“肃托”运动却殃及了我。“肃托”运动,就是在党内查找“托洛茨基”分子,“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说白了就是要抓间谍、特务。
春秋中文社区春秋中文
而此时,地委书记王武因准备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比余谦更“左”的信西华代理豫北地委书记。我很了解信西华这个人,他疑心特别重,往好里说是极左、主观,往坏里说就是狭隘、阴毒,他当组织部长时经常杀人,甚至部下不及时汇报工作都会被他下令处决,动不动就活埋、杀头,大家都很怕他。
“肃托”运动一开始,信西华先盯上了陈曙辉(时任冀鲁豫卫河支队司令员),信西华对这个别动总队出身的国民党少将很是怀疑,决定杀掉他,理由是国民党的《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中有一条:“策动本党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队,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信西华由此判断陈曙辉是特务。王武听说信西华要杀陈曙辉,赶紧劝阻,最后信西华答应把陈曙辉送去学习,但始终不同意他入党,也不承认他是高级干部。
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点,信西华后来被撤消职务、开除党籍。因为信西华的错误决定,学习后到部队作为文化教员的陈曙辉在百团大战中不幸牺牲。战友们检查他的日记时,发现他曾经是支队司令员,随后就把情况反映到党中央,中央很快派调查组调查,查清了信西华的问题。书院,文学论坛,图书,战略,装备,游戏,投资,理财,股票,网络,证券,SOHO,虚拟文学,中文论坛,春秋中文,贴图,小说,历史,战争历史,中国历史
文学|虚拟文学|武侠奇幻|历史文化|休信西华没杀成陈曙辉,又盯上了我,他认定我已经变质。关于我变质的理由,信西华有两个:一是我的生活作风有问题,二是我和王泰恭交往密切,形迹可疑。
信西华很快对我采取了强制性措施,责令我迅速归队。我非常清楚,一旦回到地委,信西华有可能很快就将我处决。于是,我躲在岳村集,坚决不去地委。
1939年阳春三月,我与沈君兰从岳村集去附近一个村赶会,正好碰到中共柳青县委秘书修昂。修昂是经我介绍入的党,我们私交不错,便在会上一起吃饭。饭间,修昂趁沈君兰出去劝我,吴仁哥,你已经因为男女关系受了处分,现在不能再搞了,收手吧,现在改正还不晚,也别再跟王泰恭他们来往了。
我说,我现在就是拉王泰恭投靠共产党,我还在革命,可信西华让我回地委,我能回去吗?他这个杀人狂,疑心又重,我回去了他还不把我杀了?
修昂说,领导同志说了,只要你改正错误,他替你担保,保证不让信西华杀你。
我又对他说,我与沈君兰相好,并不影响我革命,小蔓菁死了,我还要与沈君兰结婚呢。
修昂看劝不动我,也不再说什么,我们不欢而散。
我没有想到的是,修昂给领导汇报了见我的情况。当天晚上,八路军豫北大队将我抓住,并连夜把我押送到地委。
直觉告诉我,信西华那个杀人狂在等着我就范,这一去肯定凶多吉少。
05
五花大绑的我被两个战士押着,走在去地委驻地的路上。
又是春末夏初的季节,麦香、槐花香四处飘荡,蛙声悠扬。我想起了一年前我与白玫瑰在一起的那个夜晚,津津有味地回忆起我们短暂而充满浪漫的恋情。她因为与我的绯闻,不得不与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丧妻干部快速结婚。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也许,她改变了自己外向活泼的性格,过起了默默无闻的生活。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她给我的那份幸福,都会怀念跟她在一起的分分秒秒。
回忆起与白玫瑰的恋情,我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回过神来,我感觉浑身都不舒服,被绳索捆绑的身体无法舒展,脖子和手腕被绳子勒着的地方火辣辣地疼。我对两个战士说,咱们都是老乡,好歹我也是个高干,再说我又不是敌人,我的问题也是暂时的,一时落魄,你们就这么对我?能不能把绳子给松一点?能把人勒死。
说这话的时候,我非常清楚自己在自欺欺人。我竖着进到豫北地委大院,再出来恐怕就是横着了。我突然一阵伤心,泪水喷薄而出,投身革命这么多年,没有死在敌人枪下,却要死在一个党内的左倾主义手下。
不,我不能就这样就范。我忍住泪水,继续说服两个战士,老乡,老弟,告诉我你们叫啥名字,等我的问题解决了,官复原职了,我一定给你俩弄到我身边,混几年也弄个一官半职。
两个士兵你看看他,他看看你,再看看我,我说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我能跑了吗?给我稍松点就行,别都解开,好吧?
其中一个士兵说,俺听说过你,是个大官。他又对另一个士兵说,都是老乡,给他松点吧,捆得真紧。
另一个士兵就说,松点就松点吧,反正咱有枪,他要敢跑咱就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