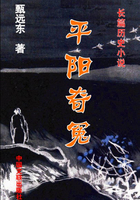我第一次看到了平原的田野。大片大片的麦子像刚发育的少女一样,已经鼓起了麦穗,在和煦的春风里摇摇摆摆。麦子里边还有开着白色紫色小花的水萝卜棵,它藏在麦子里就像做错事情的孩子一样默不作声。我跑到麦田边,便不敢再往里走,我惧怕像海一样的麦田把我吞噬。我站在地边,用嫩嫩的小手抓住一把鼓鼓的麦穗往下扯。手与麦子接触的感觉很微妙,就像娘的头发一样柔软,麦叶和麦穗在我手里被抓成碎片。我激动地不知所措,嘴里发出愉快的欢叫。
“小三儿,打死你!”
娘的一声厉喝结束了我短暂的欢叫。她放下手中的东西来到我身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
“这可是小麦,你现在把它拽下来纯粹是破坏,将来这可以打下麦子磨成面蒸白面馒头。”
她在我的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看看四下没人,又说:“要是被人发现了,非把你抓起来不行,你这个小兔孙子。”
我惊恐地瞪着眼睛,我真的很害怕。娘的话让我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不敢再去扯麦子。
06
我和我的家人来到了河南东北部平原上一个叫冢东村的普通村庄,这并不是我姥姥家所在的村庄。这时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他们慈祥的笑容一点都没有打动我和我的两个哥哥,我们也不喜欢他们。
娘却很热情地对我们说:“永生留生换生都过来,叫爷爷奶奶。”
南永生满不在乎地说:“叫就叫呗。”
然后南永生面对着墙壁,眼睛看着屋顶,嘴里叫道:“爷爷,奶奶。”
南留生不解地看看爹娘,瞪大眼睛审视了一下老头和老太婆,问:
“他是我爷爷?她是我奶奶?”
娘说:“这个兔孙子,净瞎问。不是我能叫你叫啊?快叫。”
南留生很不情愿地小声叫了一回,我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痛痛快快地大声叫了爷爷奶奶。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过爷爷奶奶,一下子出现了陌生的两个老人,我感觉很新鲜。
老太婆插话说:“媳妇儿,以后可不能再骂孩子兔孙子了,那等于在骂俺老两口。”
娘矜持地笑笑,几近羞涩地说:“我以后改了。”
我和南永生南留生完成了娘吩咐的任务,娘这时候又说话了,她像演讲一样慷慨陈词:
“永生,留生,换生,我给你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就不再姓南了,你们就改姓许了,包括你爹,他也姓许了,他不再叫南钢蛋了,他叫许钢蛋了。你,永生,叫许永生,原先的作业本名字都得改过来;留生,你叫许留生了;还有换生,你叫许换生了。我还给你们说,谁再问你们姓啥,都得说姓许,可不能说姓南。记住了吗?一个一个说一遍。”
我的大哥想说点什么,我的二哥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他对改姓的不满,甚至试图发表点反对意见。我娘早就识破了他们的技俩,果断地打断了他们还没有出口的话。她说:
“什么都不要问,什么都不要说,小孩子有很多事情都不懂,不懂也得听,坚决得听。”
我娘以不可侵犯的权威镇住了我的大哥二哥。他们垂头丧气地坐在小板凳上,眼睛专注地望着屋顶,好像屋顶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我和我的哥哥弟弟妹妹们大概有三四年姓许,后来突然有一天我们的母亲郑重宣布:以后不姓许了,还改姓南。我爹这时候像拿到了别人欠他的钱一样高兴,他说:“到底改回来了,你真了不起。”
娘再次表现出武则天的派头,她振振有词地向全家发表演讲:
“我说过,为了达到目的我们暂时可以让步,但我们一定能最后胜利。”
我的大哥那时候已经在学校里把许永生写得很顺溜了,他有点不耐烦地表示:
“改来改去,真麻烦,这回不会再改了吧?”
我的二哥也很不以为然,他接着大哥的话说:
“就是呀,说准了,别过一段时间又改。”
娘斩钉截铁地说:“不会再改了,你们是南家的人,以后你们永远姓南。”
那时候我对姓什么毫不在乎,因为无论姓南还是姓许,都是娘说了算。这时候我彻底知道了我爹是个外强中干的怂货,看着他高大魁伟身强力壮,却一点也没有男子汉的气魄。他怕老婆的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后来我还发现,改姓这一事件紧密联系着爹娘跟爷爷奶奶的关系。我们恢复姓南以后,我们家与被我们叫做爷爷奶奶的一对老人彻底决裂。
那个年近七旬、叫许仁卿的老头被我娘气得痛哭流涕,老太婆干脆一病不起,没多久就撇下老头,离开人世。
决裂的过程并不复杂。我娘每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去找许仁卿夫妇。这对无儿无女的老人节俭了大半辈子,到老了非常想拥有儿孙满堂的繁荣,不惜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帮我们家盖起三间屋子和添置了日常用品。他们这时候已经没有更多的东西来填补我们这个无底洞一样的大家庭!我娘不答应了,她站在老两口的院子里,振振有词地说:
“我们是你们的孩子,你们是我们的爹娘,这孩子有困难了当爹娘的不能不管吧?”
老人无话可说,像犯了错误一样被我娘数落。但最后他们还是拿不出钱来。
我娘这样找了他们几次,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没有半点收获。我娘开始了第一步行动。她对我爹说:
“以后见了老头老婆不能再叫爹叫娘了,叫爹叫娘他也不管咱,干脆不叫了。”
我爹迷惑地问:“那叫啥?”
我娘思索了一会,最后胸有成竹地说:“叫大爷大娘。”
就这样,我爹和娘的认下一年多点的爹娘变成了大爷大娘。这个时候我和哥哥们对老头老太婆的称呼还没有改变,继续叫他们爷爷奶奶。
大概又过了两年,我娘又创造性地改变了包括他们在内的我们与一对老人的关系。一天,她把我们都叫到跟前,反复强调地对我们说:
“我给你们说,以后再见了老头老婆,都不能再叫爷爷奶奶了,都叫大爷大娘。听清楚了吗?”
南永生说:“爷爷奶奶变大爷大娘,那不是低了一辈吗?”
南留生也说:“就是呀,这是咋回事?怎么又变辈份了?”
娘根本不解释,她像一个独裁的女王一样蛮横地说:
“不要问为什么,让你们叫大爷大娘你们就叫大爷大娘,谁叫错了看我不撕烂他的嘴!”
我的两个哥哥都伸了伸舌头再也不敢有动静了。
我的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她和爹变成了与许仁卿夫妇辈份一样。当然不仅仅是辈份的变化。关键是一转眼我娘就把我们家与许仁卿夫妇的关系变成了街坊邻居。
等到把姓恢复过来的时候,我娘已经把许仁卿夫妇对我们家的帮助忘到九霄云外。她说:
“现在我们用不着他们了,我们还要这两个老家伙干啥?我们养活自己的孩子都很困难,根本没有能力来照顾两个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爹担心地说:“街坊邻居会说闲话的。”
我娘一挥手,她再次像一个凯旋的女将军一样告诉我爹:
“谁愿意说闲话就说吧,闲话啥作用也不起,还能不让咱生活?”
07
真正到了平原,我才知道娘说的话并不可靠。她说能吃上白面馒头,其实也就是刚打下麦子的时候能吃几顿白面馒头,以后在一年中的好长时间里,都将会与白面处于分别的状态。
爹在开始的时候有点埋怨娘,他说:
“一点都不值,为了来平原我还认了爹娘,还得改姓,生活一点都没有改善。”
娘这时候虽然无话可说,但她的权威不可侵犯,她不客气地对爹说:
“男子大汉的瞎胡埋怨,你要是后悔了你自己回去,我和孩子是不走了。”
爹知错地笑笑,像一个害羞的孩子一样低下头。
娘又说:
“认爹娘的事情你得想开点,要不认没法下户口咱不成了黑人?再说了,这一认爹娘咱就是他们的儿子儿媳妇,他们就给咱盖了三间屋,还给咱添置了屋里的东西。叫个爹叫个娘算啥?可不是白叫的,咱省了多少事。咱现在叫他爹,叫她娘,那是用得着他们,什么时候用不着了就不叫了。给他们养老送终?到时候再说吧。亲儿子还不一定能做到呢。改姓更没有什么,姓啥还不都一样?你那个南有啥好的,远没有现在这个许好听,真不行了咱回头再改过来。”
我爹听得目瞪口呆,他支支吾吾地说:
“这能行?”
“行不行不是他们说了算,哼,到时候咱在村里站稳了是我说了算。”
我娘这个精明的小女人为自己的创意得意洋洋,她用手狠狠地点了一下我爹的额头,恨铁不成钢地说:
“像你这样呆头呆脑,咱能从山沟里迁到平原?你啥事也办不成!”
我的娘训斥过我的爹以后,雄赳赳气昂昂地从高大魁梧的爹面前走过去,就像一个女将军在阅兵,很有点武则天的派头。
我娘的派头对一家的生活一点也没用。夏天的时候,为了让我和我的两个哥哥省衣服,她只给我们每人做了一条说不清楚是什么颜色的棉布短裤,上衣就没有了。娘说:
“男孩家就是好,夏天不穿衣服多凉快。”
已经上小学三年级的南永生说:“娘,老师说不让光脊梁上学。”
娘说:“这是谁的规定?你给老师说吧,就说你娘说了,俺家没衣服,要不让光脊梁就让他送给你一件。”
南永生只好放弃了给娘要上衣的计划。南留生本来正支持哥哥的行动,也想有所表示,但在娘的威严中也乖乖地跑出去玩了。
我娘在穿衣服方面对我们弟兄三个真是节省到了极致。冬天里,我和南永生、南留生每人都是一件毛蓝棉袄一条毛蓝棉裤一双黑色棉鞋,内衣和袜子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外罩也遥远得可望而不可及。那时候,四五岁的我又矮又小,穿着又宽又大的毛蓝棉袄棉裤,把两只手抄在另一只的袖管里,走起路来就像一个圆球在滚。无论天多冷,我和我的两个哥哥棉袄的脖子扣是永远不系的,更没有围巾来遮挡脖子,脖子和一小片胸口就露在外边,任冬天的大小寒风吹拂。但我并没有感觉寒冷,只是有点凉。
睡觉的问题是在一个初冬的夜里暴露出来的。
在夏天,我和南永生、南留生睡在院子里的树底下,虽然有蚊子骚扰,但我们都有足够的免疫力,蚊子在我们身上连一点痕迹都留不下。
冬天就不行了,要睡在屋里,可被子太少了,我们一家为了暖和挤在一张加宽的床上,床上铺了厚厚一层麦秸,我和爹娘一个被窝,南永生与南留生一个被窝。
那天夜里,我感觉夜已经很深了。与我睡在一头的南永生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他像一根木头一样沉静。南留生虽然睡在床的另一头,我无法知道他此时的状态,但我能想象他睡得肯定很香,就是天上下雷也不会把他惊醒。爹娘一直在说话,声音时大时小。我蜷在爹娘的脚头,一动也不敢动。爹的脚总是能轻而易举地碰到我的脸,他的脚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酱味,让我整夜都处在这种味道之中。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久久不能入睡,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爹娘像纺车鸣叫一样的说话声。
我的灵魂在夜的黑暗中盘旋,无数次回忆起窑洞的轮廓。爹大概以为我睡着了,他用腿碰碰我,无限温柔地叫了我一声:“小三儿。”
娘说:“你叫他干啥?肯定睡着了。”
我没有答应。我并不是因为娘说我睡着了才不吭声,而是不想吭声。他们在夜里叫我,无非是为了避免我把尿撒在被窝里让我起来撒尿。
我又听见娘说:“他们都睡着了,快来吧。”
我不知道娘叫爹“来”干啥,爹动了一下,好像翻了个身,接着就晃动起来,被子在晃动下也随之而动,被窝里就钻进来一股股的风。我非常恼火,他们的晃动让我感到了冬天的寒冷。我在黑暗中大叫道:
“谁再扇风我就骂了。”
我的叫声在黑暗中就像一只折断翅膀的鸟碰到墙壁一样突兀,立即有效制止了扇风运动。
爹好像又翻了个身,他的腿再次碰到我的脸,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娘好像有点惊慌,她颤着声说:“没睡着呀,你个小兔孙子。”
我仍然不吭声,我懒得搭理他们。这时候我其实很想撒尿,可我不想动。我的灵魂仍然在黑暗的屋里盘旋。接下来,我把一泡热尿撒在了被窝里。
次日,爹开始在院子里挖一个有像楼梯一样台阶出口的方坑。他说:
“为了冬天不挤在一张床上,我给你们挖个地窖。”
就这样,爹把那个方坑挖了一人多深,然后在上边棚上几根木头,再铺上玉米秆麦秸,最后糊上一层泥,就成了一个地窖。爹又在地窖里铺上麦秸,把有限的被褥拿下去。我和南永生、南留生就被从堂屋里的大床上驱逐出去,住到了地窖里。麦秸和有限的被褥让我们弟兄三个温暖无比,即便是风雪交加,地窖里也暖洋洋的。
我们弟兄三个被赶到地窖里以后,我的爹娘开始了他们肆无忌惮的造人运动,他们几乎用最短的时间,为我生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娘恼火地说:
“生了小三儿就叫换生,还不换,又生了两个和尚才换了个花妮妮,我就不信我这肚里光有小鸡鸡。”
我们家里更热闹了,我和我的哥哥弟弟妹妹们都特别能吃。我娘每顿饭都要弄一大锅丢了红薯的玉米糊糊,更多的时候是煮红薯或是煮红薯片,偶然会做一顿葱花面条,蒸一次玉米面、红薯干面两掺的馍馍。那一般都是在过节的时候,我和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会吃得肚子圆溜溜的。
08
在我的繁多的记忆中,那次刻骨铭心的拉煤,至今都让我不寒而栗。
因为穷,大哥二哥的媳妇一直都没有着落。而只有十五六岁的我不上学了,开始成为村里的一个男劳力。
这时候,我的两个弟弟和妹妹都一天天长大,而我们家的房子一间也没有增加。除了妹妹跟爹娘住在堂屋里,我和两个哥哥两个弟弟五个人继续住在地窖里。
一天, 大哥对我们说:
“老二小三儿小四儿小五儿,都别吵吵了,听我说,我问你们,住在地窖里舒服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