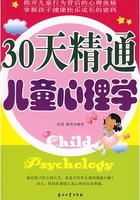或许,你会笑我自恋。当所有的人都不信任你,不相信你的时候,能够给你最大信任的,就是你自己,能够永远对你说,我支持你的也只有你自己。
在另一部戏里,我和"山鸡哥"陈小春有一场"对手戏"。
陈小春演的公子哥问跑堂的小伙计:你们大掌柜的叫什么名字?瘦骨嶙峋的我站在一边回答:"你们连我们大掌柜叫什么都不知道?"另一位女演员说:"我们是从外地来到京城的。"
"难怪啊!"我边抹桌子边说。
"告诉你们,我们家大掌柜的就是京城大名鼎鼎的刘二爷。"我停了一停,大声地说:"大名叫刘金宝。"说完还用手指往外一指。
这是我为数不多的有台词的演出,就是在这样的戏里,出来的也只是我的侧影,我的正脸只晃了一晃。出现在戏里的配音也不是我的声音,听起来怪里怪气的一个声音。但是我已经十分满意自己的镜头。
我相信,在群众演员中间,在我在工地的工友们中间,我的所作所为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自我陶醉和自我催眠。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做"内心强大"。我不是内心强大,他们对我的每一次批评,每一次否定,对我起的作用,比他们看出来的要大得多。每一次被否定后,在我的内心,都会有两种力量在撕扯,一种是:"他们说的对。"另一种是:"要相信你自己,你会和他们不同。"
我想我应该感激年纪。十六岁的年纪,内心里永远燃烧着一种不明白从何而来,但的确像山火一样旺盛的火焰。在这种火焰的作用下,你看不清周围的环境,但永远会盲目地相信自己的能量。所以,每一次两种力量无论如何撕扯,第二天,阳光再次射进小屋的时候,我还是要按自己初衷去行事。
我可能没有看清很多东西,但我始终很清楚,我为什么要来北京,我在这个城市里要得到什么。
最痛苦的时候,我跑出去,用冷水浇自己,在冷水带来的清醒中,提醒自己,不要做偏离目标的事情。我的签名,练得也越来越好了。
有好几次,我来到公用电话亭前,拿起电话,想听听家里人的声音。但总是在拿起听筒之后,迅速地把听筒放了回去。我害怕,我害怕我听到家里人的声音会哭,会对他们说:"我要回家。"
我不能回家,虽然我想家。
回了家,我做什么呢?种地,再过两年,娶媳妇,和哥哥争房子?我当初出来的时候,态度那么坚决,说得那么豪情万丈,现在就这样回去?村里人会怎么笑我呢?他们会不会对自己的孩子说:"出去,出去有什么用?你看王宝强,出去了两年,不还是回来了。钱也没挣到。"
我无法容忍自己在他们眼中,是这样的失败者的形象。
但是接下来的路怎么走,我依然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一条黑漆漆的巷子,眼前全是黑暗,全是黑的,看不到光明,一点儿指引都没有,想后退也没有地方后退。巨大的焦躁吞噬着我的心。晚上,我开始失眠。偶尔能入睡时,就似乎回到了小时候,在县城里,夜幕降临,街上空无一人,我找不到母亲,站在街上大声哭泣。
有时醒来,我发现自己在叫"妈妈"。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那个改变我一生的传呼。
日记之七:2000/2/大年初三的深夜,一口气吃了五个馒头
没有戏演,也得找活干啊。跟我住一块的伙伴们和我一起到了一个建筑队。干了一个多月,说好了一个月一百块钱,管吃管住。我什么活都干,大部分时间给人打下手。
可那天在洗手间擦玻璃的时候,是踩着洗脸池子上去的。那个洗脸池子是瓷做的,没安结实,哗的一下就掉下来了。工头过来一看,当时脸就黑了。
月底一结账,把我的钱全扣了,我一分钱也没有了。
大年初一那天,从早起没吃饭,到晚上十二点都没吃饭,饿得实在不行了,快饿死了, 去邻居家敲门,他是卖馒头的,我一口气吃了五个馒头,先赊着账,那时候身上没钱,五个馒头一块钱呢。
我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但我自己想,这是关键时刻,看你能不能顶住。有的人一开始走得很快,再后来,就越来越慢,有的人实在走不动了,就退出去了。但是只要你坚持,顶住一股劲,也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