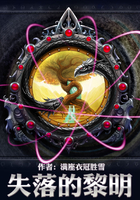对于孙氏在《墨子》一书校勘训诂方面的成就,时人给予极高的评价。俞樾曾经这样写道:“于是瑞安孙诒让仲容乃集诸说之大成,著《墨子间诂》。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整纷剔蠹,脉摘无疑。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替孙氏作传的章太炎亦云:“《墨子》书多古字古言,《经》上下尤难读。《备城门》以下诸篇,非审屈勿能治。始南海邹伯奇比次重差、旁要诸术,转相发明,文义犹诘诎不驯。诒让集众说,下以己意,神旨迥明,文可讽诵。自墨学废二千岁,儒术孤行,至是较著。”而梁启超对《间诂》一书更是无限地推崇:“大抵毕注仅据善本雠正,略释古训;苏氏始大胆刊正错简;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然非承卢、孙、王、苏、俞之后,恐亦未易得此也。仲容于《修身》、《亲士》、《当染》诸篇,能辨其伪,则眼光远出诸家上了。其《附录》及《后语》,考订流别,精密闳括,尤为向来读子书者所未有。盖自此书后,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也。”
值得注意的是,俞、梁诸人对孙著虽如此推崇,但在后来的墨学家们看来却一点也不过分。方授楚说:“俞氏虽誉之如此,盖非溢美。”陈柱亦云:“俞氏之说,诚非溢美之辞。”从这些话来看,孙书在考据学上的价值也就不言自明了。
除了考据之外,孙氏对墨学的评价也有许多新的见解:
(墨子)身丁战国之初,感悕于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谆复深切,务陈古以剀今,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惟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竟摒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务为和同,而自处绝艰苦,持之太过,或流于偏激,而非儒尤乖戾。然周季道术分裂,诸子舛驰,荀卿为齐鲁大师,而其书《非十二子》篇于游夏孟子诸大贤,皆深相排笮,洙泗,儒家已然,墨儒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厥书,释其纰驳,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
孙氏根据儒家内部亦有相互攻击的现象来解释儒墨相非的事实,已与汪中之说无异。他称赞墨子“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可见他对墨子的评价之高。观其后文,一则曰:“墨子立身应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轻相排笮”,再则曰:“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灭,与草木同尽者,殆不知凡几。呜呼悕已!”孙氏之爱墨之心溢于言表。章太炎在传记中说他“行亦大类墨氏”,足可看出墨学对他的影响之深。
从传记中可知,孙氏亦是具有维新思想的人物,生前曾亲手创办或领导创办多所学校,晚年并主温州师范学校,担任浙江教育会长。尽管在政治上他不赞成激进的革命,但从学术上他还是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变革的向往,他推崇墨子无形中构成了对儒学独尊的冲击,其中某些言论足可称作是维新革命的舆论先导。
值得一提的还有孙氏求知的热情和奖掖后进的高尚情怀。在《与梁卓如论墨子书》中,孙氏曾这样写道:
曩读《墨子》书,深爱其撢精道术,操行艰苦,以佛氏等慈之旨,综西土通艺之学,九流汇海,斯为巨脉。徒以《非儒》之论,蒙世大诟,心窃悕之。研校十年,略识旨要,遂就毕本,补缀成注。然经说诸篇,闳谊眇旨,所未窥者尚多。尝谓墨经揭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义,如欧士亚里士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惜今书伪缺,不能尽得其条理。……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复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以执事研综中西,当代魁士,又夙服膺墨学,辄剌一二奉质,觊博一哂耳。……贵乡先达兰甫、特夫两先生,始用天算光重诸学,发挥其旨,惜所论不多。……倘得执事赓续陈邹两先生之绪论,宣究其说,以饷学子,斯亦旷代盛业,非第不佞所望尘拥彗,翘盼无已者也。
《与梁卓如论墨学书》作于1897年,此时孙诒让早已是德高望重的经学大师了,他却还能虚心地学习“近译西书”,并与墨书相互印证,这种求知热情实在不能不令人敬佩。他所提出的《墨经》中有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相近的“微言大义”,实际上首开了三种逻辑相互比较的先河。在具体论证上,后来虽然变得更加精密了,但我们却不能不佩服孙氏眼光之独到。在与梁启超的关系上,孙氏作为一位长者,也显得极为谦逊,这自然会引起梁启超的感激和奋发。梁氏后来追述道:“此书初用活字版印成,承仲容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三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由此书导之。”事实证明,梁启超后来确实不负孙氏的厚望,当他开始用他那常带感情的笔锋,为墨学摇唇鼓舌并最终引起了一场墨学热潮时,人们又一次不得不佩服孙诒让识见之卓越了。
三、民国时期
经过同光时期学者们的努力,墨学逐渐获得公允的评价,很少有人再以异端目之;《墨子》书有了比较完善的版本,人们可以根据原著来把握墨家学说的精髓了,不必再信从什么耳食之言;墨家精神亦得到提倡,一些富有献身精神和救世情怀的志士常常以墨子作为其人格的榜样。所有这些,都为墨学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所以,到了民国时期,思想界和学术界终于出现了盛极一时的“墨学热”。
1.梁启超和胡适
墨学研究至孙诒让而达到一个高峰。栾调甫曾说:“自孙仲容总集清儒校注为《墨子间诂》,全书伪谬疑滞已去泰半。”作为晚清古文经学的殿军,孙氏的研究完全笼罩在汉学的传统之下,汉学为他规定了解决问题的程序和基本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从音韵入手以通文字训诂,并进而求得经典或本文的真实意涵。按照经学史家周予同的意见,孙氏比较独特之处是能够从文字演变史实中推求文字源流。但这只不过是从“由音求义”到“由形求义”的扩展而已,因此并未超出考据学的传统。真正值得人们惊奇的是,孙氏对汉学方法的应用是如此的娴熟以及他个人的识见是如此的卓越,以至于在对《墨子》一书的研究中,他解决了大部分的与文字音韵有关的训诂问题。其结果,在这同一条研究道路上,孙氏留给后人的只不过是拾遗补缺而已。
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孙诒让也并非没有遇到难题。从邹特夫、陈澧的著作中,他了解到《墨经》四篇中包含有天算光重诸学,从与外来名学著作的对勘中,他朦胧地感觉到这几篇中还可能有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相似的“微言大义”,但由于缺乏现代科学和逻辑学等知识的限制,他却无法给这些问题以恰当的说明。由发生在孙氏身上的这种现象可以看出,墨学研究已经到了不得不发生“革命”以便树立一种新的研究传统的时期。树立新的研究传统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便落到了梁启超和胡适身上。
另外,世纪之交的思想界状况亦为墨学的这种“革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西学的传播越来越深入,人们已经有可能利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古代的典籍了;科学的声誉日渐提高,科学主义开始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潮流;逻辑和方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包含有科学和逻辑内容的《墨子》一书自然会受到人们越来越广泛的重视。所以,当梁启超和胡适开始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重新整理和研究《墨子》一书时,学术界竟会出现一呼百应的现象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根据其自述,梁启超幼而好墨,在万木草堂跟随康有为读书时就“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年轻时又得到孙诒让的鼓励,从而开启了他治墨及先秦子书之兴趣。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了一些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眼界逐渐开阔。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认真地研究《墨子》一书。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后合为《墨学微》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墨子思想的著作,它标志着近代墨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后,梁氏在同一课题上继续钻研,并于2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墨子学案》、《墨经校释》两书,前者在《子墨子学说》的基础上对某些问题进行了更深的挖掘,后者则利用现代逻辑和科学专门诠释经说四篇。其他像单篇散论涉及墨子者更多,这里不必一一缕指。
前后算起来,梁氏研读《墨子》垂二十年,出版专著三本,尤可称道的是,梁氏的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汉学传统的制约,开始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方法来阐释墨学,并最先把孙诒让无力进行的中西学术比较付诸实践,这使得梁启超本人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传统的树立者。在梁氏之前,治墨者虽众,但他们大都局限于校勘训诂方面,即使有人希望对墨子思想有所评论,那也只好在短短的序言中略提一二。这既限制了思想的发挥,同样也不利于墨子学说的传播。到了梁启超手里,墨子学说被分解为宗教思想、经济思想、逻辑和科学思想,每一方面都得到了专门的叙述和解释。这样做极大地便利了人们对墨子思想的整体把握,所以,后来论述墨学的人也就大都仿效了梁氏从西方社会科学借鉴来的这种分类模式。与此相联系,梁启超的墨学研究特重比较方法的运用:有中国古代各种哲学流派之间的比较,有中西比较,亦有中印比较。中印比较、中国内部各流派之间的比较且不说,单就中西比较而言,就有各个时期、各个侧面的不同,譬如,在论及墨子的宗教、伦理思想时,梁启超就拿基督教、苏格拉底、康德等做参照:“墨子之天志,乃景教的而非达尔文的也”、“道德和幸福相调和,此墨学之特色也,与泰西之苏格拉底、康德,其学说同一基础者也”。在论及墨子的经济思想时,梁启超想到的是当时西方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墨子之生计学,以劳力为生产独一无二之要素,其根本观念,与今世社会主义所持殆全合”、“墨子是个小基督,从别的方面说,墨子又是个大马克思。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在‘唯物观’的基础上建设出来,墨子的‘唯物观’比马克思还要极端”。在论及墨子的政治思想时,梁启超则把它和西方近代的契约论相提并论:“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泰西民约主义起于霍布士,盛于陆克,而大成于卢梭。墨子之说,则视霍布士为优,而精密不逮陆卢二氏。”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这些言论在当时不但使人耳目一新,而且还能提起人们研究之兴味。后来之治墨者喜欢选择比较一途,可以说多赖梁氏的这一发端之功。
不过,由于西学并非梁氏的特长,所以他的墨西比较就难免有粗疏之嫌:说墨子和康德在伦理问题上有“同一基础”已经失据(墨子主要是一位效果论者,康德则信仰一种坚定的义务论),再把墨子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提并论更属戏论。至于说墨子思想和西方近代契约论的关系,梁氏的说法和事实刚好相反,从墨子的尚同政治中找不到任何民选的痕迹。梁氏的这些缺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知识不足的缘故,这一点到胡适的手中就发生了极大的改观。
和梁启超相比,胡适对西学的了解就深刻多了。留学美国时,胡适曾经师从实用主义大师之一杜威博士,受到了系统的西洋哲学训练。从杜威那里,他学会了用进化、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并且发现,实用主义主要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学术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方法论的完善情况。因此,胡适刻意挖掘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逻辑和方法,以便寻求与西方哲学和科学相嫁接的合适土壤。这样,《墨经》诸篇理所当然地成了他关注的焦点。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和稍后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有关墨经的内容都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些均足以弥补梁启超的不足。从传记中知道,胡适本来也是一个关心政治并对西方民主政体有深刻理解的人,但在讨论墨子的政治思想时,他却不像梁启超那样滥用比较的特权。这很可能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他切实地意识到了墨子政治思想与西方民主政体的天壤之别;第二,他太偏爱方法了,以至于方法占据了他墨学研究的主要注意力。综观胡适的墨学研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首先,第一次用发展的眼光把墨家的思想描述成一个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过程。在胡适之前虽然汪中、孙诒让已经怀疑《墨子》书中掺杂有后学的内容,但果断地把《墨经》诸篇确定为战国晚期名辨思潮正盛时墨家后学作品的却是胡适。尽管胡适用宗教和科学来区分前后期墨家太过夸张,把惠施、公孙龙称为“别墨”混淆了学派间的基本限制,但他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墨家前后期在思想倾向上的差异,意识到墨家后学与名家代表人物之间有相互呼应的痕迹,这已经是不小的成就了。后来由冯友兰提出的受到学术界普遍赞成的前后期之分说到底也只是对胡适意见的进一步完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