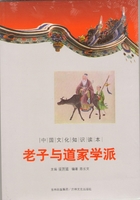自战国迄晚明,惠施一直被当作“辩者”之流,受到批评与轻视。方以智大概是第一个替惠施正名之人。他不但站在惠施的立场上,写下了令“五车吐气”的《惠子与庄子书》,而且径直称惠施为“深明大易”、“欲穷大理”的博物君子。晚近经由西学之“格义”,惠施之说常被纳入“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论域中进行讨论。如果我们不纠缠于“逻辑学”、“自然科学”这些名字的话,此种做法早由方以智开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方氏的这种“孤明先发”自不应湮没无闻。另外,分析密之表彰惠施之学的因由,对于理解方以智自己的思想性格来说,也有其辅助的作用。
一、惠施之说
惠子之书不传,除政治活动屡载于《国策》、《吕览》外,所有思想性的言论皆见于《庄子》一书。由于庄书多属寓言,相关内容是真实的思想实录,还是《庄子》作者有意的设计,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庄书中,惠施经常作为庄子的辩论对手而出场。他们讨论的话题包括“有用无用”(《逍遥游》、《外物》)、“有情无情”(《德充符》)、“鱼之乐”(《秋水》)等等。也有一些对话涉及两人的私交,如“惠子相梁”(《秋水》)、“鼓盆而歌”(《至乐》)、“运斤成风”(《徐无鬼》)等。细读这些对话可以发现,即便是那些比较私人性的话题,也仍然服务于庄子的学说及立场。比如,“鼓盆而歌”的故事,表达的是生命乃一气之化生,正不必为生死而烦恼。“惠子相梁”显示的,则是庄子对政治的厌恶和对权贵的蔑视。那些围绕特定主题的争论,不用说,更是对庄子思想的辩护和宣扬。在这些对话中,惠施只是庄子的陪衬,只是庄子或庄子学派表达自己思想的一个符号或工具而已。因此,要想从这些对话中了解真实的惠施,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儿。
唯一的例外是《天下》篇。此篇的末尾记载了惠施提出的一些论点,并对惠施的学说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尽管《天下》篇是否属于庄子本人的作品,尚有争议,但论者大都同意,它是庄书中仅有的一篇“庄语”。从该篇对其他各家叙述之准确性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对惠施学说介绍的可靠性。下面两段话便是《天下》篇对惠施学说的述与评: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晲,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悲夫!
《天下》篇认为,百家之学是上古道术分裂的结果。诸子各得一偏,是谓“方术”。惠施与众人不同的是,他乃“多方”,所以显得特别驳杂。紧接着,《天下》篇列举了惠施“历物”的十个论点。由于惠施本人的论证不存,这十个论点成了没有答案的谜语,留给了后世解释者们以无穷的想象余地。
第二段话是对惠施学说的评价。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在这段不长的评论中,《天下》篇的作者总共五次提到“物”这个词。用“物”来区分各家,本是《天下》篇的重要线索之一。像墨翟、禽滑釐的“不靡于万物”,宋钘、尹文的“不饰于物”,慎到、田骈、彭蒙的“于物无择”,关尹、老聃的“以物为粗”,庄子的“不傲倪于万物”,都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但如本段这样反复地强调惠施“强于物”(结果大概就是“弱于德”)、“于物也何庸”(对“物”无所裨益)、“散于万物而不厌”(分散心思于万物而不知厌倦)、“逐万物而不反”(追逐万物而不知返),还真不多见。品味《天下》篇的用语,其作者似乎有意要在惠施和其他各家之间做出区分:不管是墨子的“不靡”、宋尹的“不饰”,还是慎到的“无择”、庄子的“不傲”,讲的都是人对物的态度。唯有惠施一人想要了解万物本身。《天下》篇的作者显然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才说惠施的努力有如蚊虻之劳、形影竞走。
在段落的末尾,《天下》篇作者对惠施之才深致惋惜之情,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寓言故事中所描述的惠、庄友谊。我们虽不必因此而仓促得出结论说,此文一定是庄子自己所作,但有一点却是值得特别提及的,那就是《天下篇》作者对惠施的这点惋惜之情,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也几乎成了空谷足音。直到明末清初的方以智,我们才可以再次听到一些同情的回响。
二、历代评论
由于名家久成绝学,后世单独评论惠施学说者并不多见。下面选取的六家是较有代表性的言论。其中,荀子是专门批评惠施的,班固则扩展到整个名家。郭象、林希逸、焦竑的话都出自于他们的《庄子》注。朱熹则是与弟子讨论孟、庄何以互不提及时,顺便提到了惠施。
(1)荀子:“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愚惑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非十二子》)
(2)班固:“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汉书·艺文志》)
(3)郭象:“昔吾未览《庄子》,尝闻论者争夫尺棰连环之意,而皆云庄生之言,遂以庄生为辩者之流。案此篇较评诸子,至于此章则曰‘其道舛驳,其言不中’,乃知道听涂说之伤实也。吾意亦谓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辩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使性不邪淫,不犹贤于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论,以贻好事也。”(《〈庄子·天下〉注》)
(4)林希逸:“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犹为见道之偏者。若惠子则主于好辩而已,故不预道术闻风之列,特于篇末言之。”(《庄子口义》卷十)
(5)朱熹:“如《庄子》书中说惠施、邓析之徒,与夫坚白异同之论历举其说,是甚么学问?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显理?”曰:“便是禅家要如此,凡事须要倒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6)焦竑:“自惠施多方以下,与《列子》载公孙龙诳魏王之语,绝相类,解者多属臆说。范无隠与其门人尝论此云:‘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存而勿论可也。何者?此本非南华语,是其所辟舛驳不中之言,恶用解为?’虽然,凡庄生之所述,岂特墨翟、禽滑釐以来为近于道,即惠施之言,亦有似焉者也。刘辰翁所谓唯爱之,故病之,而不知者以为疾也。毁人以自全也,非庄子也。”(《庄子翼》卷八)
六家之中,荀子离惠施的年代最近。他的批评与《天下》篇的说法有近似之处,如怪诞、好辩等。所不同的是,荀子从儒家立场上指责惠施“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认为其主张不可以作为治国之纲纪;《天下》篇则惋惜惠施不自量力,追逐外物而不知返,结果在内在之德方面有所缺失(弱于德)。
班固的评论中,并没有直接提到惠施。但是,《汉书·艺文志》所列“名家”书目中,收有《惠子》一篇。因此,班固所评论的对象也应该包括惠施在内。班固与荀子一样,恪守儒家的立场。为了贯彻其“诸子出于王官”论,他把名家的起源追溯到了“礼官”。这和荀子“不是礼义”的定位,刚好处于对立的两端。班固的批评,“及譥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则与司马谈的看法一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论六家要旨》)
郭象是魏晋时期解《庄》的代表人物。他在这段评论性的话语中,首先感叹道听途说之伤实,然后给出了自己貌似“公正”的立场:从治国的角度来讲,惠施及辩者之说纯属“无用之谈”;从宣泄情绪、吸引心志的角度来说,辩名析理总比博弈这类活动要好些。郭象本人虽以口若悬河而著称,但他对惠施论列的话题显然并没有什么兴趣,一句“存而不论”,就把它们全部留给了所谓的“好事”之徒。
和郭象相比,南宋林希逸的看法更加简单。他认为惠施不过“主于好辩而已”,根本不足以厕身于道术之列,《天下》篇也只是顺便提及而已。作为林光朝艾轩学派的传人,林希逸的学术谱系可以追溯到北宋的程门。但和程氏的严正立场不同,林氏对佛、道两家的态度要和缓得多。他的《庄子口义》有一大特点,就是经常借用儒、佛的观念来解释庄子的思想。这种做法曾经引起过不少人的非议,譬如憨山德清在他的《观老庄影响论》中就曾表达过强烈的不满。不过,从林氏的这段论述来看,他显然没有把三教会通的观念扩展到惠施的身上。
六家之中,朱子的评价最出人意料。一贯主张“格物致知”的理学宗师,面对惠施的“历物之意”,却得出了不成学问的结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朱子的“格物”说,重心显然不在物理本身。其所谓“即物而穷其理”,所谓“一旦豁然贯通焉”,最后所得不过是德性伦理而已。在这段师徒对话中,朱熹还提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看法,那就是惠施之学近于禅宗,都不过是“凡事倒说”而已。至于如何“倒说”、“倒说”的意义是否相同,朱子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最后一位焦竑是明代心学家,他和大多数阳明后学不同,对于读书考据抱有浓厚的兴趣。引文所出的《庄子翼》就是他所编纂的一部《庄子》集注。之所以知道这段话属于焦竑本人所说,是因为它的前面冠有“笔乘”二字,这和焦氏另外一部书《焦氏笔乘》刚好同名。在这段话中,焦竑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惠施之说与公孙龙诳人之言“指不至”、“物不尽”、“白马非马”等属于同类的东西;第二,范无隐“存而不论”、“恶用解为”的说法太过苛刻,惠施之言“亦有似焉者”。可惜的是,焦氏并未解释惠施之说中哪些内容属于其所谓“似焉者”。
总括六家之说,他们对惠施之学的评论虽小有出入,但大体上还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好辩,怪异,无用,不成学问,不值得认真对待。这其实也是自战国到明末将近两千年间,人们对惠施的一种普遍看法。
三、方以智的观点
中国思想史中,第一次尝试给予惠施之学以同情的理解和积极评价的,始于明末清初的方以智。由于各种原因,方氏著作长期湮没,直到20世纪后半叶,经过侯外庐等学者的表彰,方以智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确立。随着方氏著作的整理,他的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和独特的视野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对惠施的重新评价,也许是其中虽非最重要但却饶有兴味的一个。
方以智对惠施的看法,主要见于《通雅》、《惠子与庄子书》、《药地炮庄》末卷的眉批中。《通雅》是方以智的早年著作,三十岁之前已有成书。由于战乱的影响,该书直到方氏晚年才得以刊刻流通。因为中间续有增补,所以并非全部内容均属早出。《惠子与庄子书》是方以智中年的作品。据文末识语,此文作于顺治九年(42岁),与方氏的另两本书《东西均》和《易余》大致同时。《药地炮庄》乃方氏晚年著作,全书完稿于康熙三年(53岁)前后。这几部不同时期的作品,同时提到惠施,说明方以智对惠施其人其学确实有着持续的关注和思考。
(1)《通雅》提及惠施的主要有两处:一处见于卷首三之《文章薪火》,一处见于卷一的“丁子有尾”条。其中,《文章薪火》的说法是:
老子、杨、墨,皆近孔子前后。自老子正言若反,而惠施交易之。其历物也,大其小、小其大、长其短、短其长、虚其实、实其虚而已。公孙龙遂为隐射钩距之机。皆杨、墨之流也。
此条意思是说,惠施的“历物之意”旨在打破大小、长短、虚实的限制,与老子的“正言若反”相近。到了公孙龙手中,则变成了猜谜、钩索隐情之类的戏法。二人皆属杨墨之流。
在方以智中、晚期作品中,除“杨墨之流”没有提及之外,其他两层意思都曾出现过。由于《文章薪火》是方以智长子方中德所笔录,时间跨度有二十年,所以我们并不能断定此条的准确年代。
“丁子有尾”条的内容如下:
《庄子》末篇言惠施历物之意曰: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此皆言物理变化本无定形定名,自我言之,无所不可耳。
“卵有毛”以下数语,属于通常所谓辩者二十一事。方以智的解释是,它们描述的都是物理变化,物理变化本身无常形、无定名,如何称谓这种变化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结果。这里虽然不是对惠施之说的直接解释,但和过去对名家怪异、无用的批评相比,显然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