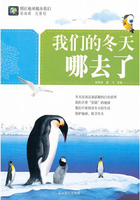从上述引用的一段话来看,学人自然熟悉禅宗的“直指心源”之旨,故其所问则有请泰钦为其直指心源之意,而泰钦的回答是“上来却下去”,显然是运用慧能禅宗“三十六对法”的思想原则来具体针对“学人上来”之语而作出的巧妙回答,其目的在于破除学人之执著。按照慧能之说,与人说法“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而泰钦“上来却下去”之言语,正好体现了禅宗的“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的说法原则。而且,当学人说“法眼一灯分照天下”时,泰钦的回答是“什么处分照”,也展现了禅宗的对法之精神。至于泰钦出世传法之缘由,其本人在上堂时曾有表白:“某甲本欲居山藏拙,养病过时,奈先师有未了底公案,出来与他了却。”这也充分说明他是文益禅师禅学和禅法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并有继承其师弘法利生事业的主观愿望。不过,泰钦的这一言说却引起了南唐国主和学人的种种揣测和疑惑。江南国主曾询问泰钦禅师云:“先师有什么不了底公案?”而泰钦回答说:“见分析次。”在道钦看来,并非有什么不了底之公案问题,而在于人心见分生出偏见、差别。但江南国主似乎并未领会泰钦之语中真意,故江南国主另日再问:“承闻长老于先师有异闻底事。”泰钦遂起身站立,江南国主见其状态则曰:“且座。”由此可见,江南国主对泰钦所言“先师有未了底公案,出来与他了却”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解,因此泰钦对江南国主多次询问此事表现出不满的姿态,尤其是江南国主认为文益有不了底的公案一事的疑问在泰钦心灵深处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泰钦所言的“了却”之意,则是为了表明其本人立志要继续文益禅师的未竟事业,并非是说文益禅师有何参不透的公案。故当有僧人问“如何是先师未了底公案”时,泰钦便打之,并曰:“祖祢不了,殃及儿孙。”可见,泰钦的行为有澄清学人思想之误会的意图。而且,泰钦为了进一步消除学人对先师文益的误解而谓众曰:
先师法席五百众,今只有十数人在诸方为导首。你道莫有错指人路底么?若错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堑。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镬汤,镬汤自消灭。且作么生商量?言语即熟。及问著,便生疏去,何也?只为隔阔多时。上座,但会我什么处去不得。有去不得者,为眼等诸根、色等诸法。诸法且置,上座开眼见什么?所以道: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珍重!
这段话表明了泰钦的思想立场和态度,即不要轻易认为文益所指引的禅悟之路是错误的。所引“先师法席五百众,今只有十数人在诸方为导首”一句,则说明了学道人多,悟道人少这一客观宗教现象,但是文益门徒之中仍有悟道之人,而在各方成为传播禅法的先导,且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而且“法席五百众”的数据也进一步说明了法眼宗传播的繁荣景象。在他看来,修学禅法的关键在于信、愿、行、证,换言之即是要相信善知识的指引,要愿意按照善知识的指引而具体的去实践,要像有向刀山、向镬汤那样向死而生的修学精神和实际行动,所谓“宝所非遥,须且前进”,最后舍去一切法而证入形上之真如境域。
泰钦禅师在传道中,还就如来禅、祖师禅有所涉及。据载:
今汝诸人试说个道理看,是如来禅,祖师禅,还定得么?汝等虽是晚生,须知侥忝我国主,凡所胜地建一道场,所须不阙。
在泰钦看来,如来禅与祖师禅是有区别的,不过,他认为无论是如来禅还是祖师禅都与禅定相关联,故其云“还定得么”,即表明了如来禅与祖师禅在禅定工夫上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关于如来禅与祖师禅的相互关联问题,可参阅洪修平、孙亦平二先生所著的《如来禅》一书,此处不多叙说。
诚然,活跃在金陵的法眼禅师当不限于上述几人,他们都是构成金陵法眼宗群体的重要成员,在弘扬法眼禅宗思想与宗风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囿于篇章而不一一叙及。由于法眼文益禅师及门徒在传禅活动中不断形成了区域性的思想群体,从而共同推动了法眼宗的繁荣与发展。
总体来看,由于金陵弟子多继承文益禅学思想与禅法风格,而将重点落实在禅宗实践上,即重在接引和指导信徒的教学实践环节,故禅师的理论建树并不见长。而禅师就一事一问发表意见,虽存有语言上的分殊,但并未改变禅宗的基本义理以及文益说禅的“清凉家风”之特点。从禅师的活动场域来看,主要集中于金陵清凉院与报恩寺,而这两大寺庙为江南国主所重视的大道场。文益禅师与其弟子长期活跃在金陵一隅,开坛说法,弘扬禅宗,自然能够形成法眼宗一系禅学思想群体,并对江南禅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思想影响和推动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法眼思想的传播与流布。事实表明,法眼宗的禅学思想魅力已经吸引了海外的高丽僧人慧炬等人前来学法,对于中外文化交往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2.法眼宗在江湖区域的思想传播
法眼宗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在江南虽以金陵为中心,但是流布于南方江湖区域的法眼禅派也不容忽视。在法眼宗思想的传布过程中,形成了以江湖区域为中心的南方法眼宗法派群体。
洪州云居山真如院清锡禅师,泉州人,系文益禅师弟子。初在龙须山广平院说法,后居云居山,后又住泉州故乡住泉州西明院。一日,当有一学僧问他:“如何是广平境?”清锡禅师回答道:“识取广平。”学僧又继续追问:“如何是境中人?”③清锡禅师又回答说:“验取。”从中可以看出,清锡禅师的语言方式简单、明快、朴实而又深藏机锋。他针对不同根器的学人所问的同一个问题,其回答是有差别的,即所谓“相身裁缝”、“对症施药”,而不重复。如有一学人问:“如何是镜中人?”清锡禅师则云:“适来向汝道什么?”而非再以“验取”二字作答。清锡禅师对不同学人之问所做出的不同之答,体现了他因材而教、不照抄照搬和不墨守成规的思想理趣。诚然,清锡禅师之答,既是对学僧的方便之答,也凸显了禅宗的活泼之趣和自由任运精神。清锡禅师将法眼禅法思想传入云居,也是对南方禅学世界的一大贡献。
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禅师,先在百丈山从照明禅师出家,后参文益禅师。在文益处有了悟道因缘而获得悟法契机。道常禅师曾问文益曰:“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当其言未说完,就被文益禅师打住云:“住,住!汝拟向世尊良久处会去。”于是道常从此而开悟。在文益看来,开悟不在问,也不在说,而在参悟、领会和体悟,即只有心地契会才能见性觉悟,超凡入圣。由于道常在文益处悟道而名声大振,故其为百丈山僧众请归并担当十一世主持,而使学人前往参学者络绎不绝。道常因参悟、领会而悟道,故其在开示学人的教学过程中,也十分注重这一参悟方法。当有学人问:“释迦与我同参,未审参何人?”道常禅师则说:“唯有同参方得知。”学人又问:“未审此人如何亲近?”道常禅师又回答道:“恁么即不解参也。”在道常看来,既要同参又要解参,不明参之真意,是很难达到开佛知见的,由此也具见道常对参修的态度是极为慎重和认真的。道常的禅法强调“心空”,提出“心空及第归”的主张,而将心空掉视为开悟的条件或基础,体现了其以“空”扫除一切执著之相的禅学意趣。在他看来,心空这即要空掉一切杂念之心、除去一切执著之见,如是才能生出般若智慧,才可洞见禅宗之奥义,以至于体验到超言绝相的禅宗之悟境,所谓“心空得见法王”。而要真正做到空心,必须在心上做工夫,即是要“识心”,识得自我本心,这体现了禅宗“识心见性”的一贯主张和立场。由于道常禅师学修并进,既四处传法,又常居于洪州百丈山,故他对江南洪州一带的禅法则不能不产生影响。
庐山归宗寺法施禅师策真,曹州人,俗姓曹氏,本名慧超。曾参学于清凉文益处而获得开悟。当慧超问文益:“如何是佛?”文益回答道:“汝是慧超。”慧超于是当下开悟,故“从此信入,其语播于诸方”。初住于庐山余家峰,后被请住入归宗寺。他传禅讲究悟入而反对知解,他说:“诸上座!见闻觉知只可一度,只如会了,是见闻觉知,不是见闻觉知?要会么?与诸上座说破了。也待汝悟始得。”在他看来,见闻觉知仍然是一种知识层面的东西,只有领悟了才能内化为生命的存在。参禅悟道中的见闻觉知是不能说破的,而要依赖于自身的解悟和体察,否则不经过自身的体悟和体察所得,一切都犹如空花不实。慧超禅师在参禅悟道的学修与教示中,特别注重对见闻觉知的真实义理进行参悟,当有学人问:“古人以不离见闻为宗,未审和尚以何为宗?”而慧超回答说:“此问甚好。”则一语点破了其重视要对“见闻觉知”进行参悟的见解。慧超禅师的禅风特点与清凉家风一脉相承,既语言质朴平实,又言下暗藏机锋。如有学人问:“如何是佛?”慧超禅师则回答说:“我向汝道,即别有也。”慧超的用意其实很明白,即是说学人要在自己心中求佛而不是向外求佛。这也反映出慧超主张自性自证的禅宗机趣。又有学人问:“如何是归宗境?”慧超答:“是汝见什么?”又问:“如何是境中人?”慧超回曰:“出去。”这两组问答,表面看似答非所问,其实“箭锋相拄,句意合机”。在慧超看来,参禅悟道,既不能执著于归宗境,又不能执著境中人,所谓对待境与人皆不能住相。按照《金刚经》之说的逻辑,所谓境,是境非境是名境;对于人,是人非人是名人。学人问境,境不自在,因人而有,故慧超“是汝见什么”之答,在于破除学人执著于境的常见。学人问境中人,慧超答以“出去”,实为以动显静。可见,慧超与学人的互动对答,既有强烈的禅门接引学人的机锋意识,也彰显了禅宗不可说破的思想精神。
在南方传播法眼禅法的禅师当不限于清锡、道常与慧超三人,而有更多的法眼子弟在南方弘化法眼禅法且影响不小。如法眼门人从显禅师曾一度在洪州观音院传法,并受到袁长史的尊重,在从显归寂后,“袁长使建塔于西山”对其予以妥善安葬。由于清锡、道常与慧超等诸禅师皆长期活跃在江湖一带,对该区域的禅学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换言之,他们既在该区域传播了法眼宗禅派的禅学思想,而又与当地的其他宗派发生一定的思想交融,从而推动了江南禅学的整体发展。
二、法眼宗在吴越的思想传播
法眼宗与吴越佛教有莫大的因缘。无论是金陵禅学中心还是江湖禅学世界,对吴越之地均可能产生思想文化之辐射作用。这与吴越一贯以来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不无关联。《汉书?地理志》云:“吴越与楚接比,数相兼并,故民俗略同。”吴越与楚同属江南区域,由于有共同的地域特征与文化习俗,这为禅宗思想流入吴越提供了条件。又因吴越政治上层极其信奉佛教,则更利于法眼宗思想顺利地传播至吴越。
法眼宗能在吴越广为流传且获得荣耀地位,则与天台德韶国师有极大的关联。德韶是法眼宗的第二代祖师,因吴越国主对其执弟子礼,故被世人尊为“国师”。由于德韶具有法眼宗祖师和吴越国师的双重身份,故他对法眼宗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除了德韶之外,在吴越之地,大力推动玄沙一脉禅法和法眼宗思想传播的还有杭州报恩寺慧明禅师。他是使玄沙正宗兴盛于吴越的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人物。
慧明,俗姓蒋氏。年少出家,精研佛门戒、定、慧三学,立有探玄道之志,故南游闽越,以求开悟。他虽然四处参学,但是“历诸禅会,莫契本心”,未获得悟道之因缘。后来,他到了临川拜见文益禅师,“师资道合”,而获得了悟法的因缘与契机。慧明悟法后离开文益,“寻回鄞水大梅山庵居”,后又迁居天台山白沙卓庵。但是他深感“时吴越部内禅学者虽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阃外”,故有振兴玄沙门庭之主观意愿。他在教授学人时,时常显露出清凉家风。
一日,有二禅客到,师问曰:“上座离什么处?”曰:“都城。”师曰:“上座离都城到此山,则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则心外有法,少则心法不周。说得道理即住,不会即去。”其二禅客不能对。
慧明禅师先以家常话语来询问禅客从何处来,紧接着他引入心法与心外法之讨论来开示禅客,语言十分质朴,但是又暗含用意。但因禅客不解个中,以至于难以作出合适的回答。慧明禅师还针对前来挑战或敌论宗乘的学人提出尖锐性问题进行诘问,使其知难而退。
时有朋彦上座,博学强记,来访师敌论宗乘。师曰:“言多去道远矣。今有事借问,只如从上诸圣及诸先德还有不悟者也无?”朋彦曰:“若是诸圣先德,岂不有悟者哉!”师曰:“一人发真归源,十方虚空悉皆消殒。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殒去?”朋彦不知所措。
朋彦虽有博学强记之能力,但未明佛理,故遇到像慧明这样的明眼人,自然难以抵挡,难免要露出知解的马脚。慧明的第一问,从知识性层面出发作出回答并不为难,但是第二问则非知解就难以回答,它涉及非知识性的佛理层面。对此,朋彦不能作答,更反映出他“夸舌辩如利锋,骋学富如囷积。到此须教寂默,语路难伸。从来记忆言辞,尽是数他珍宝”的禅之通病。慧明敌论宗乘取胜,使其在吴越之地声名鹊起,“自是他宗泛学来者皆服膺矣”,更取得了弘扬禅学与推动法眼宗发展的有利条件。朋彦也“因慧明禅师激发,而归于天台之室,悟正法眼”。慧明不仅在教内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忠懿王钱俶的进一步支持,于“汉乾祐中,吴越忠懿王延入王府问法,命住资崇院”。足见其在政治上受到的尊重和礼遇。
但是,当时吴越佛教“实际上是诸宗并列”,“而吴越的崇佛却是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故这一宗教传统导致法眼宗并未一枝独秀而挺立在吴越之国,并且吴越国主也未将其立为唯一之宗派。各派为争夺发展的空间,势必有一场思想论战即将在法眼宗派与其他诸宗之间进行,而慧明则成为了与各派论战的关键性人物。
师盛谈玄沙宗一大师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极,王因命翠岩令参等诸禅匠及城下名公定其胜负。
可见,论战是因“师盛谈玄沙宗一大师及地藏法眼宗旨”而直接造成。从“王因命翠岩令参等诸禅匠及城下名公定其胜负”的态度来看,也足证法眼宗当时在吴越未取得一枝独秀的宗教地位,而是与其他宗派并列,都为吴越国主所共奉同尊。法眼宗地位的跃升,是在此次论战之后,就此意义而言,慧明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这一场论战是在慧明与天龙禅师、资严长老等吴越禅门与教门名宿之间展开的。而担当裁判的是翠岩令参等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