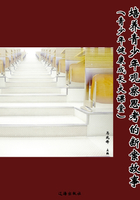“送信的是什么人?”李穆然微微一怔,看着信有些出神。继而,就听冬儿低声道:“表哥,我回去了。你你先吃晚饭。”
她下了床,沿着墙走到门旁,刚伸手去碰门,李穆然便一把拉住她的胳膊。她身子一颤,双眸晶莹看着李穆然,身子更向后贴着墙,微微颤抖。李穆然看她的眼神,不由一阵愧疚:“你吓着你了?”
冬儿垂头道:“等以后以后成亲的时候”她说到最后几字,声如蚊讷,低不可闻。李穆然淡然笑笑,他后悔方才一时情急,更怕以后跟冬儿见面她会一直这么怕自己,心想总该把话题改改,让她别再纠结于此事上,便道:“先不说这些。你今天下午严夫人给你配新丫鬟了吗?”
看他神态跟平时一样,冬儿才放下心来,道:“有。叫做青岚,比我还大三岁呢。据说原本是古姨娘家的远房亲戚,在老家遭了饥荒,逃到建康的。”
“这就是了。”李穆然点了点头,“是大将军的人。这个人和雅淑不一样,你别对她太好。”
冬儿应声道:“我明白,不会什么话都跟她说。”
李穆然又道:“雅淑也是。你要是把她当妹妹,就先教她写字、医术,以后总有用处。但别太惯她,现在我瞧着,她都快成小姐了。”
“哦。”冬儿点了点头,莞尔道,“她今天都快被你吓出病来了,有你在,她也不敢懈怠。”
李穆然笑笑,道:“我真有这么可怕么?我怎么不觉得?你小时候,还不是整天欺负我?”
听他说起小时候的事情,冬儿这才真正放松下来:“那怎么一样呢。小时候你陪我爬树掏鸟窝,跑到姬伯伯的田里偷没长成的人参,在你师父的鞋里倒墨汁要是你成天也板着一张脸,谁高兴和你在一起?”
她说着那些往事,脸上似乎都透出光来。李穆然想起那时两个人在谷中戏弄诸老,虽然每次都以自己被打或者罚跪告终,但还是其乐无穷。昔日的快乐,将他这一天的苦闷一扫而空,他拉着冬儿坐回案旁,道:“你原来还都记得。我以为你那时小,早就都忘了。”
冬儿道:“别说我小。那时那么多鬼主意,有一大半是我想的呢。”
李穆然笑道:“对对对。所以,谁敢说我家冬儿不机灵不聪明呢?”
他又提到这个话题上,冬儿脸色一沉,道:“那是我小时候聪明,长大了变笨了。就拿我们来的这一路说,庾渊骗不过你,可是骗我就一骗一个准。”
李穆然道:“那是你心善,轻信,不是不聪明。你看你戏弄刘风清,不也是把他耍得团团转么?”
冬儿嘴角微扬:“那是他更笨些。”
李穆然道:“才不是。人家也是巢湖堂堂的庶族第一公子,怎么称得上笨?只不过他太狂妄,反而更容易轻信。冬儿,外边的人不像谷里边的师父们,不会永远都对你说真心话。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算盘,你记着,只有我才对你说的都是实话,永远不会骗你,其他人的话,千万不要信。”
冬儿点点头,道:“我记住了,我只信你一个人的。”她见酒菜放在旁边,他还没动,便推到他身前,道:“怎么不吃饭?你不饿么?”
李穆然从中午饭后,一直到晚上都未进粒米,这时早饿得胃里没了知觉,但碍于冬儿的美意,还是夹了几筷子放入口中。冬儿看他将方才那封信也随手放在案上,拿来看过后问道:“是什么人约你?”
李穆然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不过应该是友非敌。多半是大将军留在这儿的暗线。”
冬儿一怔,问道:“会不会是古姨娘?”
“古姨娘?”李穆然忙摇头道,“她怀着身孕,这么晚出来,不怕危险么?”
冬儿道:“万一是陷阱呢。我跟你一起去?”
李穆然道:“不用。这人肯定是严府的。今天我们已经见过了严府上下所有人,没人武功高于我,不必担心。更何况你和我一起去,万一对方起了疑心,反而不好说话。”他看着床头的沙漏,道:“已经快到亥时二刻了,你还是早些回去吧。我准备准备,也该出去了。”
冬儿“嗯”了一声,道:“你小心些。”语罢,回身向门口走去。李穆然看着她的背影,好不容易才抑制住想要将她再拥入怀中的欲望。他看她将门关上,轻轻叹了口气,从怀中取出严府机关图来。他住的这间厢房床下有个密道,直通严府后门外的一间闲空民宅。
严府背靠狮子山,浊浪亭建在山脚下,是个离亭。
李穆然到浊浪亭时,约他的人还没有到。
他走到亭外,仰头看着天空。雨早已停了,天空疏朗无云,只有一轮明月,几点稀星。距离十五已不远,月亮几乎就是圆的,到了午夜,已近中天。李穆然掐算着时辰,想着子时已到,那人怎么还不来,他手上握紧了无名剑,只觉晚风拂面,清冷如斯。
他盯着严府的方向,看到眼睛都酸了,才见严府那民宅旁的一个柴房有人影一动,继而那人影缓缓走来。
“古姨娘?”李穆然见那人身形瘦削,却是大腹便便,大吃一惊,没想到果真被冬儿猜中,慕容垂埋下的这个伏线,竟然拖着六个月的身孕还要来为自己通风报信。
古氏双手撑着腰走入亭中,扶着亭栏倚在美人靠上,道:“领头人,让你久等啦。”
李穆然忙道:“古姨娘,您身子不方便,实在不该这么辛苦自己。倘若出了什么差池,我如何担待得起?”
古氏道:“我没事。更何况,为了贱妾一个人的安危,倘若误了大将军的事,也不是你我能担待得起的。”
李穆然被她义正词严讲得哑口无言,只得点头道:“你说得是。你约我来,究竟是要说什么?为什么大将军给我的名单里并没有你?”
古氏淡笑一声,道:“那是因为我不中用。如果我能有石氏一半厉害,大将军也不会想方设法,这次的领头人一定要安排自己人了。”
“怎么?石氏欺负你么?”李穆然听她说着说着就拐到了严府的家长里短上,有些无奈,暗忖石氏比古氏貌美百倍,若非古氏有桓氏的关系,只怕根本轮不到她来建康。既然姿色平庸,严国英厚彼薄此,也在情理之中。
古氏道:“也算不得欺负。不过领头人也瞧见了,石氏能言巧辩,美貌无俦。据我在旁观瞧,只怕我家老爷,已与姚苌同流合污,连带着乔氏也是一样。”
“哦?”李穆然倒不信石氏对严国英的枕边风竟大到如此,严国英是细作中的精锐,怎么会被区区一名妾侍影响?更何况严国英绝不是傻子,怎会不明白石氏的出身。他斜睨了古氏一眼,道:“乔氏精于机关我知道。可是,你会什么,石氏又会什么,能告诉我么?”
古氏回道:“领头人不必如此客气,您但有所问,贱妾定然言之不尽。我在严家,最大的用途就是我的身份。桓氏的远亲,虽然出了五服,但也算士族,平常出去和老爷朋友的女眷们在一起,大家也还肯给我些面子。”
李穆然点了点头,暗思古氏所言和自己之前的猜想大致相同。在那些士族贵妇眼中,乔氏就算有正妻的身份,也及不上古氏的血脉尊贵。至于石氏,她们只怕都不屑看她。
古氏续道:“石氏她精于易容,擅长歌舞。她平时不常在府中,甚至我猜,她也不常在建康。她交友遍天下,但但都是倚红偎翠之处的那种女人。”
“这倒也是来消息的好地方。”李穆然微一簇眉,“你是说,她以前是青楼出身?”
古氏说话有些吞吞吐吐,似是有难言之隐。李穆然看她话未说完,便催问道:“还有什么?”
那古氏被他一,才说了出口:“她她精于媚术。”
“哦。”李穆然想想石氏的姿容形态,不觉笑道,“这也难怪。古姨娘,你怎么知道严国英心向姚苌,可有证据?”
古氏道:“证据没有让我抓到,可是很多事,却肯定是我家老爷做的。您来之前,正月里我们得了个消息,说朝廷有意提拔一批庶族子弟入朝为官。”
“等等,‘我们’是何人?”李穆然问道。
古氏道:“是大将军安排在晋国的细作。”
李穆然道:“消息传进长安没有?”
古氏摇头:“就是此事蹊跷。派出的报信之人,不是暴毙就是失踪,后来无人敢去。我家老爷向来对长安是只报喜不报忧,朝廷提拔庶族子弟,对他之前所言不利,因此定然是他下的手。这消息,姚苌的人应该也知道,但却无人回报。两相比较,自然能看出他和姚苌暗中勾结。”
“原来如此。”李穆然陷入了沉思,报信之人不是暴毙就是失踪,那么严国英除了和姚苌勾结之外,慕容垂派在晋国的细作之中,定然出了内奸。他目光灼灼,看向古氏:“我记得,大将军派在晋国的细作之中,有位当铺老板,叫做钱无咎,是专门负责联络的。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古氏道:“我们一开始也怀疑他走漏了风声。可是看了这三个月,他还是和以往一样,并没有背叛之举。”
“我知道了。”李穆然微一点头,“古姨娘,还有其他事么?这里夜凉风大,你也该早些回去休息。”
古氏道:“倒也没什么事,只是您要小心我家老爷会对付您。”
李穆然暗暗好笑,这位古姨娘的消息灵通还不如冬儿,还不知道严国英早就开始对付起自己了。他一笑:“我明白,多谢。”
古氏一福,起身欲行,可是到了亭边,又似乎想起一事,回过身来,道:“领头人,有件事按说不该贱妾来讲,可是可是我和那位佟姑娘很是投缘所以,请您恕贱妾多嘴吧。”
李穆然听是和冬儿有关,想起方才两人在房中拥吻,多半都被这位古氏瞧在眼里,不免脸上一烫,道:“什么事?”
古氏黯然道:“当了细作之后,您的一举一动,便不能再随心所欲,只要有一日朝中不发话,您就有一日不能回去。如果时间长了,便和我家老爷一样,在这儿安下家来,娶妻生子。”
李穆然道:“我都明白。如果我在此常驻,我会说服她留下来,嫁给我。”
古氏摇头道:“恕贱妾直言,您不明白。您若真心喜欢佟姑娘,便不该让她嫁给您。”
李穆然一蹙眉,问道:“为什么?巢湖李家,二位老人家做了一辈子细作,不也是相亲相爱的?”
古氏道:“巢湖李老他们并非一开始便如此,也是多年相处,才日久生情。更何况李夫人生下女儿后,大病一场,从此便再不能生育。”
李穆然更是不解,问道:“这又有什么关系?”
古氏道:“领头人,您有没有想过,要是以后有了孩子,您希望他做什么?他如果留在您身边,会不会成为您的把柄?”
李穆然一顿,他绝顶聪明,一听便明白古氏所虑:“那严国英他之前有过子嗣,只是不在严府?”
古氏道:“对。我嫁到严府来,不过九年,但也听乔氏提起过。细作的孩子只有两个选择,如果希望孩子留在身边,以后也就必须成为细作;否则就要抱走,交到普通家庭之中抚养长大,但父母此后一生难再见。我家老爷是聪明人,便都是选了后者。乔氏曾有一儿一女,在五岁之前,皆被送走,对外便说是暴毙。”
“暴毙?这么说李家的女儿”李穆然猛地想起了自己那个从未谋面的“姐姐”,难道并没有死,而是送到了别人家中么?
古氏道:“是的,也是被送走了。乔氏忍不住骨肉分离之苦,在女儿被送走之后,曾经寻过短见,只是被救了下来。我家老爷是个绝情无义之人,见不惯乔氏整日哭哭啼啼,此后连细作的事务也不肯让她插手,在家中更是待她甚为凉薄。否则,也不会纳我为妾。领头人,您若是真心喜欢佟姑娘,难道忍心看她受此苦楚?更何况,依我看佟姑娘是柔弱的性子,她断断禁不住这种打击。”
李穆然一怔,靠着亭柱,默然不语。古氏所言虽然八字还没有一撇,但他还是不禁有些担心。的确,自己见冬儿落泪都会受不了,如果看她痛不欲生,那自己又该怎么办。恍惚间,他有些明白严国英为什么会报喜不报忧,只要秦晋交战,他就有机会能够回到秦国,不用再当这个细作。他想起临行之时,慕容垂曾对自己讲过,短则三年,长则五年,秦晋之间必有大仗;他又想起遵善寺那个住持房中,苻坚曾对自己允诺,待自己功满归国,便是一军之将,倘若真的是过了二十年再回去,这句承诺岂不成了一句笑话。
“也罢,就赌一把。最长五年,两国开战。”李穆然心中有了计较,看向古氏,见她是真心关怀冬儿,不免也对她客气了许多:“古姨娘,多谢你。那你这个孩子,以后也是要送走?”
古氏凄然一笑:“是啊,我也不知能养他多少日子。”
李穆然不知该如何劝慰她,长叹口气,道:“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提。别想这么多,说不定以后事有转机。”
古氏点头道:“但愿如此吧。”语罢,又是一福,沿着原路,已缓缓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