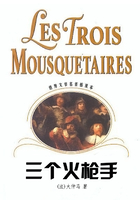金陵一役,让崎岛国军队遭到始料不及的重挫,损失了将近三个主力师团的兵力。崎岛国国土狭小,兵源有限,在沪城之战增派了三次援军之后,已经很难在短时间内募集大批援军。崎岛国原本的计划是:集中人力、火力,以最快的速度占领沪城和金陵。利用南宗仪在金陵的势力建立伪政府,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在中国本土征集军队,让中国人自己人打自己人。出乎崎岛国人意料的是,他们坐收渔利的美梦竟然在金陵一战化为泡影。
在崎岛国败军退守沪城的当口,瞿正朴从平京总指挥部紧急调动多方军队围攻沪城,同时使用飞机、把瞿军一个军的精锐部队空运到沪城战场。瞿东风一面亲自赴前线督导作战,一面充分发挥城内群众的力量、在沪城内部不断扰乱敌人。人海战术,里应外合,沪城争夺战又将从金陵败退的敌军狠狠打击了一通,让敌人付出了2万余人的伤亡代价!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的战斗中,崎岛国军队越来越明显地显出劣势。因为在中国战场的节节失利,崎岛国内的左翼逐渐在国会占据主动地位,主张撤军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金陵的春天就在出征的号角、和一声声的捷报里,匆匆地过去了。
一夜枕上听雨。清晨醒来的时候,推窗望去,雨已经停下来。
罗卿卿用过早饭,照例在花园里慢慢地散步。医官说预产期就在这几天,多散散步,可以增加产力。
已经是春花红褪的初夏,却看见一片片火红的鲜花正开得热闹。分列在甬道两侧,枝丫交叠,花红叶绿,宛然架起一座红霞流漾的天然门楼。
她走到近前去看,果然是石榴花开了。
南天明从甬道的另一头走过来。
她便高声问道:“天明,能不能告诉我咏石榴花的诗。”
南天明随口诵出一句:“却是石榴知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
“年年此日一花……开。”她笑着重复着,眉头却皱起来。
南天明道:“怎么了?是不是……”
她感觉到下腹这次不是酸痛,而是阵阵发紧的疼痛。医官说阵痛是分娩的前奏。她忍不住紧张起来,下意识地抓住天明的手。
南天明把卿卿送回房间,小心翼翼地把她扶到床上。看到卿卿紧皱着眉头问副官道:“司令……什么时候能回来?”
“军部刚有消息说,司令亲自督战,已把敌人逼到淞江县城。多久能打下松江县城,那可难说了。夫人,要不要我给司令挂个电话?”
“不……不用了。”罗卿卿急忙制止住副官,“我很好,不要让他分神。”
即便卿卿强作坚强,南天明还是一眼看出她眼里的委屈。她疼得浑身发抖,额头滋出冷汗。他一时失神,想抚摸她的额头。手伸出去,马上清醒过来,手指缩紧、攥成拳头。突然心里一阵落寞的伤感。他在自己的额头上击打了一拳。怎么在这个时候为自己伤感起来?她越痛苦,他才必须保持清醒。一个为自己悲哀的人,如何照顾别人?
他忍住内心的抽搐,对她说道:“不要害怕。即便瞿司令不在,还有我……很多人都在你身边,我们都会守护你。”
淞江南岸,前敌指挥部。
天色完全黑下来。天上浓云滚动,江岸两边的田亩和疏落的村屋都隐没在黑暗里。松江县城外,参战各部已开始了总攻前的最后准备。前敌指挥部内外灯火通明。人员川流不息,呈现出一派大战前的紧张景象。相对于紧锣密鼓的屋外,指挥室内倒是显得十分安静。
瞿东风和十几名高层指挥员围在沙盘模型前,看着作战参谋在沙盘上最后标定敌我双方的态势。瞿东风目光沉定,很少说话。只在有人主动向他请示意见时,他才跟对方轻声交谈几句。
崔炯明走进指挥室,屋内的肃静让他不由自主放轻了脚步。他走到瞿东风身边,怕打断司令思考问题,没敢立刻开口。
瞿东风看了眼崔炯明,问道:“怎么样?”
崔炯明低声回复道:“夫人顺利生产,是公子。”
瞿东风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目光转回沙盘,看着作战参谋把象征联军三路大军的旗子插在了敌军的心脏位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离总攻时间越来越近,屋外的参战部队越来越紧张的等待着攻击的命令。指挥室内更加安静了。没有人说话,甚至连粗重一些的呼吸也听不到。整个指挥部处在一片战前肃静的等待里。终于,瞿东风从红木椅里站起身,走向电话机。整个房间,只能听到他脚上的军靴、在地板上踩踏出的有力的声响。他拿起电话筒,对着电话发布命令道:“我命令,总攻、现在开始。”
瞿东风话音落后,三颗红色信号弹立即升上夜空,好像在夜幕上刺出三道血口。指挥部东北部立刻传来炮兵部队向选定目标的炮击声。隆隆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向着敌人发出了死亡的宣判。数分钟炮击完成后,响亮的冲锋号响彻淞江沿岸。各路攻击部队向淞江城发起了总冲锋。
指挥部内,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起激动的表情。
瞿东风这时候才回过头,对崔炯明道:“告诉夫人,打完这一仗,我立刻去看她和孩子。”
从淞江县战场传来捷报、已是十天之后。
“夫人。”副官走进来,“司令打来电话,问您现在的身体可能接电话。”
罗卿卿急忙道:“我可以。”
副官出去后,不多时,卧室床头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罗卿卿拿起电话,“喂”了一声。电话的另一端终于传来让她牵挂了半个月的声音:“卿卿,你好吗?”
“我很好。孩子也好。”
瞿东风顿了一下,道,“卿,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她打断他:“你有什么错呢。以为我还是任性的小孩子,要你这样哄吗?”
他长长吐了口气:“不管怎么说,这回是我欠了你和孩子。回去之后,一定尽心补偿。”
她笑了下,眼里噙了泪光:“你率部在前方苦战,就是在保护我们母子。还说什么亏欠。”
他沉默了片刻。虽然两人之间隔了将近千里的路程,这时候,都有一种错觉,好像近在咫尺,贴得那样近切,几乎能听见对方的呼吸,感受到彼此那种熟悉的气息。
他的话声终于打破沉默:“孩子什么样?象我,还是象你?”
她笑道:“自然象妈妈。”
他也笑道:“男孩子,还是应该象我。”
“我可不想他象你,那样英雄气尚。我只要他平安快乐,做个平凡人就好。”
“看看,还说不怪我。借着儿子,在埋怨我呢。我一定争取这两天就回去。当面请罪。”
“前方战事比什么都重要,你不用牵挂我们。”
他忽然放低声音道:“实是思念难耐。”
这时似乎有人走过来,瞿东风在电话那头道:“有要务处理。只能说到这里了。代我亲亲儿子。”
放下话筒,罗卿卿让奶妈把孩子抱过来。抱着熟睡的孩子,她低下头、在孩子粉嫩的小脸上亲了亲。东风越说要回来,她越觉得寂寞更加难以忍受。她把孩子抱近自己,用脸颊轻轻的贴着他的小脸。直到这时候,才宛然在坚硬的生活里,感受到一种贴心的柔软。
一直在内心深处苦苦追求人生的完美。在千疮百孔的现实里、一直觉得自己在隐忍,在逆受。直到走至此时此刻,才总算从自己的世界里完全走了出来,想对充满残缺的生活,真心真意地说一声:感恩。
是的,感恩。生活其实已给了她太多。这个臂弯的小生命,就是一件最完美的、命运的馈赠。
抱着怀里的孩子,看着这个完美无瑕的小生命,她已不敢、也不该再因为那些虚无的奢求,对生活生出毫无意义的埋怨。她只能更无怨无悔,更坚实地走下去,真正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生活厚赐的幸福。
瞿东风放下电话,看向走进来的崔炯明。
崔炯明道:“报告司令,我已查实过,俘虏的女特务的确是赵京梅。”
瞿东风双手放在桌面、十指交叉在一处,沉默了一会儿:“当初因为大哥出面跟我要人,我才把她给放了。她居然变本加厉,通敌叛国。如此咎由自取,谁也没有办法救她。告诉军法处,按律处理。”
“司令……”崔炯明上前一步,“赵京梅正怀着身孕。她说是大公子的骨肉。”
崔炯明说完,努力观察瞿东风的脸色。以他一向对瞿东风的了解,即便赵京梅怀着身子,恐怕也难逃军法处置,何况这是大公子的孩子,他更揣测不到瞿东风会作何处置。
瞿东风道:“把赵京梅通敌的证据拿给我。”
审讯室外,两条狼狗把守着大门。铁门内摆放着各式刑具。滚热的铁炉上、烧红的烙铁泛着暗红色的幽光,空气里弥散着审讯室里特有的皮肉烧焦的糊味。
“说,你都打探到什么情报?告诉给什么人?快说!”审讯员厉声喝问的声音在房间里回响。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是个中国人。是个怀了孩子的女人。孩子的爸爸是你们第五军军长瞿东山。就算当不了瞿家少奶奶,我也能母以子贵。我没有道理给崎岛国人卖命啊。”赵京梅理直气壮道。
“哼,赵京梅你真会演戏。瞿军长已经过世,你非说这孩子是他的。你怎么不敢找个活人给你孩子当爹,当面对质?”
赵京梅口气冷静道:“我跟瞿军长的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们大可以到军部去调查,看看是我在演戏,还是你在冤枉我!”
门口响起犬吠,士兵打开审讯室铁门、分列两边,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司令!”审讯员看到来人,急忙起身,身体笔直,立正行了个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