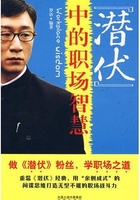对于“草头蒋”主动抛过来的“绣球”,王亚樵觉得十分好笑。去年秋天,“草头蒋”尚未与他撕破脸皮,曾派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政府保安处处长杨虎,以老乡的名义宴请他,并动员他投靠蒋介石。
杨虎说:“九哥,委员长久闻你的大名,准备重用你,赏你个中将军衔,怎么样啊?”
王亚樵冷冷地回答:“是吗?我的身价只值一个中将?”
“九哥,我军现在最高的军衔就是上将。这个中将已经不算小了。”
王亚樵看看在座的老乡柏文蔚、常恒芳、李国凤,抓起一个尖椒,在碟子里蘸了蘸,咬了一口,说:“什么中将、上将,我看都比不上这碟子大酱!”
“九哥!”杨虎忽地站起身来。他本身就是一名虎将,身高一米九,在上海滩与“三大亨”是拜把兄弟,又手握重兵,被人称作“土皇帝”,没想到王亚樵这么不给他面子,当着诸位老乡的面让他跌份。
“你不要不识抬举!”
“什么,你说老子不识抬举?”王亚樵正好被辣椒辣得嘴巴冒火,一看到杨虎这么嚣张,他按捺不住,突然机灵得像一只猴子,纵身跃上椅子,照准杨虎就是一耳光。
杨虎没有想到,只有一米六的王亚樵,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气得一把掀翻桌子,伸手就掏手枪。柏文蔚、常恒芳、李国凤见势不好,有的抱住杨虎,有的赶紧把王亚樵往门外推。王亚樵边走边骂:“士为知己者死。他‘草头蒋’一手遮天,祸国殃民,你要当他的走狗你去当,老子不愿意伺候!”
而今,蒋介石学乖了,又做出让步,叫王亚樵自己提“和解”条件。王亚樵与王亚瑛反复商议,决定“将他一军”。
半个月后,戴笠通过常恒芳给王亚樵回话:委员长“照单全收”,答应王亚樵的“和解”条件:凡是因王亚樵关系而被判刑或者关押的人员,一律无罪释放,并保证他们今后的生命安全;提供100万元遣散费,让王亚樵自行解散暗杀组织。但是,戴笠特意嘱咐:“为了证明九哥的诚意,委员长指示,让他向西南派先打一枪,随便拿谁开刀都行。”
王亚樵听后,冷冷一笑,带着蔑视的口气说:“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草头蒋’再怎么大富大贵、大权独揽,也改变不了他那出尔反尔、投机取巧的流氓本性。我即使沦落到一文不名、穷困潦倒,也是个重情讲义、言行一致的贵族。贵族与流氓,有什么好谈的?!”
不久,一次震惊全国的暗杀,进一步擦亮了王亚樵的双眼,让其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凶狠面目。
杨杏佛,又名杨铨。1893年5月4日生于江西清江。1911年参加同盟会,被誉为“青年才俊”。1918年,在美国获得商学博士学位,返回中国。
1927年8月,在《现代评论》上,他发表了《牺牲与堕落》,抒发了自己追求自由民主的情怀:
人们,你苦黑暗吗?
请你以身作烛,
用自己膏血换来的,
方是真正光明之福。
1932年12月29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鲁迅被推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杨杏佛担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在一次集会上,杨杏佛不无感慨地说:“争取民权的保障是18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20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18世纪的工作。”成立之后,中国民盟多次发表声明,批评、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非常恼怒,但对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同盟会元老蔡元培不便动手,只好退而求其次,命令戴笠干掉杨杏佛,杀一儆百。
当时,杨杏佛借住在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1933年6月17日早晨,军统特务在中研院附近潜伏,准备等他晨练时下手。可是,正当杨杏佛进入他们的射程时,一辆法租界的巡逻车刚巧从他身边驶过;等他往回跑,再次进入伏击区时,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从那里通过。特务们眼看着杨杏佛轻轻松松地跑进中研院,只能干瞪眼。
第二天,他们索性就在中研院大门外待命。那是个星期天,大门外行人稀少。约8时许,杨杏佛身穿骑马装,头戴灰色呢帽,与14岁的儿子杨小佛缓步走出,钻进停靠在门前的轿车,准备出行。就在轿车发动之时,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猛地冲了过去,用手枪朝车内一顿乱射。杨杏佛爱子心切,立即伏在儿子的身上,身中数弹。得手后,特务们按照事先预案,迅速奔向猫在一旁的接应轿车,而过得诚忙中出错,跑错了方向;等他反应过来,朝着接应车跑去时,接应轿车不但不停下来,反而朝他开枪射击,企图杀人灭口;过得诚没有办法,只得东一头、西一头地乱窜,被闻讯赶来的巡捕们围在路中央,绝望中,他不得不赏给了自己一颗“花生米”……
6月20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沈钧儒等人,不顾个人安危,前往万国殡仪馆,参加追悼大会。蔡元培失声痛哭:“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同人等当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后辈青年学子有所遵循,所以慰先生者如此而已。”
王亚樵与杨杏佛情同手足。从报纸上看见他遇害的消息,王亚樵先哭后笑,对妻子王亚瑛说:“‘草头蒋’不愧为一代奸雄,阳奉阴违。杨先生不过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他都不能容忍。我手下有数百名精兵强将,他岂能轻易放过我?宋江当年一时糊涂,本以为招安之后,他的弟兄们能过上安稳日子,结果却是被派去平田虎、打王庆、剿方腊,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后来,一壶‘御酒’,让他们全军覆没。孙美瑶也吃过这个亏。‘草头蒋’以为我是宋江、孙美瑶?”
王亚樵掏出手绢擦了把眼泪,接着说:“‘草头蒋’要我向西南派打一枪,表面上,他是想试探我的诚意,要我按照江湖规矩向他献一份‘投名状’,实际上,却暗藏杀机。如果我上了他的当,稀里糊涂地开了这一枪,就会陷入不仁不义境地,声名扫地;而且,从此失去反蒋同盟,成为孤家寡人。到时候,我为鱼肉,他为刀俎,他想怎么收拾我,就怎么收拾我。……真是痴心妄想!”
经过一番思量,他决定暂时不给戴笠回话,作为缓兵之计;他请常先生赶快想办法,帮助他离开上海,与“草头蒋”再摆战场。他知道,自己的照片早已被特务们掌握。为了不被特务辨认出来,他煞费心机,让妻子用烟头和香火,帮他在脸上烙出大大小小的浅麻子。王亚瑛眼含热泪,不愿下手。王亚樵劝道:“老婆,难道我长了几个麻子,你就嫌弃了不成?”王亚瑛还是下不去手。王亚樵火啦,大声吼道:“是脸面重要,还是性命重要?!”王亚瑛深知他的牛脾气,不得不背过脸,将烟头和香火扎进他的脸,王亚樵被烫得满脸冒烟,他嘴里咬着毛巾,声嘶力竭地大喊:“痛快啊!痛快!”等伤口长好后,他又用酱油涂脸,在阳台上暴晒多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