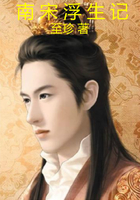在中国古代,《洛阳伽蓝记》是历史名著、文学名著,也是一部文化名著。作者杨衒之以其开阔深邃的目光、真切丰富的情韵、清朗的文字,记录了元魏后期佛教的兴衰、王朝的兴衰以及洛阳的风土人情。他巧妙地以佛寺为叙事、写人、记物的中心和线索,由寺记事,因寺写人,借寺状物,在叙写人、事、物上都表现了卓越的叙述技巧,从而深沉含蓄地用文字记录了那已远逝的元魏王朝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
《洛阳伽蓝记》描绘了元魏人物众生相,依其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不同,大体有四类人物群像:皇室者、仕宦者、僧尼、庶民。其中"有明确姓名者共得147人",为人们展现出栩栩如生的人物长廊,几乎指向元魏社会的各阶层人物。分析这些人物形象,研究作者高超的叙事写人技巧及其文学成就,进而体会这部名著所蕴涵的丰富文化趣味,是系统研究《洛阳伽蓝记》的一项基础而重要的子课题。
一、《洛阳伽蓝记》对两类庶民形象的刻画及其文学
特色这里的庶民是广义的,因其沉潜民间底层而与皇室者、仕宦者分别开来,以其生活在尘俗而与僧尼相区别。
《洛阳伽蓝记》的庶民大体分两类:一类是有名有姓、单独出场的,作品对其刻画有详有略;另一类无名姓,多以群像方式出场,往往成为一种背景式人物群像。
第一类人物有:士兵李苗(卷一永宁寺)、骆子渊(卷三秦太上公寺)、隐士赵逸(五次出场:卷一昭仪尼寺,卷二龙华寺、景兴尼寺、秦太上君寺,卷四宝光寺),死而复活的崔涵(卷三菩提寺);介于文士与庶民之间,可称为民间文士的姜质(卷二正始寺),酿酒者刘白堕、商贾刘宝(卷四法云寺),屠匠刘胡兄弟四人(卷二景宁寺),民间音乐人田僧超(卷四法云寺),婢妾类形象徐月华(卷三高阳王寺)、朝云(卷四开善寺)、春风(卷五凝玄寺),三组夫妇形象:挽歌郎孙岩及其狐妻(卷四法云寺)、韦英与其梁氏妻、侯庆与其马氏妻(卷四开善寺)。合二十余人,有士兵、隐士、民间文士、酿酒者、屠匠、挽歌郎、商贾、民间音乐人、婢妾和职业不明者。
第二类人物出场大约有七次(不包括卷五宋云、惠生出使西域中的人事),以群像方式出场,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佛教节日,如四月初八"佛诞日",有"行像"仪式,伴随有众多民间娱乐活动,如卷一长秋寺、卷二宗圣寺、卷三景明寺;又如佛教六斋日(每月初八、十四、十五为佛教持斋修福日),见卷一景林寺。二是记叙一些灾异凶兆,人群作为现场目睹者,后面往往紧接着叙述王朝变故、社会动乱等,如卷一永宁寺浮图被焚,卷二愿会寺神桑被伐,卷二平等寺金像三度"佛汗"等,作者以婉细近乎琐碎的笔触写奇幻荒唐之事,却暗示出元魏晚期的政治腐败、上流社会的纷争,写出了民间张皇的社会氛围和百姓恐惧的心态,流露作者对昔盛今衰的浓烈感怀。诚如曹道衡所言:"写佛寺的盛衰,以哀悼北魏之亡。"
杨衒之能充分吸纳古今文史著作在人物刻画上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和丰富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洛阳伽蓝记》与《魏书》一道,在北朝文史著作刻画人物上可谓有集大成的地位。
(一)《洛阳伽蓝记》刻画庶民群像,兼具史传文学尤其是杂传、志怪志人小说之优长,呈现文备众体的特色
古代史传文学厚重严谨,将史家的情意寄寓在字里行间,关注王朝兴废、社会变迁、民生疾苦,而杂传文学则关注各类普通人物,取材自由灵活,大可写社会大背景和人的一生,小可写社会一场景、人物一生的某一片断。
卷四法云寺:"周回八里"的洛阳大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有"善吹笳"的民间艺人田僧超,又引出田的"知音"--征西将军崔延伯。作者把一代民间艺人与一代名将绾连在一起,把看似琐细的笛声与军国命运关联起来,使行文兼具正统史传和杂传写法:作者以厚重严谨笔法叙写崔将军领兵平暴的时代背景、朝野送行的庄严盛大场面。用白描写崔"危冠长剑耀武于前",田"吹《壮士》笛曲于后,闻之者懦夫成勇,剑客思奋",又补叙崔将军"为国展力二十余年,攻无全城,战无横阵",这一切又都与田氏笛声壮军威、振士气分不开。最后写田氏阵亡,很快崔将军也阵亡,军败。叙述厚重严谨,叙写军国大事和一代名将。本篇又可视为一微型杂传,选一普通小人物,撷取出征这一画面,在对比中写成败,把笛声与军国命运关联在一块儿,兼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对比写法,读来厚重又轻盈。
六朝志怪写奇幻的人事,情节曲折,想象奇诡,给人诡谲风趣的兴味儿。卷四法云寺即有这样一则志怪小品,洛阳大市北"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尾长三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初变为妇人,衣服靓妆,行于道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文中屡设悬念:孙妻为何不脱衣而卧?孙妻去时为何截岩发而去(是为纪念,为抒幽怨,还是恶作剧)?洛阳男子被截发何以达百多号人?作者在叙洛阳男子时又兼用倒叙,娓娓道来,一一揭明真相,以此强烈吸引读者。作品以写实手法记怪异人事,既写出狐女的怪诞妖媚、有些调皮习气,又讽刺市井男子的荒唐不本分,见出洛阳市井风情和时人对狐又爱又怕的情态。崇拜狐狸,古已有之,因北朝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氛围,狐狸的仙化也加快了进程,借此我们似可管窥到丰富的文化意味。
六朝志人小说,往往撷取社会中一小场景,选取人生一片断,抓住最有特征的片言只语和一举一动,小中见大,以深入展现个性和内心世界;再加上志人小说手法灵活,篇什多短小玲珑,能多角度写人。卷四法云寺写刘白堕"善能酿酒",先叙其所酿酒,酒味盛夏不变,"饮之醉而经月不醒",为下文埋下伏笔;再叙京都以酒赠人的风习,点明"鹤酒、骑驴酒"二名的由来;最后讲一精彩又琐碎的小故事,"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贼盗,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日:'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全文紧扣刘氏"善能酿酒"来写,把正面叙写与侧面虚写相结合,人、事看去琐细,却鲜明彰显刘氏技艺的高超,与《庄子》写众多民间工匠异曲同工,有着经济史、民俗、名物乃至社会生活史多方面的意义。无独有偶,《水经注》卷四河水条亦记刘氏其人,但二者在写法和趣味上却迥异。
(二)多种写人技法集于一书,手法活泼多变
《洛阳伽蓝记》对庶民刻画,注重正面刻画:直接写人物的肖像、言行和神态,重白描和细节描写。卷三菩提寺有一志怪小品,记死去十二年又复活的崔涵。僧人发冢得崔,崔说人间亲人和死后在地底的生活。官府派人去核实,崔涵父母先承认有这样一子,后又惧祸否认。崔至家门,父"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谓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无殃'"。用白描"把桃枝"以驱鬼的细节描写、语言描写,表现家人惶恐冷酷。后崔飘泊京都,"性畏日,不敢仰视,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属,常走于逵路,遇疲则止,不徐行也",写其有家不得归的可怜悲凄。后写市北奉终里"多卖送死人之具及诸棺",崔言"作柏木棺,勿以桑木为欀","吾在地下见人发鬼兵,有一鬼诉称:'是柏棺,应免。'主兵吏日:'尔虽柏棺,桑木为欀,遂不免。'京师闻此,柏木踊贵。人疑卖棺者货涵发此言也"。可见民间棺商欲借重鬼言为营销之策,折射商贾的智慧或狡诈,所叙人事荒唐怪诞,但蕴涵的情味却真实而丰富,有荒诞,有父母的惊恐冷酷,有崔飘泊的悲凄、商贾的奸猾。情节曲折,手法多样,读来妙趣横生。
《洛阳伽蓝记》亦多侧面虚写烘托,有借景物、场面、气氛来写人的,也有借他人他事来对比烘托的。
卷一永宁寺,先描述永宁寺九级浮图的高大华丽,暗示王朝和佛事的昌盛,中间以史家笔法详细叙述王朝一系列的动荡变故;最后叙述公元534年2月,浮图被焚,"帝登凌云台望火",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终于在当年七月,平阳王被挟奔长安,十月京师迁邺。
文中把佛寺兴废、王朝兴衰、民心之悲三者紧紧关联,写庶民群像,既有正面的"悲哀之声,振动京邑",又有借"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的渲染,写出庶民的震撼、悲悯和仓皇,暗示元魏王朝末日将至的惶恐不安的时代氛围,昔盛今衰对比强烈。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言,昔"笃信弥繁,法教逾盛","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而今"城郭崩毁,官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昔盛今衰,引发作者浓厚的"麦秀之感"、"黍离之悲"。从这段情蕴悠悠的表白中,我们可发现《洛阳伽蓝记》的叙述角度,即作者站在追忆缅怀、痛定思痛的角度来写,强烈深沉的眷恋和悲怆之情贯注笔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