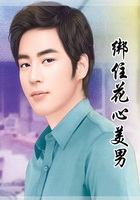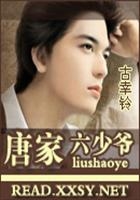见此情景,容祁原本就淡漠的眼底,竟有一圈的冰冷逐渐扩散,抬起一只手拦住了墨折:“单于不必如此,您知道容祁的来意。”
容祁的疏远让墨折精光熠熠的眼睛里淌上了一层失望,他唇角一抬,看向容祁的目光更加肆无忌惮,还有些贪婪,有些愤懑,有些痛楚,面对着这样一张让人垂涎的容颜与那让他越发兴奋的高贵和淡漠,墨折侵略性的目光变得更加尖锐起来。
他忽然一把握住了容祁的手,目光变得迷离,嘴角讳莫如深的弧度依旧:“容祁,你何必待我如此生疏,我记得你幼年时总爱唤我皇叔,如今我虽是一国之君,但说到底,这个国家还是你的,我的东西,什么时候对你吝啬过?”
“单于!”容祁原本就苍白的脸上顿时间羞愤难当,眼珠子也变得越发冷漠起来,怒气在瞳仁中凝聚,却让他难得有了情绪变化的面容显得更加的俊雅,甚至多了一分平时绝无的妖冶,忽然之间,容祁用力将手甩开,喉头一甜,抵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面白如纸。
“殿下!”堪言顿时恼火地一把推开了墨折,只恨自己没把刀带进来,要不非得把这混蛋的手砍下来不可,此刻容祁的身体状况让人越发担忧,堪言只得恶狠狠瞪了眼墨折,转向容祁,手忙脚乱地在自己身上摸索:“殿下,药……药,药在这,您快吃。”
墨折也是一时情迷,才被堪言推了个猝不及防,踉跄后退,又见容祁旧疾发作,一时不敢紧逼,只敛了荡漾的心神,神色恢复了平日的冷峻如冰,只是眼神在容祁身上流连时依旧放肆:“孤知道你今日的来意,若不是为了那位公主,你也不会上孤这来。你尽管放心,如今孤好吃好喝以公主之礼善待着她,暂时不会对她如何。”
以公主之礼……
确然,纵使那乌孙公主如今是匈奴的奴隶,但以墨折的行事,也不会公然将之随意丢在王庭之中。
似有什么东西迅速地从容祁心中闪过,难道……
容祁服下了药,神色一缓,只是黑发凌乱,墨眸如玉,面色苍白。
“这就是你要娶的女人?”墨折不知容祁心中所想,嘴角的讽刺伴随着深深的笑意:“如此姿色的女人,匈奴有的是,她配不上你。如果你是为了一个女人上孤这,此事以后就不必再提了。”
容祁眉间蹙起,若有所思,却是不语。
“自然……”墨折话锋突然一转,直挺的鼻梁下,笑意盎然:“我匈奴坐拥祁连山以北,昔日汉人猖狂,如今却根本不值一提,倒容得乌孙人胆敢与我匈奴争夺祁连一地,他们的公主到了我们手里,再尊贵,也不过一介奴隶。此次乌孙屯兵祁连,我要你将他们彻底逐出祁连,到了那时,你想要孤将一个小小奴隶赐予你,也不是不可以。”
“臣领命。”容祁陡然回神,只是淡淡拂袖,神色已是一如既往的从容淡漠,清雅尊贵,犹如神祗。
“孤乏了,你去吧。”墨折对上容祁这样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疏远淡漠,顿时有些不悦地皱起眉,神色冷下。
离开王帐,容祁不发一语,只是眉间微凝,眼眸深邃,如漫天耀眼的星辰碎成了细细的光。
堪言在身后推着轮椅,也不敢说话,只不断用眼睛偷偷去瞄容祁,欲探究他的心情究竟如何。
夜风轻拂,白袍单薄,那淡漠的神情与微凝的眉宇,纵使身坐轮椅之上,却依旧萧疏轩举,湛然若神。
在经过那座寂寞的木桩之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容祁却心头一动,忽然伸出一只手扣住了转动了轮子,迫使自己停了下来,惹得堪言也一头的雾水,却只见自家殿下忽然望那个黑漆漆的角落看去,他的神色平静,但眼底的波澜却是一圈一圈地翻滚开来,抑都抑不住。
果然,果然……
堪言顺着那方向看过去,也只看到木桩旁用链锁锁住的一个奴隶蜷缩在那的黑影而已,这在匈奴并不罕见,堪言不以为然。
容祁的神态在任何人看来还是一如往昔的平静,甚至不起波澜,只是袖下的手却已紧紧握拳,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堪言,推我过去。”
“是。”
轮椅在那蜷缩的娇小身影前停了下来,那奴隶的面容被乱糟糟的头发遮住了,根本看不清楚,一靠近,才发现她的褴褛,唯独那意外跑出衣襟的金色刺痛了他的眼。
他忽然俯身将这脏兮兮的小奴隶给捞了起来,堪言惊讶不已,但对容祁做的事却也不敢多嘴一句,只是在心里不断哀叹,那奴隶多脏啊,殿下好端端的干净的衣服全被染脏了,但殿下却丝毫不在意,惨不忍睹啊惨不忍睹!
“唔……”玉蛮忽然落入了一个馨香的怀抱,脖子上的酸疼让她一阵难受,不禁低低呜咽出声,似在哭,又似在抱怨,容祁一惊,以为她醒了,却发现她的眼睛根本是闭着的,也根本没有半点醒来的征兆,只是说胡话罢了……
容祁拥着这遍体鳞伤的小身躯,目光扫过她手腕上的手铐和脚上的链子,眼神骤然一冷。
他本就不易让人接近,此时浑身散发出的冷意更是让人觉得这个消瘦的背影更加遥远,是一座永远不可触及的雪山峰顶。
“解开她的铐链。”
平静的语气,不怒不愠,却也无丝毫温度。
这话是对那几个跟在他和堪言身后的王庭的侍从说的。
几人也被容祁忽然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意给震慑到了,这个体弱多病却对任何事都云淡风轻的容祁殿下原来也是有情绪的,他现在明显是在生气,尽管他就是正在生气,也依旧冷冷淡淡的模样,但那恼怒的火焰已在宁静的一汪深潭中搅起了一圈圈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