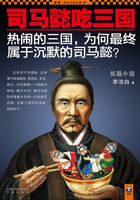1.让生活充满乐趣
比喻要有可比性,这是修辞的规律。可是,把本体与喻体之间并不一致的地方直接扯在一起,这是产生幽默感的规律。除了用不相称的分类和排列引起怪异之感以外,还可以用不伦不类的比喻来造成滑稽的效果。
从通常的修辞学角度来说,比喻要有可比性,要在本体与喻体之间有一致的地方,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可比性。比如说,一尺布可以与五丈布相比,但是不能与一斤铁直接相比。不能比就是没有可比性,把没有可比性的直接相比就犯了无类比附的错误,这是修辞学的规律。可是把没有可比性的事物直接扯在一起,却是幽默感的规律。
有一户人家,养了一只猴子。这只猴子聪明伶俐,特别讨人喜欢。而且,它还会模仿人类的一些动作,如果家里来了客人,主人有时会让它表演拿东西、让座等。吃饭之后,它也会像佣人一样收拾碗筷,很讨主人欢喜。
有一天,家中来了位远方客人,这位客人与主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但是碍于情面,主人留他在家吃午饭。喝酒的时候,这位客人似乎有些得意忘形,肆无忌惮,表现得有些失礼。主人心里虽然很不高兴,但毕竟是在招待客人,所以仍然没有发作。主人唤猴子出来给客人敬酒,猴子依言去做,客人很高兴,就拿酒给猴子喝,猴子连喝了几杯,就有些醉了,于是兽性发作,将酒洒了一地,把盘子也打翻了。主人愤怒地训斥道:“本来看你还像个人,谁知喝了这点酒,就不像个人了!”客人听出话中有话,脸一红,行为自然就收敛了许多。
这位聪明的主人碍于面子不好意思直接向客人提出不满,他巧妙地借猴子这件“物”来施展幽默术,让客人从中听出主人的不满之意,而在场面上又能够说得过去。
汉语有一种特殊的修辞方法,就是歇后语,歇后语本来属于比喻的暗喻之列,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本体与喻体之间是不伦不类的,因而大都十分滑稽,如形容人做事有条不紊或者唱曲子很有水平,从容不迫,口语叫做有板有眼的。这是一个带着褒义的词语,可是有一个歇后语,是:光屁股坐板凳——有板有眼。这里的有“板”是指板凳之板,而有“眼”则指肛门。这与做事或唱戏有水平不但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在联想意味的雅俗上也不能相容。
绝大多数歇后语都以本体与喻体之间的无类比附为特点。因而茅盾认为歇后语是一种“文字游戏”。歇后语不是一种正经的修辞方法,而是一种戏谑性的修辞方法,由于它往往远及无类,而强加比附,常常奇趣横生。例如:
(形容人不切实际)棒槌敲竹筒——空想(响)。
(形容人说话不实)阎王出了告示——鬼话连篇。
(说人的水平不怎么样)床底下放风筝——不高也不妙。
(说人潜力不大)老鼠尾巴上长疗子——有脓也不多。
(说人意图不善)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多数歇后语以荒诞、滑稽取胜。但是也有一些滑稽意味并不太浓的如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还有一些非常粗野的或者太荤的,在使用的时候,就需要细心鉴别,否则可能产生不雅的效果。不仅对不雅的歇后语要鉴别,而且对任何一种不伦不类的比喻都要留心使用。
2.生活需要哈哈镜
通过对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加以极力的夸大,渲染,来虚构某种不合理或者不和谐的因素就是荒谬夸张的幽默。因为荒谬夸张本身包含了不协调,因此总能引起人们发笑,而产生强烈的幽默效果。
夸张只是一种修辞手法,用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情境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时夸张并不都能产生幽默。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都是夸张,但是我们听不出幽默来,仅仅是浓愁锁眉,豪迈奔腾之感。因此产生幽默的夸张必须是荒诞、离奇的夸张,夸张到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可能见到的地步,这样才会产生强烈的幽默效果,令人捧腹大笑。
荒谬夸张是一种吹牛技巧。吹牛的笑话很多,你平时既可收集,从中学习,也可以自我实践,进行创作。吹牛还可能给你带来意料不到的好处,增加你的幽默感。
清朝程世爵编的《笑林广记》中有一个《瞎子吃鱼》的故事。说是一群瞎子打平伙吃鱼,但是鱼少人多,只好用大锅熬汤。鱼都蹦到锅外面去了,瞎子也不知道。他们都没吃过鱼,不知鱼的滋味;大家围在锅前,喝着清水汤,齐声称赞:
“好鲜汤!好鲜汤!”
鱼在地下蹦到一个瞎子的脚上,这个瞎子才大叫起来:“鱼不在锅里!”众瞎子感叹起来:“阿弥陀佛,亏得鱼在锅外,若是真在锅里,我们岂不都要鲜死了。”
明明是没有鱼的清水汤,瞎子却在称赞“好鲜汤”,这就是这个故事荒谬的前提。这自然是一种夸张的幻觉,但也不能完全胡吹,也得有点根据,于是把吃鱼的人设计成瞎子,让他看不见,又特别说明他们从未吃过鱼。如果没有这两点,这个前提就不能成立了。前提不能成立,以下故事的逻辑基础就垮了。
这个基础的真正荒谬之处是一种错觉,一种主观的着迷,而并不是自我欺骗,因为这是真诚的。正因为这样,它着迷得很有趣。但是光有这么一点着迷,效果还很有限,还不够劲,还得让效果放大一下,让瞎子的逻辑荒谬得更强烈一些才行,于是便有下面的高潮:原来不知没有鱼,觉得汤鲜,还情有可原,现在明明知道没有鱼,汤鲜的错觉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引出了没有被鲜死的庆幸。
这种幽默的生命,不但在于人物在一点上着迷,而且在于不管怎样走向极端,着迷点都不会消失,反而会增强。一点着迷和导致极端,是构成这类幽默的两个关键。
下面这则例子更能让你体味到荒谬夸张的幽默效果。
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在一起吹嘘他们本国的火车如何如何地快。
法国人说:“在我们国家,火车快极了,路旁的电线杆看起来就像花园中的栅栏一样。”
英国人忙接上说:“我们国家的火车真是太快了!得往车轮上不断泼水,否则,车轮就会变得白热化,甚至融化。”
“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美国人不以为然地说:“有一次,我在国内旅行,我女儿到车站送我。我刚坐好车就开动了。我连忙把身子探出窗口吻我的女儿,却不料吻着离我女儿六英里远的一个满脸黑乎乎的农村老太婆。”
荒诞夸张的程度,三者不相上下,但是美国人的夸张却格外引人发笑。因为美国人的夸张语言不是就事论事,直接说快,而是借用吻女儿这一情节的“弄巧成拙”来夸说车速之快,本想吻女儿却吻着老太婆,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幽默,经过他的夸张渲染,反衬车速之快,就更加令人笑不可抑了。
可见荒谬夸张幽默术不但是直接的夸张,而且借助其他事物渲染自己的夸张对象则更为常见,也更为幽默。例如当你夸说电话费高昂的时候,最好不要直接说出每分钟多少元,那种直露的夸张不够幽默,如果你说:“昨晚我给邻居打了个电话,说了三个字,就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就要俏皮可笑得多。
荒谬夸张幽默术的幽默程度与其夸张的荒谬程度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荒谬的程度越高,夸张得越“离谱”,就越幽默。当然这种“离谱”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天马行空、神乎其神地乱吹乱侃,绝不能称为幽默。吹牛也好,夸张也好,不是看谁把牛吹得大,把人夸得响,如果比大,是没有好结果也毫无意义的,而看你是否吹得妙,是否能引人发笑。荒谬夸张幽默术的妙处依然在于引起某种不协调,让人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它需要你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表达技巧,而不是刻意求“玄”。
3.偷梁换柱
把概念的内涵作大幅度的转移、转换,使预期失落,产生意外;偷换得越是隐蔽,概念的内涵差距越大,幽默的效果越是强烈。幽默是一种情感思维方法,它与人们通常的理性思维方法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对于相同之处,人们不用细心钻研,就可以自发地掌握;而对于不同之处,许多幽默感很强的人虽然已经掌握,但不知其所以然,而幽默感不强的人则往往以通常的思维方法去代替幽默的思维方法,其结果自然是幽默感的消失。幽默的思维和通常的理性思维至少有两个方面是不同的。第一,在概念的使用和构成上;第二,在推理的方法上。这里主要讲概念在幽默中的特殊表现。
通常人们进行理性思维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要求那就是概念的含义要稳定,双方讨论的必然是同一回事,或者自己讲的、写的同一个概念前提要一致;如果不一致,就成了聋子的对话——各人说各人的。如果在自己的演说或文章中,同一概念的含义变过来变过去,那就是语无伦次。
看起来,这很不可思议,但是这恰恰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同一个概念常常并不是只有一种含义,尤其是那些基本的常用的概念往往有许多种含义。如果说话、写文章的人不讲究,常常会导致概念的含义的转移,虽然在字面上这个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化,在科学研究、政治生活或商业活动中,概念的含义在上下文中发生这样的变化是非常可怕的。因而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在他的逻辑学中就规定了一条,思考问题时概念要统一,他把它叫作“同一律”。违反了这条规律,就叫做“偷换概念”,也就是说,字面上你没有变,可是你把它所包含的意思偷偷地换掉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可是幽默的思维并不属于这种类型,它并不完全是实用型的,理智型的;它主要是情感型的。而情感与理性是天生的矛盾体,对于普通思维而言它是破坏性的东西,对于幽默感则可能是建设性的成分。
有这样一则小幽默:
“马修,细心点!”老师说,“四加四等于几?”
“等于八,老师。”马修很有把握地说。
“你是怎么算出来的?”老师又问。
“您把书桌的四个角都砍掉就明白了!”马修终于说出了答案。
偷梁换柱、答非所问,是指答话者故意偏离逻辑规则,不直接回答对方提问,而是在形势上响应对方问话,通过有益的错位造就幽默。答非所问并不是思维混乱,而是用假错的形式,幽默地表达潜在意图,形成幽默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