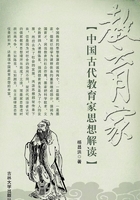尽管前三十年对于古代文化评价不高,但那时频繁的政治运动却往往发难于古典文学或历史研究领域。这里举几个比较昭著的。如50年代初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50年代后期的批判“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古为今用”以及“拔白旗”“插红旗”(在文史研究领域最为激烈);60年代批判忠王李秀成的“忠王不忠”和批判吴晗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等等都与古典文学密切相关。这个时期每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与文史有关工作的知识人更是心怀惴惴,怕写文章、怕被人抓住小辫子、怕犯错误等,也给一些善于“成人之恶”的小人以绝好的出风头、攀高枝的机会。他们眼如雷达,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四处搜寻对象。于是在研究领域的批判、否定和空论日益增多,实事求是的研究日益减少。
廖先生说这一个时期是“知识分子三灾八难的年月”,一点不假。不会看风转舵、不趋时,总带着一些理想主义的知识人更容易动辄得咎,免不了要经历“挨整、挨批、受处分”的苦难,廖仲安也是这样。
近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无不以改造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相标榜,但廖先生的感受是“运动、批判并没有使怀疑减少,而且往往更增多了怀疑”。可悲的是,文章可以少写或不写,但老师不能不讲课。讲课中如何评价作家、作品成为最敏感的问题。领导强调在这些问题上要“把好关口”。
当然这对于“无可无不可”、毫无学术良知的人好办,社会通行“宁左勿右”一套,只要把古人一概骂倒,这样安全系数最大(当然1970年代如果骂到秦始皇、法家头上结果也不美妙)。而廖仲安不能,他说“我们这些身临讲坛,在同学们十目所视下的教书人,不能不紧张地关注着校外的‘风’和校内的‘浪’”,更不能昧着良心胡说。那时有些学生在社会风气熏染下以革命自居,向党委校方举报告发老师“放毒”也是常有的事,做教师成了高危行业,不久文革就证明了这一点。廖仲安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他尽量本着学术良知去做,这就不能不与外界环境发生冲撞。我们从《反刍集》许多文章中可见其内心的挣扎,比较典型的是20世纪60年代所写评价曹植、苏轼作品的文章和20世纪70年代写《水浒浅谈》。
评价作家和作品是敏感问题,那么评价苏轼及其作品就是敏感中的敏感。苏轼是“千古一人”,是位全能作家,诗词文都有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作品传世;但他有个致命问题就是反对王安石新法。建国前谈论苏轼这不是问题,王安石被称为“抝相公”,其继承人是蔡京,新法祸国殃民几乎是公论,反新法是具有正面价值的。解放后,价值观变了,何况王安石变法又曾被列宁肯定称赞,于是王安石就成了政治正确的坐标。苏轼这一类反新法“元祐党”人,轻则被评为保守,重则斥为反动。过去评论诗词文学,往往不涉及作者的政治态度,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严嵩、阮大铖的诗歌清新流利,照样有人赞美。解放后,意识形态主导,政治文化一体化,因此再评论苏氏文学作品时,政治态度就成了不能回避的问题。
于是廖仲安写了《论变法与苏氏作品评价的关系》力图解决这个问题,文章中在肯定了苏轼与新法无关的许多佳作之后,提出就是反新法的作品也要进行分析,他认为苏氏有些作品虽写于实施新法时期,但确实反映了人民苦难,表达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如《和子由蚕布》等;有些批评了新法,但确实反映的是现实,例如《吴中田妇叹》。另有一类则是“表面看来也有现实性,实际上完全是在顽固保守的政治思想支配下彻头彻尾歪曲现实的作品”。对于这些廖先生是完全否定的,举的例子是《山村即事》: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眼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文章中说,在俵散青苗钱时虽然存在官府利用娱乐演戏等手段诱使借贷青苗钱的农民花钱的现象,但第一这不是普遍现象,第二这只是执行的问题,不是新法的毛病,第三青苗法从总的倾向上看是对人民有利的。并指出青苗法即使有缺点,也不能像苏轼这样“用的完全是一种冷嘲热讽的调子,显然不是什么积极的建议和批评”。在当时政治氛围下,这已经是对苏氏作品最大的善意了。但现在看起来仍有可訾议之处。比如,既然承认有缺点,作为文学家为什么不能“冷嘲热讽”?
说到底那时公正的文学批评是不能做到的,因为有几个大前提是不能碰的,如“政治标准第一”(“第一”往往便成“唯一”),评判作家先要经过政治过滤器。苏轼政治倾向先天不足是既成事实,谁也改变不了。另外王安石变法是先进的社会运动也被视为定论,是不能怀疑的。于是廖仲安只能在划定的圈子转。其实我们放下这些,从另一个角度想,很好解决。就算变法百分之百正确,没有任何瑕疵,全为贫困百姓着想(当然这不可能),难道它在推行中也会完美无缺?如果有些缺点,哪怕就是万分之一能不能写?文学创作不是政治家写条陈,要注意态度和可接受性。文学家考虑的是写得好不好,感人不感人;想通了这些,就会觉得苏轼一些批评新法、青苗法的诗写得很俏皮,非常精彩,他的确是写讽刺诗的高手。
《水浒浅谈》写于文革中(1972—1973),本是军宣队和革委会分派的任务。那时林彪刚倒台,社会上一度批判极左,局势稍稍稳定。但文革的反复折腾,大多数知识人是满怀恐惧的,屡经劫难的廖仲安更不会例外,但分配的任务又不能不做。廖仲安是文章快手,但这本四万字的小册子,他写了半年多。他说:
在写作过程中,虽然对《水浒》这本小说以及有关的资料研究得很不够,但是对毛主席和鲁迅谈论到《水浒》的话,却是做了比较认真的搜集工作,凡是在公开的文献上能找到的材料,不敢说毫无遗漏,也敢说十得八九。
历经种种被批斗的苦难之后,第一次又拿起笔来写作,怎么能不吸取点教训!他心怀惴惴,怕犯政治错误,本来廖先生是非常注重文本和参考资料的,此时文本、资料都可以放一放,个人看法(有些与我聊过,如对宋江形象的认识等)更不敢写入,尽量采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用大量的时间收集毛主席的指示与鲁迅的论述,并加以消化。这是在为此书上政治保险。历史仿佛爱跟老实人开玩笑,这两项保险突然不灵了。因为有了新的“指示”。《水浒浅谈》仍然难逃罪责,廖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箭靶子,再遭整肃,再度被下放。注定受难,再挣扎也没有用。
三、拨乱反正与探索
粉碎“四人帮”后,文化教育都是重灾区,拨乱反正的任务尤重,古典文学研究也是如此。许多中青年研究者(知识界认为中国被耽误了二十年,大家都减二十岁,廖仲安被视为中年)成为拨乱反正的积极参与者,廖就是其中的一位。1980年古典文学界研究期刊《文学遗产》以大型研究刊物形式(文革前只是《光明日报》的副刊)复刊,他被聘请为编委。《反刍集》中的文章大半写于1977年后十年,有的就发表在《文学遗产》上。他不仅批判“四人帮”与极左思潮对于古典文学的歪曲,如《晴雯的新冤案》《孔子文艺思想漫谈》《“剔除”与“吸收”》《漫谈杜诗中的忠君思想》等,更重要的是他在研究上有反思也有探索。
20世纪80年代,在古典文学研究上,鉴赏作品一窝蜂,从上海辞书出版社《唐诗鉴赏辞典》出版后,许多出版社纷纷效颦,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也被卷入,而廖仲安更注重考证和对作品思想艺术的探索,并将两者结合起来。《穷源溯流的指导思想》一文中指出:“文学史,是人类精神文明历史中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要把这些人文之美展示出来,决不能只局限作品本身,更要对当社会背景、文化氛围有深入的理解。从许多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如《再评宋江》针对《水浒》研究中都把宋江称作“小官吏”这一现象,指出在宋代“官”与“吏”有很大区别。官属于士人系统,是官人,犯罪了,脸上也不能刺字;吏是庶民,称公人,犯罪了脸上可刺字,而且吏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比一般庶民又低了一层)。从这个考订来分析宋江形象的实质及其所代表的意义。
宋代胥吏社会地位极低,但实际权力极大。侵官病民根固窟穴,缔交合党,很有神通。吏胥与“盗贼”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愈是胆大冒险,敢于逾越这条界限的人,在江湖上就愈有威望”。宋江就是一个脚踩黑白两道的人。这篇论文给《水浒》研究一个重要提示,不要老在农民起义上纠缠,梁山一百零八将中没有什么农民,应该多考虑一下像宋江这样的社会边缘人的问题。可惜这篇论文早在80年代就发表在《文学遗产》上,但引起的关注的并不多,一谈宋江还是“小官吏”,对别人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是近些年来学术界的重要盲点。
廖仲安还关注清代文化专制统治,清统治者属于少数民族,其统治期间注重防范汉族臣民,有一套办法。为此廖写了《读〈名教罪人〉有感》《〈红楼梦〉与清代政治管见》《龚自珍与〈红楼梦〉》《沈德潜诗述评》等篇都涉及文化专制。清代的专制统治不仅较历代严酷,而且是通过民族歧视与压迫来实现的,因之,它不仅关系文艺创作,更涉及到近代民族性格的形成。清代是离我们最近的皇权专制王朝,破解清代的统治秘密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廖先生几次提到鲁迅在这方面的工作及其期待:
鲁迅很希望有人能从《东华录》《御批通鉴楫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等书中,将其中的关于驾驭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从这些材料里,不但可以看出清代统治者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而且还能明白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
实际上这是直至今日也尚未完全的任务。
《反刍集续编》中许多文章涉及到其他文化领域。如《鸦片战争以前的“西学”偶谈》《“阎罗王”与“开天圣”》《野蔬充膳甘葵藿》《辨味、烹调与美学质疑》《衣食与中国文化小议》《诗经印谱》等都是从古典文学的角度引发的感受。
四、廖仲安先生为人
我是在1962年年底上文学史课时第一次见到廖先生的,当时他已经很有名了。上课铃响了,他穿一件蓝棉布大衣,戴一顶长毛绒的帽子迈着持重的步子走进阶梯教室,缓缓地脱下大衣,用一只手提起头顶上的帽子,把它轻轻地放在讲台上,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授课。当时,廖先生还不到四十岁,我们这些比他小不到二十岁的学生,觉得他已经很老了,是位渊博的老先生。听讲唐传奇沈既济的《枕中记》给我印象最深,卢生得仙人吕翁瓷枕,一梦之中享尽人间富贵,当他醒来时,逆旅主人蒸黄粱饭尚未熟。分析完这个故事,廖先生忽引《随园诗话》记载的邯郸黄粱梦某穷书生的题诗“四十年来公与侯,虽然是梦亦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与先生借枕头”。他感慨此人无慧根,人家已经告诉你是梦,你还要尝试!
1964年大学毕业时被整肃,被发到南口农场劳动,1968年底又被接回北师院。这时虽在文革中,但热闹的造反已经过去,革委会把学生与教职员工编在一起搞“斗批改”。此时学生仅有1965届(此年入学),我就插在这些学生当中,与老师一起参加运动,从而与廖先生有了许多接触。后来因战备下放到东方红炼油厂(现在的燕山石化)、顺义良种场、平谷关上、大兴陈各庄劳动不必像在学校正襟危坐谈学习心得体会,都放松了。也是我没改造好,不能忘情“封资修”,有的青年教师觉悟高,不免制止或批评一下,而廖先生却有兴趣,这样就慢慢熟了。离校之后,因与廖先生住家相距不远(他住宣武门内未英胡同,我住菜市口),徒步只需20分钟,于是便常去他家,向廖先生请教学习。使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岁月、外部力量似乎很难在廖先生身上镌刻下痕迹,几十年了,除了发福一些,有点白发外,还是我初见到时的样子。他为人谦和,从无疾言厉色,脸上仿佛总是泛着一丝笑纹。文革当中,挨批斗时,他也是这个样子,小将愤怒了:“我们批斗他,他还笑!”廖先生无奈地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怎么办?”走路仿佛是在踱步,我没见过他跑步,不知他跑步是什么样子。他永远是那样不紧不慢地走,我想大约这合乎古礼的规范。然而,他绝对不是儒者,尽管许多人称他“廖夫子”。他很早就受到五四的启蒙,虽然家乡西昌地处偏僻,但其兄长曾在北京读书,回乡作小学校长,带回了鲁迅的书和《新青年》,他很快就接受了新文化导师们的思想理念。抗战末,他考上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后来转入北大,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秘密加入地下党。但他没有那些激进人士的外露张扬,更无唯我独革的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