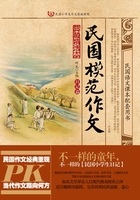民国时期,应该说是帮会最红火的时期。因为他们一直标榜是反清的,孙中山本人也曾加入洪门,职为红棍。这些帮会,参与了孙中山等人领导的反清起义,用孙先生的话说,是“无役不从”——没有一次战役他们不跟着打的。实际上,孙中山作为受了西方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与帮会的诉求是不同的。怎么把底层游民的传统诉求与知识分子的追求相融合,孙中山做不好这个事。刚刚推翻清政府时,孙先生等领导革命的人物对帮会起的作用评价过高,好像天下是帮会打下来的。应该说,清朝灭亡是极自然的事情。这个带有民族压迫色彩的皇权专制王朝到了20世纪已经千疮百孔,正在自然解体,辛亥革命只是轻轻推了一下,它便轰然倒塌。
民国政府一开始有点犒赏帮会的意思,后来又要整顿他们。有很多人评价说,这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忘了底层人民对革命的功劳,把他们抛弃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帮会没有一点儿近代意识,就是“打天下坐天下”那一套,就像李逵那种意识似的,孙大哥对他们就像是大皇帝,他们统统做小皇帝,做将军什么的;这是连改朝换代、建立一统王朝也不能允许的。政府要想正常执政,推行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就不能不改造帮会。或者实施另外一种做法,像朱元璋,把这些人统统借各种理由铲除杀掉。当时孙中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他所受的思想影响来看也不允许他这样做。后来的袁世凯想这样做,也是力不从心,因为这些力量多在南方,而南方在他的势力影响之外。
民国间,秘密帮会大多公开化了。当时游民很多,他们又招收了很多人,以打天下的功臣自居,形成了强大的势力。
民国时期政府是个弱势政府,直到1949年前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统一过。军阀割据,党阀分权,他们在不同的外来势力的支持下互相争斗,于是中间出现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大多是由帮会或说黑社会来填充的。政府作为一个统治机构,已经从老百姓那儿收了税了,搜刮了不少钱财,却不能提供全部公共服务。土匪、异地的武装力量对老百姓的危害,它们不能提供保护;地痞流氓对百姓的骚扰,它们不能制止。有时黑社会却能出来承担这个职责,当然这也决不是义务白干,而是要收保护费的,肯定比税还要高。可见黑社会起的是二政府的作用。有的帮会领导人好一点,能够约束下面会众的行动。但从总体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这个人,打出名堂后,追求名声是他为人重要的特点。他出身店员,文化程度很低,特别希望跟文化人往来,以提高自己在主流社会的名望。民国时著名学者杨度、章士钊都曾被他礼遇,用他的钱。他在民国元老文人章太炎先生身上也花了好多钱,就希望太炎先生为他的家庙写个碑文。杨度对章太炎说,杜先生这个人你别看不起他,他就是《史记·游侠列传》中朱家、郭解那一类人物。后来章先生为他写了。民初总统黎元洪被迫下台后,流落上海,得到杜月笙热情款待,黎元洪为他题了“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的对联,把杜月笙比之于战国时大侠春申君(春申君封地在上海附近),并把他拟之于“城南韦杜,离天尺五”的贵族。
你看杜月笙那样子很老实,实际上他手面非常大,组织能力很强,据说在抗日战争中,在后方杜月笙组织的流亡老百姓的接待站,比国民党政府办得还好。他救过很多人,当然,也害过很多人。过去老说他害人的一面,现在又过分强调他救人的一面,只看一面都是不公正的。
这个例子说明了事情的复杂性,不能简单用阶级论分析。作为杜月笙本人来讲,的确个性很强,是会做人的人。他常强调为人要吃三碗面,“一是情面,二是体面,三是场面”。他靠娴熟的人际关系交际遍天下,为他赢来了名声。这与现在很多戴着墨镜,穿着黑西装,打黑领带的所谓黑社会的大哥是不一样的。
我在六岁的时候,见过一个在理会的在北平的头头。这个组织在北方有很大影响力,其特点就是不喝酒,不抽烟。我父亲那会儿做买卖,不跟这种人打交道是不行的。带我到他家去过一趟,父亲叫我称他为师爷。他穿着棉袍,挺长的胡子,人很体面,家里干净清寒,缠足的老妻站在一边为客人沏茶倒水,亲热招待客人。老人面容好像当时民盟的领袖沈钧儒,你完全感觉不到他是一个黑社会的头子,是“一跺脚,北平四九城乱颤”的人物。他似乎就是非常普通的老秀才,对小孩和善慈祥。所以现在所谓“黑社会”一看就不是黑社会,仿佛都是电影里的人物。所谓黑社会的大哥仿佛是胡同的小玩闹似的。
1949年之后,黑社会曾经被迅速清除,可是近几十年,有组织的犯罪又开始出现,您觉得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情况呢?
王学泰:解放后,政府用行政组织手段代替民间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社会,这种情况下黑社会消失是必然的。老百姓很支持,因为老百姓百年来一直受黑社会的欺压,受害太深。政府也是强势政府,无所不至,黑社会自然灰飞烟灭。
现今处在社会转型期间,行政力量也逐渐从民间社会中退出,民间社会也在逐渐恢复。自生社会自然是良莠并存。不能期待大自然只长好草,不长杂草;社会也是这样,关键是法制社会具有强大的矫正能力。现在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的出现并不奇怪,应该用正常的法治手段去解决,见微知著,最好在其萌芽时就能发现,就能绳之以法。不是“打”——“打”这个词不是非常准确的,它是政治运动常用的动词。在正常的法制社会无论良民还是“莠民”,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应该防止人犯罪,而不是诱导人犯法(如钓鱼执法)。我们对黑社会也是这样,不是等它成气候了去打它,而是从经济上、法律上排除其犯罪的土壤和条件。
中国的黑帮
这篇是答《南都周刊》记者杨猛先生问,发表在2009年11月11日。
王学泰曾经亲历过一次“打黑”。1957年夏天,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当时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初中三年级的王学泰,到西河沿的劝业场去买《唐宋名家词选》。突然劝业场前后门都被警察封死,顾客只准进,不准出,冲进来一队警察,进行搜场,逮捕了数十名流氓犯罪分子。劝业场类似今日集贸市场,有数百家摊位,常有流氓在这里敲诈勒索,警察在周末采取突击行动集中抓捕骚扰市场的犯罪分子。年少的王学泰被困在市场1个多小时。这事给他印象非常之深。王学泰所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探讨了古代游民组织化过程和有组织犯罪的关系。
帮会的历史和“袍哥”
记者:“黑社会”的概念是一个舶来品,近代才频繁出现在新闻、纪实作品中。中国历史上有没有“黑帮”或者“黑社会”组织,是怎么产生的?
王学泰:所谓黑社会,我觉得须具备三条:第一,做的事情为主流社会不允许,是非法的。比如靠黄赌毒生存;第二,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结构,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力量,因此能够从事暴力犯罪或暴力威慑;第三,人员相对较多,不是一二百人就能构成一个“社会”。它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某种程度上能与政府分庭抗礼。换句话说,如果真能称得上黑社会的话,政府也不是一打就能打掉的。
“黑社会”这个概念应该是与“白社会”相对而存在的。所谓“白社会”就是正常的社会,这里的人们遵纪守法,按照通常的、为大众所认可的规则生活,这些都显露在日常生活中,为众人所知的,所以我们称之为“白”。而“黑社会”为了获取不正当的利益,采取了非法手段,他们的许多行为特别是与获取利益相关的行为是对外保密的,有的还在互相联系的语言行为中设立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符号,如黑话(秘密语),洪门的“出手不离三”等。这种不为外人所知的诡秘——黑,再加上他们为了获取利益不择手段——心黑、手黑,这三“黑”是黑社会的本质特征。
据我所知,民国时期开始使用“黑社会”这个词。民国时期的江浙一带的青红帮,北方在理会,湖广一带的洪门,四川云贵一带的哥老会等帮会形成的势力构成了与“白社会”相对的黑社会。
我们现在常说帮会,实际上,帮和会不是一回事,两者是不同的。帮,是一种江湖组织,清代以来主要在小城镇活动,清末也扩大到上海大城市,主要成分是游民。
会,主要是指秘密会教门。 近代史上,像义和拳、小刀会、白莲教、闻香教、八卦教等,其性质都属于会。会,是地域性或者说乡土型的。比如白莲教多在山东一代活动。成员以农民为主,组织者仍以游民为多。白莲教等秘密会道门都有职业传教者,世代相传,我见过一个人家里数代都以传教为生。他们也搞气功治病、符水治病,也传教,宣扬极乐世界以吸引会众,信众之中也搞一些互助活动等。解放后,大多会道门都被列为反动组织,被取缔,如一贯道、九宫道等。
在组织结构上帮和会也有区别。会,讲究辈分,比如白莲教,是师徒之间的传授。而帮没有辈分,一入门都以哥弟相称。比如洪门、哥老会,讲究“哥不大,弟不小”,表面一律平等。但实际也有“大哥”的决定权,对兄弟的处置权绝不比父亲、师傅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