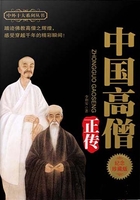二十年前同外地来的朋友一起洗澡,洗完后,他搓澡。搓完后,这位老兄双手高举,几乎要喊起了:一路的风尘,全部搓下。说请吃饭喝酒是“洗尘”,那能洗什么“尘”?这才是真正的“洗尘”,简直是搓掉了一个“旧我”,推出了一个“新我”,我整个是个“新人”了。文革中我们一块“劳动改造”过,我说“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他也劝我搓一搓,我没有尝试,“我还是老老实实做我的‘旧人’吧”。不过中年以后,去澡堂我很注意用搓脚石搓脚。这是一种有马蜂窝的、很坚硬的火山熔岩。在热池子里水把脚泡得软软的,用搓脚石三下两下,脚后跟的老皮皴裂,一扫而光。全脚面目一新,让我想起聂绀弩的诗句“老头能有年青脚”,快何如哉。
在池子里出透了汗,一出池子是口干舌燥,全身酸软,最惬意的喝上一口沏好的小叶花茶,在床上眯一小觉。进池子之前,买包茶叶或把自备的茶叶交给茶房(现在饭馆不许自备酒水,真是自古少见的章程),客人出了池子,茶早已沏好。带有余香的包茶叶纸被叠成一个纸三角,套在壶嘴上,免得尘土进入,精致而且细致。此时一杯酽茶,清吻润喉,无比畅快。喝痛快了,我常常是带本书,躺着看,倦了就睡着了。
因为看书睡觉我还出过一次事。1974年的夏天,带了本钱穆的《国学概论》(30年代上海出版的)到清华池洗澡,洗完后,躺着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突然听到“有人看黄书”,跟着有人将我推醒,一看是服务员,旁边还站着一个气呼呼的当兵的和几个莫名其妙的洗澡客。他们都以诧异的眼光看着我。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当兵的就质问:“你为什么看黄书?”我感到很奇怪:“什么黄书?”那个当兵脸都涨红了,他一只手提着《国学概论》一个犄角,用力抖动,气愤地说:“你看看,你还敢赖?”书是用“白报纸”印的,三四十年了,纸张焦脆变黄,书脊开胶,一副黄脸婆模样。当兵的当做战利品抖了抖,纸屑飞舞,快散架了。“你是干吗的?那是我的书,你这样一抖落就报销了。”当兵的气势汹汹地说:“我是干什么的!学**的,解放军。你看黄书还理了?这是犯法的!”其实那时有什么“法”。不过那时社会上正在调查“手抄本”,如《第二次握手》《曼娜回忆录》《梅花档案》之类,统称黄书。
这个“学**”的小兵自觉地站在阶级斗争第一线,又出于对“书”本能的敌视(那时除了红宝书外,看其他任何书都有反动之嫌),好像发现阶级敌人一样。服务员是熟人赶紧解围说:“老来的常客,洗累了,睡着了,没什么,没什么。”那个当兵不依不饶:“不在他睡不睡觉……”我知道今天他要找“书”的毛病,解释是不管用的。我反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书吗?”这充满底气的一问,当兵的有些打结了。我紧接着说:“现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是评法批儒的书,以后人人要学的。
”当时“法家”被捧上天,说是“评法”,实际上是“赞法”,为法家、特别是秦始皇大唱赞歌,大有红宝书第一,法家著作第二的趋势,连马列都没它吃香了。这个小战士有些尴尬了,那时全民搞批林批孔,一些旧书拿出做参考,大约他在什么地方也看到过,再加上他又看不懂书上的繁体字,自觉气馁。那位老服务员赶紧打圆场:“没事,没事,大家休息去。别妨碍这位师傅学习。”又向我道歉:“对不起,师傅,耽误您学习了。”本来醒来就想走了,经他这么一闹,反而不好马上走了,仿佛落荒而逃似的。我一边品着花茶,一边继续看《国学概论》,但再也没有最初的兴趣了,看不下去了,只得装模作样地捧着书呆想。觉得自己也很无聊,为什么去蒙一个小兵呢?还连累远在海外的钱穆,让他临时充当一下“评法批儒”的干将。
在澡堂子聊天也是很有趣的,老北京爱聊,泡澡堂的“澡友”,还得加个“更”字。因为他们多是中老年有阅历、又有闲。许多印象较深的接触,现在想起来仍很有趣。比如绸缎庄老店员衣履服饰的讲究,他们脱衣服时要一件一件叠好,一出池子,先要从自己带的小包包里拿出梳子对着小镜子把仅有的几根头发小心地梳光溜,这是自小学徒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又如听打小鼓(现在没了。这一行走街串巷,或挑挑,或夹一包袱,手持牛皮小鼓,细藤棍敲打,招徕卖主)讲收旧货,讲他们如何从破落户(20世纪50年代初极多)家中收“好东西”,如何“买死人”(暴利收购)“卖死人”(暴利售出);听“典当行”的老伙计说这个行当的规则、职业操守和难处,告诉我“当”字(专门用来写当票的)的写法和规律;听京剧的底包演员讲过去跑江湖的辛苦、风波险恶和老江湖如何应付自如以及京剧名角的趣事……总之,只要是社会上有的事,这里都听得到。从反右到文革结束这二十年,大多数人不敢多言多语了,但此之前,澡堂就像个茶馆,可以听到各种怪怪奇奇的事情。文革之后,这种风气像要恢复,后来随着洗澡业的衰落,它便成广陵散了。
文革当中,大约是1974年春,有次在虎坊桥浴池洗澡,洗完之后,正在喝茶歇息,对坐的也从池子里出来了。他是一个体态微胖的老者,看样子像位工人。老人一面用服务员递过来的热毛巾揩面,一面向我打招呼,寒暄。我看他肋下有个一尺来长的刀口,仿佛做完手术没多久,伤疤经热水一烫,分外红亮。我问:“刚做完手术吧?要注意伤口啊。”老者说:“没事,没事,一年了。手术做得地道,你别看我是普通工人,这个手术可都是一级专家做的。”我觉得奇怪,觉得老人有些自吹,谁去看病,医生也不会吹嘘自己是“一级专家”。
他看我面带疑惑,便打开了话匣子:“我得的是癌症,而且是肝癌,最初以为活不多久了。我有福在于,跟一位首长——”此时他身子倾斜过来,在我耳边小声说:“……的病一样,位置和身体状况都一样。于是,给我治病的、开刀的就是给首长治的那拨人。用药,开刀后护理,连吃饭都一样。当时领导就说了,你这病难治,但现在是一级专家给你治,让你给首长趟趟道。这不是我还真趟过来了,好了。”他拍了拍伤口,得意地笑了。我问:“首长呐?”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没趟过来。”“奇怪,你这趟地雷的过来了,怎么后跟着走的倒没过来呢?”“说的说呢?也许我趟时,地雷没炸,他跟着走时,炸了。这就是运气吧!”说着他狡黠地笑了。
50年代以后的澡堂子有个从私营到公私合营,再到国营的转变过程。从经营上说日益规范,价格便宜(长期稳定在0.26元、0.23元),也不收小费了,也没有“爷”的称呼了,日益废除了唱收唱谢的习惯,扫荡了旧社会的遗迹。新社会强调浴池的单一的清洁卫生功能,为此许多澡堂增加了洗衣和熨衣(主要是衬衣衬裤)的服务,而且很便宜,洗一身内衣也就四五毛钱,为顾客提供了方便。澡堂还日渐淡化洗澡的休闲功能和娱乐功能,与此有关的服务项目减少了许多(如代买食品、叫外卖、捏脚等)。另外一个措施就是限制洗澡的时间,平时一般是两个小时,如果是节假日仅一个小时。到时候就下逐客令,这在过去的服务业是绝对没有的事。有的澡堂子采取超过规定时间增加收费的办法。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个纯政治化的社会,政治中心的北京尤甚。社会运动在澡堂子里也有反映。例如大跃进时,各行各业都跃进,澡堂也搞超声波、蒸馏水(后来北京澡堂几乎都卖蒸馏水就是从1958年开始的),蒸馏水的纯度要勇攀世界高峰、要达到几个“九”等。大跃进高潮中(1958年10月)出现了许多奇事,例如北京的服务单位都有跃进的数字指标,如电影院要放多少场电影(24小时连续放),要有多少观众;图书馆要有多少读者看书,借出去多少本书;澡堂子就要保证每天有多少顾客洗澡等等。
那时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跃进,没人来怎么办?有的是走出去,如图书馆把书用三轮车拉到工厂学校去借;电影院到学校放电影;澡堂子没法走出去,就派服务员在门口拉人洗澡,路过者如说我没带钱,那没关系,当时钱在人们心目中已经不起作用了,都快到共产主义了要钱干什么呀。如说“没工夫”,那也没关系,把人拽进来,服务员帮他脱衣服,进池子涮一过就出来,就算增加一个。文革当中,革命大批判进了澡堂。批判的矛头第一个就是解放前的“旧澡堂”,说那是剥削阶级、反动派的残渣余孽聚集的地方,我们要把它们扫荡干净;后来又强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即使是洗澡、睡觉也不例外(当时称无产阶级要占领“八小时以外”的阵地),服务员要提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上面说的“黄书”故事背景就是“全面专政”,去洗澡一不留神被专了政,也是件倒霉事。听说有人洗着澡被拉出批斗的,我没见过,但荒谬时代无奇不有。这样氛围下连“池子红”们也不敢唱传统戏了,而唱样板戏,如果荒腔走板那可是个政治问题,而且“板(儿)戏太直,没有传统戏一唱三叹的味道”。于是泡澡的少了,唱的更少了。
三十年前北京的澡堂子有一百多家,本来各有名号,文革中“扫四旧,立四新”,扫去了旧的,多以所在地址命名,方便是方便了,一听名字,就知道在哪,可是原有的文化气没了。一百多澡堂子中最有名的当属“清华池”“清华园”“华清池”“东升平”“一品香”等等。人们热衷以“华清”“清华”命名可能与当年杨贵妃“春寒赐浴华清池”有关。“清华”因与“清华大学”同名,遂成为相声的噱头。马三立说的《文章会》其中就有这样的包袱:
甲:“我大学毕业。”乙:“您哪个大学毕业的?”甲:“清华。”乙:“哪个清华?”甲:“北京的。说清华,还有哪的清华?北京的清华嘛。”乙:“啊。北京的清华,您先跟我说说北京的清华在哪?”甲:“北京的清华还在哪?在北京嘛。”乙:“北京的清华当然在北京。您跟我说说具体在哪条街上。”甲:“……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北边,八面槽那里。”乙:“清华园澡堂子啊——”
这个“包袱”一层一层地翻,最后一抖,效果极好,特别是让老北京来听。我也听过侯宝林说的这个段子,前面相同,最后用的是“东珠市口,开明戏院对面”。这是指清华池澡堂。
谈到洗澡、泡澡,老北京更重视消闲、娱乐这个主题。
我的“北京的符号”
2006年,7月初,暑热的一天,《新京报》评论版编辑来电说今天上午高考作文题目是《北京的符号》希望我也写一篇,第二日发表。我想,46年前,我也经历过这一场奋斗,那年的题目是《大跃进中的二三事》,前尘往事,思之可笑。
哪一个“符号”能代表北京?我想所谓“符号”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主观自然要受制于人的经历,因此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它可能有无数答案。笔者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住过老北京城内许多地方,还在北京慢慢变老,在这个城市里备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因此我心目中能代表北京的就是老北京城,或者简单地说就是老北京内外城和皇城。因为有了这些城墙与城楼才是完整的北京。
京剧《梅龙镇》(又名《游龙戏凤》),那位“风流天子”正德皇帝朱厚照对凤姐介绍说自己住在“那个大圈圈里套着小圈圈,小圈圈里套着黄圈圈”之中。“大圈圈”“小圈圈”“黄圈圈”就是完整的北京城。现在让我想起老北京来,有两个景致令我难忘,一个是大小院落里和买卖店铺门面前春夏秋三季必搭建的天棚,一个就是北京外、内、皇三套城墙和城门。天棚虽然少了,但只要有地方还可以搭建,而作为完整北京代表的城墙、城门楼却永远地消失了。
斑驳陆离老城墙是既是北京的屏蔽,又是北京立体的绿化带。城墙长满了杂草、荆棘,偶尔也会有棵亭亭如盖的小树,在墙垣上留下一片绿荫。城墙中间是一马平川,由着我们这些刚刚懂事的孩子疯跑。有时也跟着稍大一点的孩子翻草稞子,逮蛐蛐。登上北京城楼,可以俯瞰全城;如果是晴天,阳光下各色琉璃瓦反射着五色光辉,天穹则是一片碧蓝。在车如流水马如龙、软尘十丈的北京,荒野的城墙仿佛是条带状的农村插入了繁华的闹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