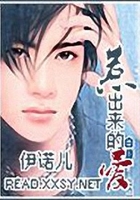第三天下午两点,乌云密布,气压很低,各组集合,毕业班到礼堂听传达文件。但去得同学很少,只有我们中文系二班一百多人去了(后来知道有反动学生的班才去)。礼堂显得空荡荡的,此时外面雷电大作,风雨交加。中文系总支书记陈某某宣读《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政治思想反动的学生的处理通知》和北京市委大学部、北京高教局关于贯彻中央决定的决定。礼堂静得出奇,每个人都是心怀惴惴,不知道是否会有什么倒霉的事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我更是自知难免。陈某某拖着他那河南腔,宣布清理反动学生运动开始,并说清理思想运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清理反动学生是解决敌我矛盾。这是对敌斗争的开始。他还宣读了划分反动学生的六条标准:基本核心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就是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对党的反修政策,追求民主自由等。会后大多数人松了一口气,他们解脱了,我粉墨登场了。
中文系1964年应届毕业生三百多人,分四个班,每班划两个反动学生,共八人。这八个属于内定的,不戴帽子,不给行政处分,按毕业生对待。一个公开的,戴上帽子,给予处分,不按毕业生对待,劳动考察期间每月只给生活费28元。其实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只是与同学私下聊天时,曾说到庐山会议和困难时期的经济状况,对于“三面红旗”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很痛心。另外,在学习“九评”(1963年到1964年之间,《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苏共中央给全体苏共党员公开信”的九篇社论)时,我曾提出个问题,同样是政权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为什么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就不能和平过渡,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就能够和平演变?不久有诗记此段心情:
超邈道心岂可求,天涯海角系浮鸥。刘郎偶题伤春赋,楚客长吟去国愁。
莫道三生如一梦,谁知万死即千秋。扁舟落叶中流去,不觉风飚浪打头。
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个集子所收的大多与个人经历有关的散文与随笔,或者说是多少带有点自传性质的文章。
写自传对于我们那一代中国人是不陌生的,我们生活在垂直的组织化的社会,你那点事总得让组织知道呀,因此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怎么讲求“个人隐私”的,把自己的事告诉组织,光嘴上说还不行,最好还是写,这就近于自传了。
1954年,我上初中,正逢“忠诚老实运动”,只要是在国家单位工作的,人人要写自传,而且要货真价实,不许吞吞吐吐。我上初中二年级时,有一篇作文题是“我的自传”,一个十三四岁孩子有什么可写的?但还得搜索枯肠,拼凑词句,装作大人的样子,发表对人生的感悟,真是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了。
到了高中,开始参加政治运动了,在红专大辩论中,批判个人主义。为了做到红专相兼,第一步就是向党交心,把丑陋的、不正确的思想向组织说清楚。写自幼以来的思想经历,这就近于思想自传了。依稀记得我曾写过:小时候,母亲老给我讲穷孩子认真苦读的故事,从而事业有成,考中进士,做了官,给祖宗争光。这就是自己为什么生在新社会而又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的原因,最后还要表态要与这种影响划清界限,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也许是个性所致吧,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总觉得自己跟不上社会的脚步,时时有掉队之感,例如学校组织大家到郊区参与亩产小麦120万斤的高产田的深翻土地活动,我就表示不理解而被校方从大跃进的行列中开除,并责令回学校写检讨,深挖错误的思想根源。这一般都要从家庭写起,按照社会的要求猜度你还没有降生前的情景。这是个包括家庭背景的自传了。再后来也许是自己命不好,或者说缺乏自我矫正的能力或习惯,不断地出错,不断地检讨,不断地挖犯错的根源,于是小时候的经历就不断地回到我的记忆中来,所以写自传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前两年,老同学和同事闵家胤先生拿出了一本50年前(1960年)为全班同学写的小传,自然也包括我的小传。我上高中时闵家胤是我们班的班长,1960年考大学时,他立志要考北大哲学系,没想到给分到不入流的二类学校——北京工农师范学院中文系,与我沦落到一个学校、一个系。他很生气,但也办法。
1960年的高考是非常奇怪的,从上高三开始,北京教育局想要使北京高考成绩超过福建、上海(50年代老是福建、上海、北京是高考考分的前三名),从高三开始要求人人住校,严格执行作息制度,加大复习作业量,三天两头搞模拟考试,要求把成绩提上去。当时的北京教育局孙国梁局长亲自主持两次全体高三毕业生参加的誓师大会,全体同学也以获取高考高分自我勉励。可是考完之后,考分突然不作数了(那年发榜非常晚,到8月下旬大家才拿到通知书,其中必有反复过程,但至今尚未揭露出来),大学录取完全靠政审。政审时有四个戳子:破格录取,一般录取,降格录取,不宜录取。大约闵家胤就属于“降格录取”(他是班主席,本身不会有问题,但父亲是国民党航空公司的起义人员,这是会影响录取的)的,所以,他心里憋了一股气,早早报了到,表示“服从分配”。但到了学校,没事情做,就写了这份同学小传。他说,文革当中,许多文字资料都被学生抄走了,包括日记等,但写小传的本子却无意被保留下来了。于是就可以看到50年前,我在先进同学心目中的印象:
王学泰
旧地主官僚家庭出身,解放后父亲劳改。家开补地毯作坊,到现在还是私营单干。这是一个在旧诗词、旧小说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人物。中西若干唯心主义哲学著作、一大堆历史知识、美学知识、音韵文字学知识等等,杂七杂八充塞在他头脑里。他追慕的人格是:看破红尘,疏世独立,清高飘逸,不骛名利,放荡不羁,冷嘲热讽的亡臣隐士。他向往的生活是:一屋线装书,一壶清茶。一切新事物他都用指手画脚的嘲笑来表示厌恶,一切积极分子他都认为是营营追名逐利的小人。在思想上他常说自己“又走进了死胡同”——他最终决定去追求丰富的学识。这样,他就有了傲世人不学无术的资本,生活就有了内容和乐趣。任何新事物的缺点、失败他都欣喜,他都用来证明自己是时代目光犀利的受难者。高一高二时,他是班上的“白旗”,各种反面言论的维护者,受到过多次批判。劳动中他踏实苦干,有些进步。这个人有哪几项好的品质,使他还能跟随时代的潮流呢?高一高二时他敢于谈出自己真实的思想,追求真理;他时时感到世界发展得太快了,得阅读些新书;他珍视友情。
他是个白脸虚胖子,睡眼惺忪,外号Cnamb(俄文“睡”),眼镜,手表,府绸衬衫。现跟我同院同系。
开始说家庭的一段不确切,我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制作仿古地毯,抗战之前曾一度发达过,日本占领北京后,把羊毛列入军用物资,不许民间经营,家庭日益走下坡路。最后一句是完全正确,我们俩同院同系,困难时期北京工农师范学院解散,学生教师都归并到北京师范学院,我们仍然是同院同系。其他的如不追求进步、喜欢读书也是事实,但不像他说的读那么多书,他说的那种程度我50年后的现在也没达到。其实当时仅仅是“追求丰富知识”乱读书而已,而且乱读了许多没有什么用的书,因书而兴奋,缘书而倒霉。
在高中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可以说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于是连续的倒霉就不可避免。1964年大学毕业时清理思想就被清理了出来,成为“反动学生”,那年师院毕业1000余人,公开划的就我一个,但还有“内定”的八位,就是不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还分配工作,但分配后第一年去农场劳动,在档案上写上。闵家胤兄毕业也“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不过还属于“内定”的,先劳动了一年,才分到中学教书。我是在各种苦难中辗转,后事出偶然,又被送入监狱。
厄运真正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安定了。我也有了一份能把谋生与爱好统一起来的工作,后来成家,有了妻小,直到退休,不愁吃穿冻馁,再也没有因为一两句话说得或写得不当,有人找麻烦了,有了点为人们艳羡的“庸福”。龚定庵说“文格渐卑庸福近”,我的“文格”从来也没高过,“庸福”冉冉而来,也属正常吧。
前两年,工人出版社的王建勋兄没有退休的时候,约我写个自传。我说只想分着写点各个生活阶段的感受。比如读了几十年的书,我写了一篇《读书随想录》五万多字,1999年《十月》杂志分为两段发表;还想写一篇《娱乐记往录》,记北京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看电影、看话剧、听戏、听音乐等有趣的生活。其他如在南口劳改、在农村劳动、在监狱的生活和近三十年在学术界活动都不乏可记之处。他说:这不就是“自传”吗?快写吧!可我觉得规模太大,他又催稿很急,就为他写了一本别的书,所谓“自传”就搁下了。当然如果有报刊相约,往事还是经常出现在笔端,因此就有了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得以裒为一集。
集子借用了苏东坡的《定风波》中的名句,非敢以坡翁自拟,而是反思自己一生的缺点真是与他有相似之处,都是没有做到孔门的两大告诫“节饮食,慎言语”。坡公感慨这是“人之所共知而难能者”(《东坡易传》),所以他明知一肚皮装的都是“不合时宜”的,但又偏偏寄之于诗,结果是闹出了“乌台诗案”,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差点没能出来。本来因诗得罪,蒙皇恩浩荡,大年除夕被释放了,总应该接受点教训了吧,可是一出狱坡老的手又痒了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又给他酝酿了后祸。
虽然我也很早就知道这两大金律,但总觉得这是对有权有势的君子说的。他们生命金贵,生老病死关系着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福祉;由于“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口”之事亦大矣,要把好这一关。至于平民百姓,命如蝼蚁,言若飘尘,爱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前提是别闹“自然灾害”和买得起),口无遮拦也没多大关系。到老了才明白了这两条的普适性,别以为它们与自己无关。也可以说这是传统文化贡献给人类的普世价值吧。
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坡翁贬居黄州之时,玩赏于沙湖道上,遇雨。雨具先去,同游之人狼狈不堪,而坡公却浑然不觉,仍然徜徉在山山水水之间(这是苏东坡派头,是我等俗人学不来的)。一会儿雨停了,他写下这首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虽然才情不能望坡公项背,但对风雨的耐受,差可相拟,因此不惮众人哂笑,用以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