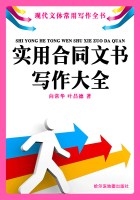小孩若爱啼啼哭哭,睡不安宁,便写一张字帖,贴在行人小便的处所,上写着: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
文字的神力真不少。
小孩跌了一交.受了惊骇,那是骇掉了“魂”了,须得“叫魂”。魂怎么叫呢?到那跌交的地方,撒把米,高叫小孩子的名字,一路叫回家。叫名便是叫魂了。
小孩渐渐长大了,在村学堂同人打架,打输了,心里恨不过,便拿一条柴炭,在墙上写着诅咒他的仇人的标语:“王阿三热病打死。”他写了几遍,心上的气便平了。
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她受了隔壁王七嫂的气,便拿一把菜刀,在刀板上剁,一面剁,一面喊“王七老婆”的名字,这便等于乱剁王七嫂了。
他的父亲也是“名教”的信徒。他受了王七哥的气,打又打他不过,只好破口骂他,骂他的爹妈,骂他的妹子,骂他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便算出了气了。
据江绍原先生的考察,现在这一家人都大进步了。小孩在墙上会写“打倒阿毛”了。他妈也会喊“打倒周小妹”了。他爸爸也会贴“打倒王庆来”了(《贡献》九期,江绍原《小品》页七八)。
他家里人口不平安,有病的,有死的。这也有好法子。请个道士来,画几道符,大门上贴一张,房门上贴一张,毛厕上也贴一张,病鬼便都跑掉了,再不敢进门了。画符自然是“名教”的重要方法。
死了的人又怎么办呢?请一班和尚来,念几卷经,便可以超度死者了。念经自然也是“名教”的重要方法。符是文字,经是文字,都有不可思议的神力。
死了人,要“点主”。把神主牌写好,把那“主”字上头的一点空着。请一位乡绅来点主。把一只雄鸡头上的鸡冠切破,那位赵乡绅把朱笔蘸饱了鸡冠血,点上“主”字。从此死者的灵魂遂凭依在神主牌上了。
吊丧须用挽联,贺婚贺寿须用贺联;讲究的送幛子,更讲究的送祭文寿序。都是文字,都是“名教”的一部分。
豆腐店的老板梦想发大财,也有法子。请村口王老师写副门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也可以过发财的瘾了。
赵乡绅也有他的梦想,所以他也写副门联:“总集福荫,备致嘉祥。”
王老师虽是不通,虽是下流,但他也得写一副门联:“文章华国,忠孝传家。”
豆腐店老板心里还不很满足,又去请王老师替他写一个大红春帖:“对我生财”,贴在对面墙上,于是他的宝号就发财的样子十足了。
王老师去年的家运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来,拜了天地,洗净手,拿起笔来,写个红帖子:“戊辰发笔,添丁进财。”他今年一定时运大来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讳的。古时候,父名晋,儿子不得应进士考试。现在宽的多了,但避讳的风俗还存在一般社会里。皇帝的名字现在不避讳了。但孙中山死后,“中山”尽管可用作学校地方或货品的名称,“孙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实同志都应该称他为“先总理”。
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去。
北京下来之后,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今天又有人提议改南京做“中京”了。还有人郑重提议“故宫博物院”应该改作“废宫博物院”。将来这样大改革的事业正多呢。
(《名教》)
“名教”国家的祖传法宝
前不多时,南京的《京报副刊》的画报上有一张照片,标题是“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宣传处艺术科写标语之忙碌”。图上是五六个中山装的青年忙着写标语;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满铺着写好了的标语,有大字,有小字,有长句,有短句。
这不过是“写”的一部分工作;还有拟标语的,有讨论审定标语的,还有贴标语的。
五月初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我时时往来淞沪铁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钟的旅行所见的标语总在一千张以上;出标语的机关至少总在七八十个以上。有写着“枪毙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活埋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杀尽矮贼”而把“矮贼”两字倒转来写,如报纸上寻人广告倒写的“人”字一样。“人”字倒写,人就会回来了;“矮贼”倒写,矮贼也就算打倒了。
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有人说,这是从苏俄学来的法子。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没有看见墙上有一张标语。标语是道地的国货。是“名教”国家的祖传法宝。
试问墙上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同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或“抬头见喜”,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衣钵?
试问墙上贴一张“活埋田中义一”,同小孩子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法宝?
试问“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同王阿毛贴的“阿发黄病打死”,有什么分别?王阿毛尽够做老师了,何须远学莫斯科呢?
自然,在党国领袖的心目中,口号标语是一种宣传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中小学生的心里,在第九十九师十五连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员的心里,口号标语便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罢了。如果“打倒帝国主义”是标语,那么,第十区的第七小学为什么不可贴“杀尽矮贼”的标语呢?如果“打倒汪精卫”是正当的标语,那么“活埋田中义一”为什么不是正当的标语呢?
如果多贴几张“打倒汪精卫”可以有效果,那么,你何以见得多贴几张“活埋田中义一”不会使田中义一打个寒噤呢?
故从历史考据的眼光看来,口号标语正是“名教”的正传嫡派。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的心里,墙上贴一张“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正等于门上写一条“姜太公在此”,有灵则两者都应该有灵,无效则两者同为废纸而已。
我们试问,为什么豆腐店的张老板要在对门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岂不是因为他天天对着那张纸可以过一点发财的瘾吗?为什么他元旦开门时嘴里要念“元宝滚进来”?岂不是因为他念这句话时心里感觉舒服吗?
要不然,只有另一个说法,只可说是盲从习俗,毫无意义。张老板的祖宗下来每年都贴一张“对我生财”,况且隔壁剃头店门口也贴了一张,所以他不能不照办。
现在大多数喊口号,贴标语的,也不外这两种理由:一是心理上的过瘾,一是无意义的盲从。
少年人抱着一腔热沸的血,无处发泄,只好在墙上大书“打倒卖国贼”,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写完之后,那二尺见方的大字,那颜鲁公的书法,个个挺出来,好生威武,他自己看着,血也不沸了,气也稍稍平了,心里觉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于是他的一腔义愤,不曾收敛回去,在他的行为上与人格上发生有益的影响,却轻轻地发泄在墙头的标语上面了。
这样的发泄情感,比什么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谁不爱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惯例了,于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都照样做去:放一天假,开个纪念会,贴无数标语,喊几句口号,就算做了纪念了!
于是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于是老祖宗几千年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而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
(《名教》)
“名教”的哲学
我们试进一步,试问,为什么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或“枪毙田中义一”可以发泄我们的感情,可以出气泄愤呢?
这一问便问到“名教”的哲学上去了。这里面的奥妙无穷,我们现在只能指出几个有趣味的要点。
第一,我们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就是魂,我们至今不知不觉地还逃不了这种古老迷信的影响。“名就是魂”的迷信是世界人类在幼稚时代同有的。埃及人的第八魂就是“名魂”。我们中国古今都有此迷信。《封神演义》上有个张桂芳能够“呼名落马”;他只叫一声“黄飞虎还不下马,更待何时!”黄飞虎就滚下五色神牛了。不幸张桂芳遇见了哪吒,喊来喊去,哪吒立在风火轮上不滚下来,因为哪吒是莲花化身,没有魂的。《西游记》上有个银角大王,他用一个红葫芦,叫一声“孙行者”,孙行者答应一声,就被装进去了。后来孙行者逃出来,又来挑战,改名做“行者孙”,答应了一声,也就被装了进去!因为有名就有魂了(参看《贡献》八期,江绍原《小品》百五四)。民间“叫魂”,只是叫名字,因为叫名字就是叫魂了。因为如此,所以小孩在墙上写“鬼捉王阿毛”,便相信鬼真能把阿毛的魂捉去。党部中人制定“打倒汪精卫”的标语,虽未必相信“千夫所指,无病自死”;但那位贴“枪毙田中”的小学生却难保不知不觉地相信他有咒死田中的功用。
第二,我们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文字)有不可思议的神力,我们也免不了这种迷信的影响。这也是幼稚民族的普通迷信,高等民族也往往不能免除。《西游记》上如来佛写了“喳嘛呢叭醚畔”六个字,便把孙猴子压住了一千年。观音菩萨念一个“喳”字咒语,便有诸神来见。他在孙行者手心写一个“咪”字,就可以引红孩儿去受擒。小说上的神仙妖道作法,总得“口中念念有词”。一切符咒,都是有神力的文字。现在有许多人似乎真相信多贴几张“打倒军阀”的标语便可以打倒张作霖了。他们若不信这种神力,何以不到前线去打仗,却到吴淞镇的公共厕所墙上张贴“打倒张作霖”的标语呢?
第三,我们的古代圣贤也曾提倡一种“理智化”了的“名”的迷信,几千年来深人人心,也是造成“名教”的一种大势力。卫君要请孔子去治国,孔老先生却先要“正名”。他恨极了当时的乱臣贼子,却又“手无斧柯,奈龟山何!”所以他只好做一部《春秋》来褒贬他们,“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这种思想便是古代所谓“名分”的观念。
“名”是表物性的,“分”是表我的态度的。善名便引起我爱敬的态度,恶名便引起我厌恨的态度。这叫做“名分”的哲学。“名教”、“礼教”便建筑在这种哲学的基础之上。一块石头,变作了贞节牌坊,便可以引无数青年妇女牺牲她们的青春与生命去博礼教先生的一篇铭赞,或志书“列女”门里的一个名字。“贞节”是“名”,羡慕而情愿牺牲,便是“分”。女子的脚裹小了,男子赞为“美”,诗人说是“三寸金莲”,于是几万万的妇女便拼命裹小脚了。“美”与“金莲”是“名”,羡慕而情愿吃苦牺牲,便是“分”。现在人说小脚“不美”,又“不人道”,名变了,分也变了,于是小脚的女子也得塞棉花,充天脚了。
(《名教》)
墙上的符箓与心中的鬼
——现在的许多标语,大都有个褒贬的用意:宣传便是宣传这褒贬的用意。说某人是“忠实同志”,便是教人“拥护”他。说某人是“军阀”,“土豪劣绅”,“反动”,“反革命”,“老朽昏庸”,便是教人“打倒”他。故“忠实同志”、“总理信徒”的名,要引起“拥护”的分。“反动分子”的名,要引起“打倒”的分。故今日墙上的无数“打倒”与“拥护”,其实都是要寓褒贬,定名分。不幸标语用的太滥了,今天要打倒的,明天却又在拥护之列了;今天的忠实同志,明天又变为反革命了。于是打倒不足为辱,而反革命有人竟以为荣。于是“名教”失其作用,只成为墙上的符箓而已。
两千年前,有个九十岁的老头子对汉武帝说:“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两千年后,我们也要对现在的治国者说:
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
一千多年前,有个庞居士,临死时留下两句名言:
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
“实诸所无”,如“鬼”本是没有的,不幸古代的浑人造出“鬼”名,更造出“无常鬼”,“大头鬼”,“吊死鬼”等等名,于是人的心里便像煞真有鬼了。我们对于现在的治国者,也想说:
但愿实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
末了,我们也学时髦,编两句口号:
打倒名教!名教扫地,中国有望!
(《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