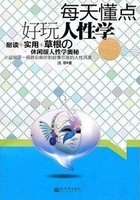东西方文明的不同
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只可以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们说“不知足是神圣的”(Divine Discontent)。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
固然,真理是无穷的,物质上的享受是无穷的,新器械的发明是无穷的,社会制度的改善是无穷的。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有一器的满足,改良一种制度有一种制度的满意。今日不能成功的,明日明年可以成功;前人失败的,后人可以继续助成。尽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满意;无穷的进境上,步步都可以给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所以大诗人邓内孙(Tennyson)借古英雄Ulysses的口气歌唱道:
然而人的阅历就像一座穹门,
从那里露出那不曾走过的世界,
越走越远永永望不到他的尽头。
半路上不干了,多么沉闷呵!
明晃晃的快刀为什么甘心上锈!
难道留得一口气就算得生活了?
……
朋友,来罢!
去寻一个更新的世界是不会太晚的。
……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回来了,剩下的还不少呢。
现在虽然不是从前那样掀天动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们毕竟还是我们——
光阴与命运颓唐了几分壮志,
终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寻,去发现,
永不退让,不屈伏。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不是人的文明
西方新文明和东方古文明的优劣,近年来颇有人出力争论,其实这是很明白清楚的问题,有眼睛的都应该看得出,哪有争议的余地。简单说来,中国的儒家思想也未尝不想做到一种“正德、利用、厚生”的文明。只可惜一班道士要无为,后来又添了一班和尚也要无为。无为是一条死路,万走不上“正德、利用、厚生”的目的地去。果然,大家讲无为,只好决心不要做人了,只好希望做神仙、做罗汉,成佛升天。于是中国的文明便成了仙佛的文明。仙佛的文明就是不要做人而妄想成仙、成佛的文明,这种文明便不是人的文明。
这种不是人的文明有种种奇怪的现状。他们妄想仙佛的三十二种庄严,七十二般变化,却忘了一身的龌龊,一家的污秽。他们在那不洁的环境里住惯了,不知不觉地把他们的龌龊污秽加在神仙的身上去。于是有烂脚的神仙,嗜痂的神仙,遍体生疮的活佛。这种理想反照回来,神仙菩萨都可以污秽不洁,何况凡人呢?于是有“躐蹋躐蹋,吃了做菩萨”的成语了。
他们妄想仙佛的长生不死,腾云来去,却不想想法子改造他们的轿子和舢板船,也不想想法子改良他们的医药。他们妄想仙佛的庄严净土,嫏嬛福地,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却不睁开眼睛看看他们府上的满地鸡屎浓痰,厨下的满地猪屎牛粪,街上的遍地毛厕臭水,野外的满地棺材坟墓。他们望着天上,却完全忘记了地下。
疾病来了,只好求神、求仙方、许愿。人死了,都是命该如此。瘟疫来了,只好求瘟神。瘟神无灵时,只好叹口气,闭门束手等死。死一家,只是一家命该绝。死一村,只是一村命该绝。至于猪瘟、牛羊瘟、牲口瘟,更是没有法子的事。万物之灵的人,尚且顾不得自己,何况哑口说不出苦痛的牲畜呢?
这便是那不是人的文明。不是人的文明的唯一特点便是人命不值钱。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如电如露,值得什么!因为人命不值钱,故医药之学三千年中从不曾列于六艺,列于四科,列于太学学科之中。因为人命不值钱,故公共卫生三千年中从不曾列入国家行政之内。
这便是东方的精神文明的怪现状。
(《公共卫生与东西方文明》)
混同的世界文化
所以我们说,一百四十年的轮船,一百二十年的火车,一百年的电报,五十年的汽车,四十年的飞机,三十年的无线电报——这些重要的交通工具,在区区一百年之内,把地面更缩小,把种种自然的阻隔物都打破了,使各地的货物可以流通,使东西南北的人可以往来交通,使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都可以彼此接触、彼此了解、彼此交换。这一百多年,民族交通、文化交流的结果,已经渐渐的造成了一种混同的世界文化。
以我们中国来说:无论在都市、在乡村,都免不了这个世界文化的影响。电灯、电话、自来水、公路上的汽车、铁路上的火车、电报、无线电广播、电影、空中飞来飞去的飞机,这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不用说了,纸烟卷里的烟草,机器织的布,机器织的毛巾,计算时间的钟表,也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于我们人人家里自己园地的大豆、老玉米,也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大豆是中国的土产,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有用的一种植物了。老玉米是美洲的土产,在四五百年当中,传遍了全世界,久已成为世界公用品,很少人知道他是从北美来的。
反过来看,在世界别的角落里,在欧洲、美洲的都市与乡村里,我们也可以随地看见许多中国的东西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磁器、中国的铜器、中国画、中国雕刻、中国蚕丝、中国刺绣,是随地可以看见的。茶叶是中国去的,橘子、菊花是中国去的,桐油是全世界工业必不可少的。中国春天最早开的迎春花,现在已成了西方都市与乡村最常见的花了。西方女人最喜欢的白菊花、栀子花,都是中国去的。西方家园里、公园里,我们常看见的藤萝花、芍药花、丁香花、玉兰花,也都是中国去的。
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交通,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翻成白话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老玉米现在传遍世界,难道是洋枪大炮逼我们种的么?桐油、茶叶传遍了世界,也不是洋枪大炮来抢去的。小的小到一朵花一个豆,大的大到经济政治学术思想都逃不了这个文化自由选择,自由流通的大趋向,三四百年的世界交通,使各色各样的文化有个互相接近的机会。互相接近了,才可以自由挑选,自由采用。
(《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创造与模仿
凡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模仿的人决不能创造。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名词,其实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古人说的最好:“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我们不要被新名词骗了。新名词的模仿就是旧名词的“学”字:“学之为言效也”是一句不磨的老话。例如学琴,必须先模仿琴师弹琴;学画,必须先模仿画师作画;就是画自然界的景物,也是模仿。模仿熟了,就是学会了,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练的细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这一点功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叫做创造。
凡不肯模仿,就是不肯学人的长处。不肯学如何能创造?伽利略(Glileo)听说荷兰有个磨镜匠人做成了一座望远镜,他就依他听说的造法,自己制造了一座望远镜。这就是模仿,也就是创造。从十七世纪初年到如今,望远镜和显微镜都年年有进步,可是这三百年的进步,步步是模仿,也步步是创造。一切进步都是如此:没有一件创造不是先从模仿下手的。孔子说的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就是一个圣人的模仿。
懒人不肯模仿,所以决不会创造。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那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我们到了民族中衰的时代,只有懒劲学印度人的吸食鸦片,却没有精力学满洲人的不缠脚,那就是我们自杀的法门了。
(《信心与反省》)
贫乏的固有文化
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在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我们且谈谈老远的过去时代罢。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我们的文化的贫乏了。尤其是造形美术与算学的两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
我们试想想,《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正和孟子先后同时;在那么早的时代,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大落后了!(少年爱国的人何不试拿《墨子·经上篇》里的三五条几何学界说来比较《几何原本》?)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骄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缺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哪里去了?
(《信心与反省》)
无根据的信心没有力量
信心是我们需要的,但无根据的信心是没有力量的。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
(《信心与反省》)
反省而后知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