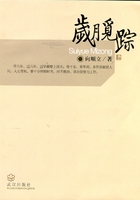《鹅妈妈的故事》在最初出版的时候,却用的另外一个书名:《从前的故事》(Histoire de Temps passé)。作者的署名是他儿子的名字:贝洛尔·达尔芒戈(Perrault d’Armancour)。
因为这一集中所包含的八篇故事——《林中睡美人》(La Belleau Bois Dormant),《小红帽》(Le Petit Cbaper-on Rouge),《蓝须》(Barbe Bleue),《猫主公》或《穿靴的猫》(Maitre Chat;ou,Le Chat Botté),《仙女》(Les Fées),《灰姑娘》或《小玻璃鞋》(Cendrillon;ou,La Petite Pantoufle de Verre),《生角的吕盖》(Riquetà la Houpe),《小拇指》(Le petit Poucet)——都是些流行于儿童口中的古传说,并不是贝洛尔的聪明的创作;他不过利用他轻倩动人的笔致把它们写成文学,替它们添了不少的神韵。又为了他自己曾竭力地反对过古昔,很不愿意用他的名字出版这本复述古昔故事的小书,因此却写上了他儿子的名字。所以他便把这些故事,故意用孩童的天真的语气表出。因了这个假名的关系,又曾使不少人费过思索和探讨,猜了很多时候的谜。
至于这集故事之又名为《鹅妈妈的故事》的原故,也曾经不少人的研究。大部分人以为在一首古代的故事歌中曾说起过一匹母鹅讲故事给她的小鹅儿听,而在这本故事第一版的首页插图中画着一个在纺纱的老妇人,身旁有三个孩子,一个男的和两个女的,在这图下,有着“我的鹅妈妈的故事”的字样,所以便以为贝洛尔是将古代的故事歌中的母鹅人化了而拟出这个书名的。此外,还有许多对于这书名的不同的推解,我想,这于小朋友们没有什么需要,也不必很累赘地费许多文字来多说了。
至于这几篇故事的真价值,我也想,小朋友们当然已能自己去领略,不必我唠唠叨叨地再细述了。但是,有一桩事要先告罪的,就是:这些故事虽然是从法文原本极忠实地译出来的,但贝洛尔先生在每一故事终了的地方,总给加上几句韵文教训式的格言,这一种比较的沉闷而又不合现代的字句,我实在不愿意让那里面所包含的道德观念来束缚了小朋友们活泼的灵魂,竟自大胆地节去了。
最后,还得补说一句:沙尔·贝洛尔是死在一千七百零三年,距这本故事集之出版,只有六年;在这六年之中,我们的作者并不曾写过比这本书更著名的故事。
国际劳动者演剧会
在莫斯科,去秋成立了一个“国际劳动者演剧会”,是由各劳动者俱乐部的剧团和苏维埃职业剧团组织成的,将扩大到和各国的一切革命的戏剧团体携手。
“国际劳动者演剧会”搜集各国的无产阶级戏剧作品;将这些作品译成各国的语言,而且用种种方法使这些作品民众化;将这些剧本送给各分会和会员,作一个剧本的交换,而在劳动者的俱乐部和剧场上演。
在今年夏天,“国际劳动者演剧会”想在苏联表演德国劳动者优伶的戏,和曾演过《改过所中的反叛》的“青年演剧者”的戏,以及巴黎的“艺术戟队”团的,和纽约的劳动者剧团“新戏剧作家”的戏。
在本年八月,“国际劳动者演剧会”将召集一个劳动者演剧的国际大会。
阿耶拉
阿耶拉(Ramon Perez de Ayala)是西班牙当代的出众的小说家,同时也是诗人,批评家,散文家,是那踵接着被称为“九十八年代”的乌拿莫诺、阿索林、巴罗哈、伐列·英克朗等一群人的新系代中的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于一八八○年生于阿斯都里亚斯(Asturias),现在还活着。在去年(一九三一年)西班牙革命以后,他出任为英国公使。虽则已是五十二岁的老人了,但是他底那种矍铄的精神,在行动上以及在著述上,是都足以使后生们都感到可畏的。
他底文学生活是从诗歌开始的。他一共出了三部诗集:《小径的和平》(La Paz del Sendero,一九○四),《不可数的小径》(ElSendero Innum erable,一九一六),《浮动的小径》(ElSendero Andante,一九二一)。他的诗都是用旧的韵律和鲜明的思想(Ancho ritmo,clara idea)。早年的诗虽则颇受法国象征派诗人们,特别是法朗西思·耶麦底影响,但有时他底诗甚至比耶麦底更深刻点。
使他一跃而成为西班牙文坛的巨星,并成为世界的大作家的,是他底小说。《倍拉尔米诺和阿保洛纽》(Belarminoy Apolonio),《蜜月苦月》(Luna de Miel Luna de Hiel),《乌尔巴诺和西蒙娜底操劳》(Los Trabajos de Urbanoy Simona),《黄老虎》(Tigre Juan)等书,都使他底世界的声誉一天天地增加起来,坚固起来。
从阿耶拉底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特点。第一,是他底文章手法上的特点:他底微妙婉转的话术,他底丰富的用字范围,他底丰富、流畅、娇媚而又冷静的风格。其次,是他底那种尖锐、奸诡、辛辣而近于刻薄的天才(而它又是隐藏在他所聪敏地操纵着的迂回曲折的语言的魅力中的)。凭了这两种特点,接触了英国的“幽默”作家及他本国的诸大师,又生活在西班牙的那些奇异的人物——大学生、发明者、流氓、政客、教士、斗牛者等——的氛围气中,他的作品是当然就连法国的弗洛贝尔(如果他能看见)都要自愧不如的了。
《黎蒙家的没落》(La Caida de los Limones)是在一九一六年出版的题名为《泊洛美德奥》(Prometeo)的三个诗的中篇小说(Novelas poemáticas)中的一篇,是阿耶拉的杰作之一,颇足以代表他的全部的风格。这是一篇以Casa de huéspedes(寄寓)底古典的描写开始的最残酷的故事,而阿耶拉又是带着那种不怕伤了读者的刁恶、热情和冷嘲讲出来的。
诗论零札(一)
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
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
单是美的字眼的组合不是诗的特点。
象征派的人们说“大自然是被淫过一千次的娼妇。”但是新的娼妇安知不会被淫过一万次,被淫的次数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要有新的淫具,新的淫法。
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
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法文:变异)。
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劣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脚的鞋子。
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
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种情绪的形式。所谓形式,决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决非新的字眼的堆积。
不必一定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我不反对拿新的事物来做题材),旧的事物中也能找到新的诗情。
十一
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
十二
不应该有只是炫奇的装饰癖,那是不永存的。
十三
诗应该有自己的originalité(法文:特征),但你须使它有cosmopolité(法文:普遍)性,两者不能缺一。
十四
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十五
诗应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诗本身就像是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
十六
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写出来。这种笔触又须是活的,千变万化的。
十七
只在用某一种文字写来,某一国人读了感到好的诗,实际上不是诗,那最多是文字的魔术。真的诗的好处并不就是文字的长处。
诗论零札(二)
竹头木屑,牛溲马勃,运用得法,可成为诗,否则仍是一堆弃之不足惜的废物。罗绮锦绣,贝玉金珠,运用得法,亦可成为诗,否则还是一些徒炫眼目的不成器的杂碎。
诗的存在在于它的组织。在这里,竹头木屑,牛溲马勃,和罗绮锦绣,贝玉金珠,其价值是同等的。
批评别人的诗说“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是一种不成理之论。问题不是在于拆碎下来成不成片段﹐却是在搭起来是不是一座七宝楼台。
西子捧心,人皆曰美,东施效颦,见者掩面。西子之所以美,东施之所以丑的,并不是捧心或眉颦,而是他们本质上美丑。本质上美的,荆钗布裙不能掩;本质上丑的,珠衫翠袖不能饰。
诗也是如此,它的佳劣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有“诗”的诗﹐虽以佶屈聱牙的文字写来也是诗,没有“诗”的诗,虽韵律整齐音节铿锵,仍然不是诗。只有乡愚才会把穿了彩衣的丑妇当作美人。
说“诗不能翻译”是一个通常的错误。只有坏诗一经翻译才失去一切,因为实际它并没有“诗”包涵在内,而只是字眼和声音的炫弄,只是渣滓。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中都永远保持着它的价值。而这价值,不但是地域,就是时间也不能损坏的。
翻译可以说是诗的试金石,诗的滤箩。
不用说,我是指并不歪曲原作的翻译。
韵律齐整论者说:有了好的内容而加上“完整的”形式,诗始达于完美之境。
此说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仔细想想,就觉得大谬。诗情是千变万化的,不是仅仅几套形式和韵律的制服所能衣蔽。以为思想应该穿衣裳已经是专断之论了(梵乐希:《文学》),何况主张不论肥瘦高矮,都应该一律穿上一定尺寸的制服?
所谓“完整”并不应该就是“与其他相同”。每一首诗应该有它自己固有的“完整”,即不能移植的它自己固有的形式,固有的韵律。
米尔顿说,韵是野蛮人的创造;但是,一般意义的“韵律”,也不过是半开化人的产物而已。仅仅非难韵实乃五十步笑百步之见。
诗的韵律不应只有浮浅的存在。它不应存在于文字的音韵抑扬这表面,而应存在于诗情的抑扬顿挫这内里。
在这一方面,昂德莱·纪德提出过更正确的意见:“语辞的韵律不应是表面的,矫饰的,只在于锁骼的语言的继承;它应该随着那由一种微妙的起承转合所按拍着的,思想的曲线而波动着。”
定理︰
音乐︰以音和时间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
绘画︰以线条和色彩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
舞蹈︰以动作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
诗︰以文字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
对于我﹐音乐、绘画、舞蹈等等﹐都是同义字﹐因为牠们所要表现的是同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