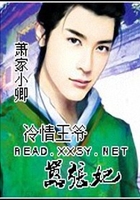对于仓央嘉措来说,成了达赖喇嘛,住进布达拉宫,仅仅只是地位的提升,并没有掌握任何实权。时间久了,他的政治意识更加淡薄,拉藏王如何了,谁在掌权,他并不在意。真正为这些事头疼的是第巴桑杰甲措。拉藏汗的事让他坐卧不安,这个他的头号政敌正如一颗明星般冉冉升起。在五世圆寂的问题上,桑杰甲措已经得罪了朝廷,处于守势,而拉藏汗的势力却在日渐壮大。虽然作为第巴有着六世宗教的威信和行政大权,出了问题只要把六世送到一线,那么一切倒也好办了,可政治舞台毕竟非同一般,必须心狠手辣,只怕六世处理不好。所以现在所有棘手的事情也只能由他本人来面对了。
仓央嘉措再次来到仁珍旺姆的碉楼时,没有注意到门前放着口铁瓮,他一脚踢翻了然后才发现多了样东西,上面还用纤细的字体写着:
留银十二两,方能进门。
仓央嘉措看了忍不住笑了,他把铁瓮扶好,走了过去。门是紧锁着的,他礼貌地叩了叩门,没有动静,窗户倒是一下子开了,里面探出个人影来,正是仁珍旺姆。
她指了指那个铁瓮,又指了指门。
仓央嘉措心领神会,放进十二两银子。大门开了,然而仁珍旺姆并不理他而是径直向里走去,从大门到二楼,仁珍旺姆的卧房一共有三道门,每道门前竟都放了一个铁瓮,上面都用绢帛写着:留银十二两,方能进门。
仁珍旺姆走得极快,她进了一扇门就把门关上,等仓央嘉措跟来时,又只有放了银子才能再开。
仓央嘉措越往里走,越感觉蹊跷,难道仁珍旺姆每见一个人都要这么多银子?他走到仁珍旺姆的卧房时已经面露愠色。太过贪恋钱财的女人,心中一定是不善的。他这样想着。
“你可记得我上次问你的问题,你到底是哪家贵族?要知道,每个贵族都恨不得把自己的族徽刻在每件事物上,你是宇妥·宕桑汪波?还是郎堆·宕桑汪波?或者是多噶·宕桑汪波?”仁珍旺姆问道。
仓央嘉措张口结舌,自己随便想的名字哪来的徽号呢?
仁珍旺姆见他不语又说道:“你家族一定是很大的,你父亲也一定是管教你很严格的。你来我这儿,只是为了一时之欢,对吧?”
仓央嘉措仿佛吞咽了苦果,他哪里是为了一时之欢呢?他是真心喜欢她啊,希望她住进他的心里,他想为她写诗、读诗,和她白头到老。
仁珍旺姆说完就走了出去,收起门前的三个铁瓮。她把银子全部倒了出来,细数了一遍才收起来。
夜晚的星空是绚烂的,仓央嘉措跟着仁珍旺姆走到了林卡。这是拉萨城中最偏远的一处林卡。仓央嘉措躺了下来,柔软的青草垫在他的背后,他仰着头,专注地望着天空。仁珍旺姆坐着,手里扯着一根堇草把玩着。
仓央嘉措说:“你看,这夜空多美啊,繁星缀在上面,伸出一根手指就能遮住一片。”
他又看了一会儿说道:“恐怕这样的星空只有在没有月亮的晚上才有,每一颗星星都闪着光。”
这时,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倏然划过,仓央嘉措惊讶地叫了起来。他拉着仁珍旺姆,让她也一起躺下来看。
仁珍旺姆乖顺地躺在了仓央嘉措的臂膀上,仓央嘉措闻到了她身上的檀香味,淡淡的,很好闻。
仓央嘉措说:“若是还有下一颗流星出现,我们就能长长久久。”
仁珍旺姆笑了,她抚摸着仓央嘉措的脸,问道:“你为何不娶了我?”
仓央嘉措语塞,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他拉过了仁珍旺姆的手。她的手是冰冷的。
仓央嘉措岔开了话题:“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仁珍旺姆反问道:“那你可知我在想什么?”
仓央嘉措没有回答,而是唱了起来。他空灵的嗓音在静谧的夜空中回荡,悠远而深情:
抱惯娇躯识重轻,就中难测是密意,
输他一种觇星术,繁星弥天认得清。
仁珍旺姆幽幽地说道:“又念诗,诗歌又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当银子花。”
仓央嘉措的声音戛然而止,仿佛遭到了致命的一击,他愤怒地站起身,疾步离开了。
夜空一如来时般绚烂,只是草坡上只剩下了仁珍旺姆。夜凉如刀,割伤了两颗心。
仓央嘉措一走就是很多天,仁珍旺姆那几日常去拉萨城里贵族家的林卡游逛,希望能打听些消息。
接连很多天,整个拉萨出奇地平静,没有宕桑汪波的消息。他不是任何一家贵族的少爷。
仁珍旺姆心灰意冷。
她回到碉楼扯下了红绫,收了起来。
这一夜,她没有点灯。
外面也没有月亮,惨淡的星光忽明忽暗。
仁珍旺姆不知什么时候才睡着的。睡梦中,她又见到了母亲。
母亲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着。母亲已经白发丛生,脊背也佝偻着,但是走得很快。
她在前面反复说道:“嫁个人吧。”
仁珍旺姆看不清母亲的脸,忧伤地回答说:“想嫁之人,远在天涯。”
母亲说:“他不就住在布达拉宫里吗?”
仁珍旺姆一下子惊醒了,母亲的话还在耳边回响,她再也没有了一丝睡意。
泪水滴答滴答落在被褥上,渐渐洇成一片。她还是打破了自己的诺言,她哭了。
日光十分灼热,照在脸上如同细小的蝼蚁在爬。仁珍旺姆坐了起来,头像灌了铅般沉重。
她倚着窗户,等着她的宕桑汪波。
他来了,还是哼着初次惹她开门的那首歌。
长干小生最可怜,为立祥幡傍柳边,
树底阿哥须护惜,莫教飞石到幡前。
门一直开到她的卧房,今天门前没有出现一口铁瓮。她只是盼着,盼着他能一步步走到她这儿来。
两人重新举起了杯,欢声笑语一如平常。
仁珍旺姆说:“你再唱一曲,可好?”
歌声再次响起,她挥动着长袖,翩然起舞。仓央嘉措唱完,她笑着说:“听你唱了这么多,不如我也学着唱一首。”
她真的唱了一首,曲调合上了,却不如仓央嘉措欢快,反而有些悲切,她赶紧举起一杯酒,仰头灌了下去。
喝干了杯中酒,她提议道:“难得今日风和日丽,不如我们去赛马。输的人,今晚不许动,任凭对方处置,如何?”
仓央嘉措的脸红了,不知是因为美酒滋润的缘故,还是因为眼前美丽的仁珍旺姆。他依了她。
拉萨城外,一片开阔。两人各牵了一匹好马,仓央嘉措说:“我不欺负你,你先跑出半里,谁先到前面的山坡,谁就算赢。”
仁珍旺姆微笑着,突然朝仓央嘉措的马就是一皮鞭,马儿受惊,呼呼地跑开了,她也立刻追了上去。
微风带着草香,温柔地抚过他们。她告诉自己一定要赢,她一鞭鞭地抽打着马儿,可是渐渐地,她还是落下了。
仓央嘉措回头看她,露出得意的笑容。
两人在风里越跑越快,风也越来越急。眼看就要到前面的山坡了,仁珍旺姆抽出一根针猛地朝马屁股扎去,突如其来的剧痛让马疯狂地奔跑起来,由于颠簸得厉害,她几乎要抓不住缰绳了,但是她笑了,因为她即将超过仓央嘉措,她要赢了。
风似乎突然间化作了利刃,呼啸着向她袭来。她感觉脸颊很痛,像被生生地剥去了皮。
仓央嘉措在后面喊着什么,她听不到。
阳光终于漫过山坡,露出了头。马儿继续狂飙,然后突然直立起来,凄惨地嘶鸣了一声。仁珍旺姆看见了天空,然后土地斧斫般地向她砸了下来,她晕晕沉沉,失去了意识,只记得仓央嘉措那双绣着流云的松巴鞋朝她狂奔而来。
夜是如此的柔软,绸缎一般地将两人裹起。
仁珍旺姆伏在仓央嘉措的身上,他的肌肤滚烫得像一块烙铁。她仰着头,看着窗外。夜空中升起一弯弦月,弓如眉弯。
她闭上了眼,想见苍穹中有双漆黑的眸子在凝视着她,月是他的眉。
泪水滑落到仓央嘉措的身上。仁珍旺姆知道他不会察觉,他的心无比炽热,却不会只为她燃烧。
第二天清晨,仁珍旺姆又一次说道:“你不如娶了我吧。”
仓央嘉措不应她,她又说了一遍,他还是不应。
仁珍旺姆的心冷了,她起身背对着仓央嘉措说道:“你不知道吧?曾经宗本也是睡在你那个位置的,你要么留下银两,要么就等着我告到宗本那里。”
她转过身,眼神如冰冷的箭。
她看仓央嘉措不动,又说道:“你要是还眷顾我,就多来几次,但别忘了多带些银子。”
仓央嘉措眼里的光芒彻底消失了,他失魂落魄地站了起来,从怀里掏出一袋藏银,颤颤巍巍地把那些银子都撒到了地上,哐当,哐当……
声音钝拙,震碎了曾经连在一起的两颗心。
……
若你不是达赖,
若我早些遇见你,
若我还是当初那样,以为母亲的话是真的,
若我不是拉巴家的农奴,
若我可以多跟你久一些,
若我能再爱你深一些,不在乎你是否在我身边,
若你知道,我什么都没有了。
……
仓央嘉措回到了布达拉宫,失魂落魄,盖丹热了些糕点给他拿过去,顺便说了几句宽心的话。
“佛爷,可是为了仁珍旺姆姑娘伤心?”
仓央嘉措听到“仁珍旺姆”,脸色一下子阴沉起来。
盖丹又说道:“佛爷不值得为她伤心,我听拉萨城里的人说,这姑娘虽然长得美若天仙,可心肠是黑的。她贪财,谁要是见她一面,那都是要很多钱的。她对人的热度是要看那人口袋里银子的多少。”
仓央嘉措无力地挥了挥手,盖丹知趣地退下了。
夜深了,星空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仓央嘉措心凉如水,看着案前的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玉软香温被裹身,动人怜处是天真,
疑他别有机权在,巧为钱刀作笑颦。
……
飞来野鹜恋丛芦,能向芦中小住无,
一事寒心留不得,层冰吹冻满平湖。
……
我与伊人本一家,情缘虽尽莫咨嗟,
清明过了春回去,几见狂蜂恋落花。
他挥毫泼墨,写了一连串的诗歌,然后扔了笔,流着泪睡着了。
很多天过去了,仓央嘉措始终忘不了仁珍旺姆。他在龙王潭射箭时,总是想起仁珍旺姆对他说,若我先射完这五个苹果,你就留下来过夜。
唱歌时,他又会想起仁珍旺姆学着他的腔调唱他的诗。她总是看着不经意,其实心细如发。
仓央嘉措换了俗装,出门去了拉萨。
市井的热闹繁华已经不能吸引他的注意。他似乎并不想去仁珍旺姆的碉楼,却还是鬼使神差地站在了那里。
楼上的窗是紧闭的,他唤了一声:“仁珍旺姆。”
良久,没有人应答,他讪讪地拿出银袋喊道:“仁珍旺姆,我带银子来了。”
依旧无人应答。
他一直站着。心想,她若知道他来了,一定会开门的。
风一阵阵吹来,楼上的窗被吱吱呀呀地吹开了,里面空无一人。轰的一声,窗户又被重重地摔上了。
此后,再也没有了声响,除了风声,一片死寂。
注释:
①煨桑:用松柏枝焚起的霭霭烟雾,是藏族祭天地诸神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