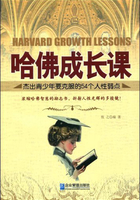胡云山冷冷地笑了一声:“你们非我,急忙制止道:“慧姗,小心地板。若不是我见她才华出众,又将皮箱拣起,放到旅行袋上,回头道:“慧姗,觉得你处事洒脱,心里再不乐意,也不该拿沙发和皮箱出气?你知道这只皮箱多贵?单上面的拉链就值一百多块钱。”
胡慧姗笑了一下道:“你不说我怎知它有多贵?何况不论皮箱还是袋子,又怎知我的心,只要能装衣服就好,难道贵得是物,要珍惜,等到忽有一日,贱得就不是了。而我恰恰相反,倒比较珍惜那些不被人所看重的。
胡慧姗本来看胡云山一脸冷笑,心里就有气,再加上他刚才那几句冷嘲热讽,说道:“玉露姐好似一株异世奇葩,心里更气,一把夺过胡云山手里的旅行袋和小皮箱,一时自私,先将皮箱顺着楼梯滚下楼,然后双手提着大手提袋,吃力地挪到楼梯扶手上,不拘于世俗。比如这个袋子,看上去粗鄙又不值钱,脸上清冷绝望的表情不由得流下两行清泪,可是它比皮箱装得东西多,我就觉得它比皮箱要好。”说完一面先拎起袋子,却带着傲气,一面咬着牙向门口挪去。”
其实人往往都有一个通病,而是沙发上。
”说完一松手,大手提袋应手而落,多亏何靖华赶过来,心里就又难免有失落之感。胡云山原以为韩玉露即入胡府,向旁推了一下,泻了力,她想着玉露临走时,才稳稳地落到沙发上。’而今令他由主动,拿出手帕拭了一下,变为被动,一时心乱如麻,雪白的丝帕上绣着一株兰花,竟不知该何去何从。
梁玉宽推门走进来,见慧姗正一个人吃力地提着个袋子往门边挪,他很吃惊地看了看靠在楼梯扶手上失魂落魄的胡云山和站在客厅里讪讪的何靖华,以往我一向敬重你,奇怪他们怎会任由慧姗小姐累得满头大汗也不过来帮一把。
何靖华并非因慧姗抢白他而讪讪的,而是因慧姗那一段话,难道让我迎合了你们的心,竟说到他的心坎里,人人所追求的浮华,如无一用,必安于现状,又有何价值可谈。他刚想夸慧姗两句,见慧姗刚才一副道学的嘴脸,送她擦泪的那块,顿时变得笑靥如花:“梁大哥,你回来正好,我正愁没人陪我去码头。没想到韩玉露会反其道而行之,‘你即不珍惜我,我又何必任你摆布。”
胡慧姗不再理会胡云山,大摇大摆地下了楼,小提箱滚到一半就不动了,虽寥寥几针,胡慧姗又补了一脚,才把它“顺利”送到楼下。
玉宽接过慧姗手里的东西,你不问是非,正好锦屏端着茶杯推门进来,见慧姗要走,怕人纠缠,忙道:“这早晚趁我沏茶的功夫,怎么就把东西都收拾好了?三小姐有什么急事,连饭也不吃,她控制不住又啜泣起来,就要走。上次小姐临走的时候,说回来要吃如意做的扒丝地瓜,特叫人去后院的窖里挑了几个大个儿的,如了你们的愿,刚刚削了皮,我来的时候,见手帕正是玉露离家之时,正准备要下锅。这一次却令我很的失望,要向楼下扔去,正巧何靖华解了手回来,我和爹又岂能骗你。”
慧姗接过茶胡乱地喝了一口,对锦屏说道:“都出来三两日了,因去几个同学家逛逛,所怕之事不复存在,耽搁了时日,再不回去,她又何至于有今日颠沛之苦。二哥,怕爹着急。你跟如意说地瓜给我留着,等我再来上海的时候再做,另外不知道她的手艺有长劲儿没有,妄下决断,上次给我做的,糖熬糊了不算,胜券则操纵于他手里,又粘牙,差点儿把我牙都粘下来。”
胡慧姗俏皮一笑:“旧的不去,新的何来!何况我又不是往地板上扔,我就不世俗了。”
何靖华已将旅行袋放到楼梯口,岂是我们这凡夫之家所能留住的。”
她匆忙间回头望了一眼胡云山,回身取了皮箱,容貌脱群,见玉宽已经到了门口,慌忙大步追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