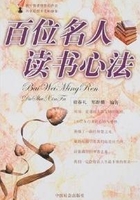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夜的黑暗渐渐淡化了,天空有了熹微的晨光。灰黑色的雪变成了灰色,浅灰,灰白,淡白,雪白,当感到雪色刺眼时,天色已大亮了。透过汽车挡风玻璃,我看见在深邃的天空上,盘旋着几只鹰隼。它们时而盘旋、时而滑翔、时而一动不动地定在空中。仁丹才旺也仰望着雄鹰,又双手合十地虔诚起来。我也学他的样子,双手合十对着空中的雄鹰顶礼膜拜,问:“才旺,听说你们藏民同胞把鹰视作神鹰,非常崇敬。”
“我们藏人十分崇敬神鹰,我们藏人死后天葬,就是让神鹰食去我们,使我们的灵魂升天。”
雷指导员看了下手表,说:“一班长,他们俩出去快三个小时了,也该回来了。”
“估计到道班了,冬天推土机不好发动,没有一个小时别想开出来。要是不出意外,再过一个小时推土机会开到这里。”
雷指导员长叹口气,钻出驾驶室,察看整个车队的情况。我也钻出驾驶室,仁丹才旺也钻出驾驶室。
时间从黎明转到了早晨。风小了许多,雪也小了许多,气温似乎比夜晚更要寒冷。我伸了一个懒腰,又嘘了口气,感到清爽了一些,但仍然头昏耳鸣,浑身疲软无力。冰雪的反光刺得我眯起眼睛向公路的两头眺望,全连五十多台车分散在二三公里的路段上。早在几个小时前,全连的车辆都停止了毫无意义的挣扎,挖雪的司机助手都缩回驾驶室里保存体力。我看到相邻几十米的车上也下来几个人,我向他们招了下手,他们也向我招了下手,就再也没有动作了,我们的体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雷指导员又操起铁锹,开始挖汽车前的雪。
仁丹才旺走到雷指导员跟前,从怀里掏出一个很精致的小壶,说:“指导员,吸口鼻烟,提提精神。”
“我不会吸鼻烟,谢谢。”
仁丹才旺把鼻烟壶里的黄色粉末朝左手大拇指指甲盖上倒了一丁点,送到鼻孔跟前,用力一吸,那些黄色粉末全吸进鼻孔。连打几个喷嚏,呛出许多眼泪和鼻涕,用袖子擦了一下,我觉得他精神了许多。
“杜班长,你也试一试?”他又把鼻烟壶递给我。
“我从来没有吸过鼻烟。”我有点想试试,又不好意思接鼻烟壶。
“不要客气,鼻烟提精神,还治感冒。”他抓过我的左手,朝大拇指指甲盖上倒了一点。我就学着他的样子把大拇指指甲上的鼻烟送到鼻孔跟前,用力一吸。我的妈呀,吸进我鼻孔、肺叶的全是辣椒面子、火碱面子,火辣辣地难受。我立即蹲在地上,鼻涕眼泪涌了出来,还连连咳嗽。过了四五分钟,鼻孔、肺叶、眼睛才恢复正常,我擦了眼泪站起来,仁丹才旺盯着我的眼睛问:“怎么样,眼睛都呛红啦。”
“受不了,真受不了,你们抽这玩意有啥意思?”
“要的就是这个刺激,你现在觉得鼻子通了吧?”
我试着吸了一口气,鼻子果然通了。这几天我有些轻微感冒,鼻孔里老是囊囊的不通气。
“你现在觉得身上轻快了许多?”
我扭动了几下腰肢,又活动了手脚,果然觉得轻松了许多。
“杜班长,这就是鼻烟的好处,头痛发烧小感冒,吸口鼻烟能治好,再吸一口。”
“才旺,你饶了我吧,那玩意哪是人吸的东西,比毒药还厉害。我吃了这次亏,再不会上你的当啦。”
仁丹才旺笑眯眯地把鼻烟壶盖好,又揣进怀里。
我和仁丹才旺吸鼻烟逗嘴的工夫,雷指导员又挖起雪来。
“指导员,等一会儿推土机就来啦。”
“万一推土机不来怎么办?挖一点是一点,前进一步就离胜利接近一步。”他只挖了两三分钟,就挖不动了。
“指导员,我来。”我伸手去接铁锹。
“一班长,你要保存好体力,就是一会儿推土机来了,车辆还需要驾驶。现在,我最担心的是驾驶员累倒。驾驶员倒下了汽车就瘫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保护驾驶员的体力……”
雷指导员还是停止了挖雪,走到了仁丹才旺跟前,问:“才旺,你女儿多大岁数啦?”
“八岁。”
“你出来和我们一块儿执行任务,谁替你照看女儿?”
“我阿妈的妹妹。我阿妈去世早,我都是她老人家带大的……”
“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朵玛。”
“上学了没有?”
“没有,我们藏区方圆几百里没有学校,要上学就得去县城,也没有那么多钱……”
“哦……”雷指导员望着仁丹才旺,思考了一会儿,说:“才旺,你现在就通知你女儿朵玛,让人把她送到县城或者玉树州读书。花费你不要考虑,我们连有一百多个人,也就是说小朵玛有一百多个叔叔,这一百多个叔叔资助她上学。只要她有本事,考上中学我们供到中学,考上大学我们供到大学。就是我不在这个连队当指导员了,下一任指导员也会接着供给。这一茬子兵复员了,还有下一茬子兵。你放心,兵是流水的,营盘是铁打的,只要我们汽车九团二营四连的番号在,就断不了朵玛的学费伙食费。”
“指导员,这怎么能拖累你们全连,又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要好多年哩。”
“才旺,我们这辈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们现在拼死拼活地奋斗,还不是为了朵玛这一代活得比我们幸福。她正是读书的年龄,现在不读书,这一辈子就完啦。”
“雷指导员,你们真是我的大恩人,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仁丹才旺要是不报,就死在这把祖传的刀下!”仁丹才旺嗖地抽出腰刀,在手臂上一划,流出一股殷红的血,有几滴滴在雪地上,雪上有了几点艳红的梅花。
忽然,我似乎听到一点异样的声音,急忙揭开皮帽子的掩耳,支棱起耳朵仔细听了一阵,果然有一种非常细微的轰鸣声。“指导员,你听,有声音。”
雷指导员也揭开帽耳朵,听了一阵也惊喜地说:“是推土机的声音!”
二十多分钟后,我们看见一堆红色的钢铁物件翻过一道山梁,向我们这边蠕动过来。
“推土机来啦,推土机来啦!”刚才还龟缩在驾驶室的战士们全出来了,高兴地呼喊起来。距离太远,互相只能看见动作,不能听见声音。
推土机开到我们汽车跟前,李石柱从推土机上跳下来,挣扎到离雷指导员二三米远的地方,立定,敬礼,双手捧着手枪递给指导员。
“王勇刚呢?”雷指导员问。
“他在道班等我们呢,他累坏了。”
我脑子里立即浮现出道班房里的牛粪火、奶茶、手抓羊肉、铺着狗皮褥子的火炕。
“你为什么不在道班休息?”雷指导员帮着李石柱拍去帽子上的冻雪。
“全连都在这里,我怎么好意思在道班睡觉!”
雷指导员爬上推土机,对开推土机的道班工人说:“咱们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把车与车之间的积雪推开,使整个车队连在一起。第二步是你在前面开路,车队跟在你后边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