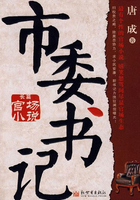听到这里,金戈甩开马鸣,调头就往回走。
马鸣一看急了,生气地对金戈的背影叫道:“都是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家伙!”
丁家村里,戴金花一个人蹲在凳子上抽着旱烟,满屋子都是烟雾缭绕。桌上放着金戈留下来的望远镜,戴金花越看心里越来气。此时猴子在外面喊道:“队长,大海回来了。”
戴金花赶紧放下烟锅子看了看窗外,接着问道:“一人还是俩人?”
猴子道:“就他一个。”
戴金花失落地道:“回来就回来呗,这点小事也要到我这来报告呀。”
猴子打趣道:“知道了,吃饭是大事,你出来吃吧,炸酱面。”
戴金花火道:“你再啰唆我把你当酱炸了。”窗外顿时无声无息,戴金花忍不住有些难过,低着声骂道:“金刀子你真不是东西,不仗义!姑奶奶为了你可以不当官,你却连多待一会儿都不肯,你哪怕做个假样子,说声舍不得大家你就会死呀!”说着难过地捂着脸低下了头。突然耳边传来声音道:“现在说,不知道还行不?”
戴金花缓缓松开了捂着脸的手,猛地抬头,发现金戈正站在眼前,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指着金戈磕磕巴巴地说道:“你你你……”
金戈笑道:“不是鬼。”戴金花看了看四周,没有发现马鸣,金戈继续道:“他没来。”
戴金花哼了一声道:“他就是来了,我也不愿听那句话了。”
金戈接着笑道:“可是你说了,不说这句话会死的。”
戴金花气道:“你回来干什么呀?气我呀?”
金戈指着桌上的望远镜道:“我不是还没教你怎么用望远镜测距离吗?”
戴金花一把抄起望远镜就要摔,金戈慌忙抓住戴金花的胳膊,吃惊地道:“哎呀,你想干什么呀?”
戴金花挣扎着道:“我摔了它,怎么着!”
金戈松开手道:“噢,那就摔,解气嘛!”
戴金花犹豫了一下,举着的胳膊不知是该放下还是继续举着,然后做势道:“我真摔了。”
金戈耸了耸眉说道:“这个德国进口的卡尔莱司望远镜,价格大概能顶半头牛,摔起来痛快。”
戴金花一愣道:“啊,这么贵呀?”
金戈赶忙打蛇随棍上地讨好道:“不怕贵,只要你开心就行。”
戴金花先是有些心痛,慢慢地发现有些不对劲,瞪着眼看着金戈,金戈再也憋不住,噗嗤一下笑出声来,戴金花这才明白金戈是在逗自己,不由生气地大声道:“你到别处死去,反正我交给马部长的是活的。”
金戈嘴角一撇道:“我还不想死呢。”
戴金花又道:“那就赶紧去根据地,那里多好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你这小脸能越养越白。”说着躲开金戈,走到炕上盘腿坐下,又叼起烟来。
金戈摇了摇头道:“可是跟他在一起活着不痛快,不利落,所以我又回来了。”
戴金花惊讶地一抬头道:“马部长能同意?”
金戈笑道:“我给你们上级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
戴金花打量着金戈半晌,有些得意地道:“可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哦。”
金戈上前一把将烟锅子夺下道:“马回不回头不在乎它是不是好马,而在乎草是不是好草,甘之如饴。”
戴金花一愣道:“又跟这儿拽,臭毛病。你、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金戈笑道:“就是指这个草吃起来甜得跟糖一样。”
戴金花呵斥道:“扯淡!”
金戈惊诧道:“这怎么是扯淡呢?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呀。”
戴金花道:“你吃过草吗?”金戈摇了摇头,戴金花又道:“没吃过你怎么知道草是甜的?我告诉你,我吃过,吃过野菜,苦得很,涩得很!”
金戈尴尬道:“是吗,也许马吃了觉得甜呢。”
戴金花轻呸了一声,道:“更扯,你又不是马你怎么知道!”戴金花一通瞎掰把读了一肚子书的金戈给说得哑口无言。
戴金花望着无言以对的金戈不禁叹道:“看来这以后只能我费费力气,好好给你补补课了,嗨,我这受累的命呀。”
是夜,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停在医院的大门前,钱柏豪正跟医生办理出院手续。
医生衷心地感叹道:“真是奇迹呀,这么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都恢复得这么快。”
想到柳文婷,钱柏豪的脸上也带上了微笑,“主要是您的功劳,感谢您!”
医生却摇了摇头,“不,你在窗台上留下的那一百多束沁人心脾的小花才是最好的药。不过,这种病不是很稳定,需要这种进口的特效药来长期治疗,只是我们这里没有。你要自己想想办法了!”说着把一张字条递给钱柏豪。
接过字条看了看,钱柏豪抬头道:“在哪里可以买到这种药?”
医生摇摇头道:“这可都是管制药品,没有关系弄不到的。”钱柏豪的眉头轻轻地皱了起来,不过在看了看车上双目呆滞的柳文婷后,他的目光变得坚定了起来,转身对医生道了声谢后,便上车离去。
大雨瓢泼,在这样的夜,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连平时一些热闹的茶馆、戏楼也因为生意不好显得有些死气沉沉。但在茂发洋行总号门前,一个人正打着伞站在雨中焦急地眺望着远处寂静的街道,连衣服被大雨淋了个半湿也浑然不在意。这雨中的人,正是刚接柳文婷出院的钱柏豪。
一道灯光划过钱柏豪的脸,钱柏豪顿时脸上洋溢着喜悦,赶紧冲下台阶迎了上去。一辆黑色小汽车停在总号门前,钱柏豪上前开门,身穿笔挺西装的蔡立峰走下车来,钱柏豪忙举过伞赔笑道:“兄弟辛苦了。”
蔡立峰看着殷勤的钱柏豪,无奈地摇摇头道:“你要的东西可是上面严格控制的特殊药品,不好弄呀。”
钱柏豪咬了咬牙,从怀里拿出一块玉佩递了过去,想了想缓声道:“我就只有这样的东西值钱了。”
看了看玉佩,蔡立峰摇头道:“这还不够。”
一听蔡立峰这样说,钱柏豪不由得急道:“那您说怎么办,要不我把这条命押给你。”
蔡立峰马上不悦道:“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说到这里,蔡立峰对着心急的钱柏豪说道:“大老板说了,如果你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一切好商量。”说完上前附着钱柏豪的耳朵小声交代了一番。
钱柏豪听完后不由得面露难色地道:“这是不是有些强人所难呀?您知道,文婷的病还没有好呀,我得陪着她。”
见钱柏豪是这种反应,蔡立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大盒全是英文的药物在钱柏豪面前晃了晃道:“那你看着办吧。”
看到这药,钱柏豪低头想了想,抬头道:“一个月之后再说行吗?”
蔡立峰看了看手中的药,笑着塞到了钱柏豪的手中,“一个月!”
一个月后,身着国军训练服的钱柏豪持着一把步枪站在训练场上,步枪枪管上放着一颗子弹壳,一支插在子弹壳里的野花随风微微抖着。只见钱柏豪把枪口往上一撂,子弹壳带着小花腾空而起,钱柏豪瞬间连开三枪,枪枪命中远处的靶心。
一收枪,伸手接住掉下来的弹壳和小花,远处一群穿着统一服装的训练生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但钱柏豪并不在意,回身对面前的学员道:“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已经没有身份、没有出身、没有名字,只有代号的工具,将进行魔鬼般的训练!你们只有把自己变成魔鬼,才能把鬼子一口吃掉,否则,你们就将变成无名烈士!今天的训练科目是,忍!现在,开始训练!”
学员在各级的教官咆哮的口令下,开始忍着痛相互击打对方的腹部。钱柏豪将视线落在女生训练的队伍中,眉头不时皱了两下,眼中偶尔闪过一丝什么,但他还是飞快地恢复了平静。蔡立峰站在钱柏豪身后,看着远处的训练道,“我看好六号。”
钱柏豪忙回身立正道:“处座。”
蔡立峰接着缓缓地道:“东安城我们迟早是要回去的,将这把刀好好磨利,到时候一定会有大用场。”顿了顿,他看着钱柏豪又道:“有些心痛了?”
钱柏豪正色道:“没有,国土沦陷才是我们最大的心痛!”
蔡立峰满意地看了看钱柏豪,从西装里拿出一张纸递过去道:“这是金戈的阵亡通知书和抚恤金,东安城寄不进去,你先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