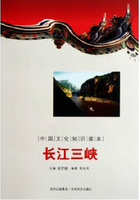拍完《战旗》,还没有掸掉来自外景地王佐的土,就听说要出书了。
制片人嘱我写个小序,再三强调文笔要朴实,说明我以往有掉书袋的毛病,我答应了,一定努力写点接地气的话。
说到这个戏,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接这样一个剧本,我答:好看!
记得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正在当“主席”(在四川国际电视节做评委会执行主席),每天被看片搞得精疲力竭,碍于制片人的情面就翻了一下剧本,就这样我自此陷入了一年的“万劫不复”之中。
剧本强烈地吸引了我,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靠自己的想象写出了一个如此好看的抗战戏,让我这个大学专业学编剧的自叹弗如,情何以堪。
它塑造了两个极其生动的人物形象,两个完全是平行线的人物居然在编剧的笔下发生了交汇,编剧娴熟地运用了倒挂金钩的创作手法,让那些看来必然成为绝境的情景居然发生了逆转(好像我的叙述风格又犯老毛病了)。
好吧,他们在大大小小三十多场战斗中成长,但每一次的战斗都非常具体有趣,都推动了人物性格的发展,这在战争戏中往往是容易被忽视的,当然,这些战斗也把我们给“拍残”了,这是后话。
总之,这是一个有趣并好看的剧本,值得一读,为了不破坏大家的阅读快感,我就不“剧透”了,看完了书再看看片子就更完美了,就像喝完了美酒可以来点主食。
说到这儿想起没说缺点,其实缺点很明显,就是全剧没有一场好看的喝酒的戏,其实编剧酒量不错,而我在酒场的名气远大于片场,这太不应该了,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们决定再合作一部戏。
飞机下降了,就写到这吧,再辩解一句,没拍出一场喝酒的好戏是有客观原因的,就是从开机到停机我没喝过一滴酒。
导演 毛卫宁
2012.9.25于赴北京飞机上草就
竹签上的山里红。
文字的万千风情,来自于千万种表达。同一个故事,剧本和小说有着不同的讲述。小说,擅长描绘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意境,而剧本更多的是表述行为和视觉,阅读小说、剧本与观看影视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感触。电视剧《战旗》的剧本改编成小说,那种阅读的间隙感同样强烈。好在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那些生动有趣、独特传奇的主角一样能打动人心,好在《战旗》还有金戈、戴金花这样两个青春肆意的人,无论生命还是爱情都格外张扬,格外感染人。读者一旦走近金戈、戴金花,走进《战旗》中人物的世界,富有动感的人物将会弥补阅读转换带来的间隙感,进而喜欢上他们。
在强情节当道的当下电视剧市场,似乎人人都在说情节,都在要求密节奏,似乎只有把高密度的强故事情节变成一根竹签,穿上山里红那就是冰糖葫芦,穿上羊肉、鸡肉就是烤串,穿上各色人物,才能出现一部好剧,才能跟世界潮流类型剧接轨。起先我也是在这样的标准下玩命写了很多剧本,尽管都有播出,大部分收视率还过得去甚至不错,但是始终有些游离“佳作”的标准,直到《战旗》一稿完成,播出平台确认之后。在评估剧本中的一个偶然时刻,我顿悟到这一看似简单,却又很难捅破的窗户纸——人物,这也就有了《战旗》中非常着力刻画的两个人——金戈和戴金花,而把我一贯擅长的情节设计放到了次要位置,最终对人物价值架构的确定,改变了竹签和山里红之间的关系。
把冰糖葫芦的竹签由故事换成人物,山里红由人物换成故事,说着容易改变起来其实挺难的。前七集全部推倒重来,除了脑子里不断闪现问号之外,金戈和戴金花也在彼此忽远忽近地摇晃着,这种痛苦的感觉无疑掏肝掏肺地难受。我常常一个人躺在沙发上,一躺一天,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金戈和戴金花总是在一旁傻乎乎地看着我,只不过他们身上有镣铐,嘴上贴着封条,我看他们挺可怜,他们看我更可怜。在可怜的状态下创作,作品腰身不壮,角色胆气不足,幸好这个时候毛卫宁导演加入了,导演是一个气场十足,眸子锃亮,手舞足蹈,说话时不许别人开小差的家伙。在他们影响下,金戈和戴金花这俩扭在一起生长出来的新品种竹签,既有楠竹的坚韧,又有斑竹的情愫,而原来早已烂熟于心的各种各样传奇好玩的故事点就化身为裹着冰糖的山里红。
文字活了,导演居功至伟。从穿着羽绒大衣开始,到裤衩背心结束,导演带着王雷、王媛可等一帮弟兄把金戈、戴金花变成有血有肉的影视艺术形象,你可以触摸到他们丝丝的呼吸,感触他们怦怦的心跳。如果说《战旗》的剧本让我有些小得意,那么这部电视剧,这个风格独特的影视作品,则让我骄傲。
这串糖葫芦,于我,于读者,于观众,能品尝出“荒腔走板的爱情,一本正经的抗战”,将是我最大的收获。
王成刚于长沙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