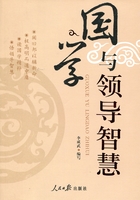李成才:“那也不怨你爸,我们这地就是那个习惯,风俗也是这个样,谁都拿它没对策。但是,到了某一天,要真是为了那事而不活了的话啊。可能你爹会有点醒悟,可能会悔恨自个不该开始如此待你。就惋惜到那天就太不赶趟了,太迟了,由于世上压根是没有卖悔恨药的地方。”
尚丽丽:“他能悔恨吗?不相信!非但不后悔,并且还会说你要是跟了他就应该稳稳生活,不能寻死不活,不让家里安心的。”丽丽极不同意地反说着。
李成才叹说:“可能他在说你的一并,不能想到弄死你的杀手其实是他自个。”
尚丽丽似乎听明白了他说话,然后不吱声了。李成才也像说完一样也不吱声了。他们两都在思考。过了很久,李成才俯身一瞧怀中的尚丽丽,人早已经睡着了。他赶紧脱下自个的上衣披在尚丽丽身上,并尽力坐直早就酸痛不已的腰,慢慢地把她抱住,使她在自个的怀里尽量睡的得劲一些,惬意一些。
星空中的明月已经向西了,并且比原先看似更远,更好看,更圆,就是比才暗时小了很多。跑了整天,累得很困的李成才也睡意若隐若现有些支撑不了了。上面下面眼皮直打架,像是羡慕他们无比亲热的模样,有些妒嫉老想相依在一块。
李成才一直不敢打瞌睡,虽然困得要命。上面下面眼皮刚碰着,一点风吹的动静,他赶紧睁开眼睛,瞧了下周边,什么都没有,全部依旧。李成才就很有趣地讲:“俺们俩人也不能无拘无束地一直依偎着,怎能使你们俩这样嚣张。”讲完就尽力睁大眼睛,不在眯着闭眼睛了。
有阵凉风吹来,吹起了披在尚丽丽身上李成才的外衣,李成才打了个寒战,用已经冰凉的双手胆胆怯怯地帮尚丽丽披好上服,但没成想他本来已经轻轻地行动还是弄醒了睡觉着的尚丽丽。
尚丽丽睁开睡眼朦胧的眸子,从李成才的怀中起来了。害羞地道:“赶快回,俺困死了都。”然后就打个呵欠,动着腰身,擦着双眼,真像马上就可以睡着的模样。
李成才边直起已经痛的身子,边很神气、很调气地道:“俺还行思你要在俺怀中睡一晚呢?”
尚丽丽只晓得自个睡得舒服,哪懂得李成才的不得劲难言之苦呢,丽丽给李成才披好衣服,羞羞答答地柔声说:“滚你的,属你坏心。”语中充斥着信任与爱意和情味。
接着两个人又相互依偎,互相挽扶,互相牵着拉着沿着来路向回走,一直说不没的言语又飘荡在他俩耳边,钻入他们的心田。
尚丽丽满含幸福地道:“实话告知你,成才,俺长到现在,除在爸妈兄妹,亲戚长辈怀中呆过,没别的,真是真心实意只呆在你这个人怀中睡过觉。”
李成才极为骄傲地说着:“讲真实的,丽丽,俺活了这些多年,不算侄娃,妹妹,孙子什么的小一辈人小娃在俺怀中呆过,别的,也就有你这个人敢钻进俺的怀中,一并也是俺真心实意唯一许可了的那个。”
尚丽丽:“俺初恋的爱护与甜蜜都从你身里感受到了。”
李成才:“俺初吻的快乐和柔情也都在你这儿品味出来了,”说完李成才用手指着尚丽丽的嘴,惹得尚丽丽直乐,并且笑个没完,之后又道:
“不管怎样,今夜你对俺来说是俺一生中唯一一次,真的。”
“反正,今晚你和俺就俺而说也是俺这世的第一回,确实。”李成才调皮地像对对联那样回答着尚丽丽的每一语,逗得尚丽丽笑个没完。尚丽丽只感觉他那个人真好。
又到了分开的道口,他们俩好像还都有很多的话想说,可又不知该讲些啥?该从哪说起?互视一下,狠狠地搂抱在一块,一个特别甜蜜,特别爱护,多少的人做梦想求得,多少的人痴心向往,但他们却能随意的一吻化解了双方心里的千言千语,过了很长很长的几分钟过后,差不多有六分钟,两个人才约好明晚饭后见,不谋而合地松开了另一方,放了手,差不多在同一时同一声道了声:“俺们的约定是从月亮圆开始啊。”说完两个人对视笑了,不谋而合地仰头瞧了一下东南方星空那徐徐下落的明月,又相互看了一下然后分开了。
李成才一直瞧着尚丽丽过道口,到了门边,走进了家里,接着过了十几分钟的样子,窗户上的灯熄了灭了,才往自己家中走去。
刚入冬的早上,虽没有下雪,但还有霜,并且特别冷。
在尚品庄村后面的那片农作物地里的坟墓地里面,不大的、不小的;很新的、很旧的;没草的、长草的;长树的、无树的;方的、长的坟墓堆,横七竖八、一点规则地放在这儿。
坟墓地四周的农作物里银白色一片,这不是雪到是冰霜。坟墓地的枝叶上,杂草杆上都有一层厚霜,并且凝结成厚冰,像是有了一层水镀。坟墓堆上面的树枝子在晨风里哗哗作响。这竹杆上挂着的火钱串儿链儿也在早风中啦啦地叫,像是在抽泣,在倾诉。冰冷的、微微刺骨的早风吹得墓地的杂草也嗷嗷地哭着。
有时,令人憎恶、反胃、反感的老鹰在坟墓堆旁的枝叉上发着几声不好听的惨叫,使人毛发竖立,一直打寒颤。那样的情况,就算死人都不敢从土地里出来瞧着,活的人也仅有看看罢了。(意外情况不算。)
伙计,当你把身子放这悲惨荒凉的境遇中,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能不担心吗?
但是,在这条衔接着村子和荒坡,经过坟墓地的林间小道边,在那座不算大的、几乎没有树的,也五草的,甚至一个纸条子和纸串子也没有的刚建的墓坟旁边。这时候,却盘曲着个不明物。在老远一瞧就像个只灰狼,但走近仔细一看却是个真是的活着的人。
他只是斜倚在坟墓堆旁的,腿特别不随意地卷曲在身子下。分明是跪累了斜趴下去就已经睡着觉了。
他的上身着的破棉衣已经破开了,很黑很脏,并且没了纽扣,是虚系着的。腋窝里,上衣的布料撕了个很大的口子,一直扯到棉衣大襟边。暴露出了里面疙瘩疙瘩的旧烂棉花,没有牵连的上衣布料没有精神地送拉着。厚厚的冰霜已在这脏棉袄外面子上冻起了一层冰霜。一动身,袄里面还吱吱咯咯地动呢!
这人睡着呢,掩袄大襟的手放开了。开始掩得特别严实的上衣如今就像车门似的没有拘束地敞开着,凉风一股劲地向怀里灌。棉袄里穿着一件黑不啦叽的破毛衣,粘满了灰色泥土并且没有领。衣服下面一没有衬衫二没有内衣。
他既瘦既脏的脸都黑到了脖子根里,好像几年几十年都没洗了。残次不齐的黄发中加杂几绺白发,但已被厚霜冻结了,像是抹了发胶弄了形一样。一整个头好像个孵蛋的老母鸡窝一样。额上的皱褶,使他看似苍老了很多。
他穿着破裤子,裤裆也开了,臀部后面还有两个窟窿。裤缝隙从大腿跟一直开到脚下面,像个长裙,裤子比上面的棉袄都要脏,都要烂。可能是时常习地而跪,而坐,经常摩擦的原因。裤腿与上面的棉袄似的都有一层厚霜覆盖着。
他脚踩着一双破棉鞋,赤着脚,也没穿棉袜。从这拉到腿肚上的裤子腿上,一眼就瞧到那瘦得像个栓的下肢和冻得发青的腿腕处。棉鞋破烂糟糟的前面坏了,那几个紫红色的足指头暴露在外面。
他那另外一只腿卷曲在身下面,瞧不清是啥模样的。肯定也与能瞧到的、之前的那只腿的情形一样吧。
他这粘满泥土的手全是血花,红色的血口处在他手面上随着肤纹分布。暴露在外面的手没有力气地耸拉在身旁,伴随呼气而起起伏伏。压在身下的手弯曲着,往上微抬着,平停在坟墓堆上的斜坡边上,用头枕着。
一张有色照片放在坟墓旁边的杂草里,伴随着早风微微动着。
他那个样子猛一瞧特别像个老人,肯定是个乞讨的,特别是在这凄凉乱坟墓堆里。特别分明,他在那没有无人烟的坟墓地睡的觉,并且不只一晚,从他的睡觉姿势就能容易瞧出。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大概有神精病吧?那他那样做到底为了啥呢?
事实上,他是李成才,他本来,一直,先天就无神神病,他就是为了他本人。他原来不是村中人,他本住在那块对边的这个村里的。
中秋佳节过完,该栽的麦子都已逐渐栽完,该施的肥已经到了田地中,该干农活不用别人叫,也不需要谁管,大家早就你追我赶地依次干完了。能离开的人,家中有两位或者两位以上劳动的人,已经出去一位打工赚钱去了,立不开人的就留在家中喂喂畜牲,做些家里的活,有空收拾下柴禾。
刚入冬的早上,太阳都没升上来,懒懒的人们都在炕里热被窝中睡觉呢。而在那尚品庄村后的这一整平处农田里,在这条乡间小道上,朝着坟墓地走着好几位拿绳拿刀的庄稼男子。弯着腰,低下头,攥着手,移着小步伐,边道着话边行着路,瞧样子是想穿过坟墓地到山坡里去捡些柴禾。
好个人不谋而合地立在了这个蜷缩着一个不明物的刚建的坟前,瞧着这睡得特别香的外地汉,啥也不讲,也不问。当中一个年轻的男孩拾起这张飞落在杂草丛里的相片,细细地看着:
相片站着个女孩。她的脚穿着一双白色的旅游鞋;棕色的美身裤把丰润的双腿勒得特别紧;上面一件鹅黄色的衬衣,外面穿着一件有波纹形状的粉白色花毛衣;一张干干净净的小脸特别吸引人;有些稍黄的头发像一个黄黑颜色的水瀑飘荡在脑后和胸前;那双眸子没有看向镜头,反而是把两眼满含着秋波赠给了脚底下道的远处;有只手使力地放在腰上,还有一只手特别随意地垂放着;一对眼睛,两个脚很随便地站成“休息”的状态。这个人说是动却静,说是静却好像在动。在她那着急的眼中一瞧就晓得,她正在等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