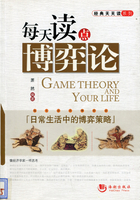沈略小跑着到他面前,正纳闷的时候,被他毫无预警地抓住手臂,然后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的雪白胳臂上多出了一串黑色的鬼画符,格外的刺眼。
唐颂把笔旋进笔套里,还给咨询台的小护士,只是抿抿唇就把人家迷了个七荤八素。
“我的电话,有事找我。”他回头对沈略说,语气是习惯性的霸道,仿佛写了,她就一定要找他。
沈略从胳膊上那十一个数字还有他龙飞凤舞的签名上回神,右手抹了几下没擦掉,咬牙道:“你既然可以借笔,为什么不能再借张纸?!”
还有那啥签名,有必要吗?他又不是王力宏!谁稀罕啊!
唐颂笑得恣意,对着垃圾桶做了个投篮的手势,危险地眯起眼问:“然后让你转身就这样?”他敢肯定,写在纸上的下场绝对是墨迹没干就投入了垃圾桶的怀抱。现在这样多好,她圆润光滑的胳膊上还署着他的大名,嗯,他的女人。
沈略瞪着圆眸,搓得手臂通红却无可奈何,这个该死的男人,居然专门借了油性笔。
唐颂好笑地拍拍她的脸颊,说道:“不用送了,回去吧,外面热。”说完,这次真的潇洒离开。
徒留沈略还在跟胳膊上的字迹奋战。几分钟后,她嗷的叫了一声决定放弃,如果不是怕父亲担心,真想跑到窗口买几个创可贴全给挡住。
沈略耷拉着脑袋往回走,还没有进父亲的病房,便听到章天秋的大嗓门。
“老沈啊,我可是亲眼看见沈略从他的车上下来,两人临别前还亲嘴,哎呀,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跟一个成年大男人。真是!出息啊,高中没毕业就知道傍大款了!你还真得管管,看看现在的新闻,什么陪酒啊坐台啊代孕啊,不知道这些女孩子怎么想的,真不害臊!”完全忘了她是怎么怂恿自己的女儿了!
沈略在外面听得火冒三丈,砰的推开房门,沉声道:“我爸爸需要休息!”
章天秋唾沫星子还没落地,看到沈略的表情,傻在那里了,然后悻悻地说:“我渴了,下去买两瓶水。”
嚼了半天舌根,当然渴。沈略鄙夷地将她“请”了出去,紧紧地关上房门,回头却被父亲的神色吓了一跳。
“爸……爸爸,你别听她胡说。”她有些忐忑,不敢去看父亲的双眼。
沈如海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道:“小略,是爸爸对不住你,总是连累你,现在父女俩你伤手掌我断腿的,还得照顾我。”
“爸爸,你别这么说——”沈略红着眼眶,赶忙插嘴。
沈如海却摆摆手打断了她的话,继续道:“小略,人往高处走,想出人头地没错,可我们要注意方式。爸爸不相信你像你章姨说的那样,但是,你最好跟那个男人断绝往来,他跟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不会给你想要的生活。”
沈略眼带湿意地猛点头,表示自己明白。很多人说她父亲懦弱,小白脸,不配当一个男人。可是,父亲在她心中却是顶天立地的。
她小时候,父亲也因为家里贫瘠的环境,因为难以忍受别人的指指点点而脾气暴躁过一段时间,有次甚至失手打了她。她委委屈屈地蒙住被子哭着哭着便睡着了,半夜醒来时,发现父亲在她的床边垂泪,边扇自己边向还是孩童的她道歉。
自那以后,他总是控制着自己,尽其所能想给她最好的,当初跟章天秋在一起,本意也是给她一个完整的家,不再漂泊。可是,后来的日子谁又能想到呢?
许多婚姻走到了最后只是将就,得过且过,这辈子也就这么算了,所谓爱情,往往是最奢侈的情感。
沈如海真的为她付出了许多,所以,沈略也学会了装,在他面前装她过得很好,将一次又一次的摩擦化小,委屈咽肚。
“吃软饭的沈如海”,这是别人对他的评价,可沈略知道,他最不想做的事情,便是依附,依附他人。
“爸爸,你放心,我不会跟他有什么的。”沈略吸吸鼻子,郑重地保证。出卖自己,藤蔓似的攀着男人,迟早会遭到对方的鄙弃。
沈如海这才扯了抹心酸的笑,闭上几十个小时未合的眼。
沈略小心翼翼地给他盖好床单,再调整好枕头,然后坐在一边出神。
她又看了眼胳膊上的数字,暗暗决定,等过几天工资发了,就连同上次在校医院时他给的钱,全部还给那个男人。实际上哪怕父亲不说,她也早打算这么做。
距离开学没几天了,父亲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沈略没心思继续工作,出去给经理打了个电话请辞,经理人不错,说先帮她把工资领了,她随时可以过去取。
等章天秋买水回来后,沈略又回家了一趟,沈如海腿部刚用夹板固定好,头颅CT显示还有轻微脑震荡,需要观察一阵子。陪护这种事情指望章天秋绝对不可能,还得靠她自己。
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她顺便买了排骨,仔细地调好汤底放入煲锅,然后才慌慌张张地开始收拾衣物,一切准备好到达医院时天已经黑了。
她满头大汗地跑到电梯口,赫然发现几部电梯都停在十几楼,许多人还等在那儿,想想父亲的病房也不高,决定爬楼梯上去。
让沈略意外的是,楼梯道里居然也拥挤不堪,拐角睡得都是人,有的枕着硬纸板叠成的枕头已经睡着了,有的随便用蛇皮袋占着位置站窗口抽烟,夏天的汗臭味、烟味……杂合在一起,兼伴着呼噜声,堪比春运时的火车站。
她低头深怕踩到各种睡姿的人们,上去后才知道那些都是照料病人的家属,外地过来的,庞大的医药费本就让家庭负重,自然舍不得在B城住上一晚好几百的酒店。
路过值班办公室时,骨科的主任医师居然亲自迎了出来,客气地说要给她另备一间休息室,沈略连连摆手,推迟许久,主任才勉为其难地说:“好吧,那我就给您在这屋加张床,有什么别的需要,您尽管吩咐。”
这番热情,沈略自然知道都是看谁的面子,无形中那份人情又重了几分。
怎么办才好呢?难道真得肉偿?
正想着呢,有人敲门,走过去拉开一看,霎时让她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