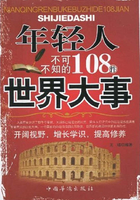到茅台来,又何止于品酒,还会就近拜谒仁怀、习水、遵义、土城和娄山关等一系列革命圣地。遥想当年,长征路上,转战迂回,四渡赤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凡此攸关历史转折的“而今迈步从头越”,就虎跃龙腾在这一片红色的土地上。
为丰富“文化酒”,我在会上建议茅台还应编辑一套所有涉及酒的诗文丛书。应涵盖诗经楚辞李白杜甫《三国》《西游》《水浒》《红楼》等凡写到酒的篇章,让读者能了解酒与人生何等相近相亲难解难分。酒是神圣的,最初只作为祭品;酒是密切的,生活中紧贴灵魂。酒是思绪的喷泉、情感的泪腺……
这次喝上了储存几十年的茅台酒,二十二年前的感受得以更新。茅台酒香,绵延不尽。我期盼着有朝一日重访茅台,便用现场诌的顺口溜抒发感慨:“一路风光烂漫开,廿载春秋我又来。日精月华凝佳酿,山魂水魄铸名牌。天有灵光照遵义,地存宝气聚仁怀。品味三杯天下醉,流芳百代是茅台。”
茅台镇夜饮
熊召政
我的心中有很多圣地,譬如丰镐、郢都、灵鹫山、延安、卢浮宫等等,与它们相关联的是国家、民族、故乡、宗教、理想与艺术。作为酒徒,如果有人问我:你的圣地在哪儿?我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他:茅台镇。
正因为如此,我才产生了往茅台镇朝圣一次的想法。近些年来,我不止一次得到邀请,但总因各种缘故而未能成行。二○○七年十月末,《人民文学》组织几位作家前往茅台镇采风,执事者邀我参加。其时我正带领一个摄制组在三峡工作。经仔细调整拍摄方案,这才挤出两天时间,由宜昌飞重庆,会合诸位文友,乘上茅台酒厂派来接机的中巴,于下午三时,驶上崇山峻岭中的黔渝高速。
暮秋的天气,在黔北山中,是绵延的雨与卷舒的雾,是让花无精打采、让人怔忡迷盹的轻寒。行车七个小时,才在万山尽墨的仲夜,来到灯火阑珊的茅台镇。
因为摄制组的时间安排,第二天我必须赶回。但这么远的路程是我始料所不及。原以为黄昏时到达,可以推杯把盏品尝茅台夜宴,第二天上午还可以参观酒厂,看来这愿望要落空了。与我同来的敬泽兄知道我的心情,便让此行的组织者朱零老弟敲开我的房门。行装甫卸,我们文友数人,在交了子时之后,一起上街寻找小酒馆了。
茅台酒虽然声名远播,但茅台镇毕竟嵌在川黔交界的乱山之中,离它最近的城市遵义,也有一百二十公里。因此它不可能像重庆、成都那样把夜晚交给灯的河流、光的瀑布。它仍然固守小镇的传统,几盏睡意惺忪的路灯,偶尔的步履悠闲的行人,三两爿虽开着门但生意清淡的商铺。置身其中,我立刻感到亲切而温馨,因为我的青少年便是在这样的江南山中小镇度过,我有了回到故乡的感觉。
唯一遗憾的是,所有开着的店铺都没有茅台酒出售。询其因,得知茅台酒厂的年产量供不应求。所以,当地人并不能因地利之便,而尽兴地品尝茅台。
“不能品尝茅台酒,我们可以品茅台镇嘛。”我如此说,并非完全自嘲。潮润的空气中飘荡着的酒糟的酱香味,已是让人惬意。此时,本地作家赵剑平说:“我建议你们喝一喝镇上小酒厂酿造的散酒。其品质虽然不及茅台,但仍不失为酱香的佳酿。”敬泽兄立即应允,并立即跟着剑平兄前往打酒。我和朱零则找了一处大排档,点了几样烧烤。一会儿,敬泽拎了一只装散酒的矿泉水瓶回来。一看瓶中微黄的液体——这茅台酱香型酒特有的颜色,心中立刻升起了酒兴。
在中国众多的白酒中,若给茅台定位,应允为酒中的贵族。
说它是贵族,不仅仅是它特殊的工艺、严格的酿造,更因为它酒中的品质。培养这贵族的,是茅台镇周围山中的高粱与小麦,是绕镇而流的赤水河。离开茅台镇,哪怕用同样的工艺、同样的原料,也无法酿造出茅台酒来。今天,所有的白酒,唯有茅台敢理直气壮地说:喝出健康来。
是夜,我们这几位文人,想到的倒不是喝出健康来,而是喝出情调来。店家送来五只一次性塑料水杯,敬泽兄全都斟满,明知道和他比酒量是以卵击石,但架不住这夜饮的诱惑,竟也暂时做起了比酒胆不比酒量的英雄。
这散酒味道委实不差,毕竟,它亦出自酒之圣地,古人曾言:“宁要大户的丫环,不娶贫家的小姐。”窃以为指的是教养。转比于酒,则茅台镇中的散酒,放之别处,亦可称为大家闺秀了。
烧烤的味道不敢恭维,故我们几个人吃得少、饮得多、说得多。由酒谈到文,由文谈到人,谈到文人中的超级酒徒,从杜康、陶渊明、李白等谈到眼下这位敬泽兄的酒量无敌,不觉夜深、不觉行人更稀、不觉灯光睡意更浓、不觉朱零老弟又跑去偷偷地打回一瓶……
凌晨一点,非常酣畅地回到宾馆,兴奋之余,诌了八句:
天下茅台酒,人间味道长。
含香怜赤水,入窖酿秋光。
招饮惊陶令,飞觞悔杜康。
谪仙若到此,一醉射天狼。
品茅台,知中国
张生
很难想象,像茅台这样的酒产自上海或江浙会带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当然,我知道,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很难让人想象。可如果你曾去过贵州,尤其是去过茅台,你就不会对我有这样的想法感到奇怪或惊讶,或许,你不仅会赞同我的想法,还会加上一句,这怎么可能?
是的,这怎么可能?
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我和一些朋友应《人民文学》之请,赴茅台参加由《人民文学》杂志和茅台酒厂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文化酒论坛。我与同行的郜元宝由上海出发,先乘两个多小时的飞机到重庆,在江北机场和其他人聚齐后,下午三点,按计划一起乘茅台酒厂派来的一辆中巴驱车前往茅台镇。
在离沪之前,我曾在地图上看了一下重庆到茅台之间的距离,虽然也感到不算近,但毕竟抽象很多。在地图上,崇山峻岭化作一片绿色的阴影,长长的公路细若游丝,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城镇稀稀落落地点缀其间,几乎让人无所适从。而之前的飞行又让人对距离失去了应有的体验,在空中,除了能偶尔透过云雾依稀看到山川的皱褶外,同样不会让人对机翼下的大地有什么具体的感受。所以,当汽车离开重庆这座迷人的山城,开始在渝黔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奔驰时,我才觉得此行刚刚开始。
实际上,这段漫长的旅程的确也是刚刚开始。尽管司机一路上驾车飞驰,路途的遥远以及所消耗的时间还是远远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这一行整整花了七个多小时,直到晚上十点,我们才闻到空气中飘着的那一股浓浓的酒香,在深沉的黑暗中抵达面向赤水依山而建的茅台镇。
可是,在剩下的夜晚,在梦中,我仿佛依然在继续着这段旅行,汽车在快速行驶时所发出的震颤声和呼啸声,连绵不绝的高山和大川,在我的脑海中都统统混杂在一起,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样汹涌澎湃,无边无际,还有那像藤蔓一般在山腹中蔓延的一节节隧道里的灿烂的灯火,也像一串珍珠一样在我眼前忽明忽暗地闪烁着,这一切,都让我觉得自己犹在途中。
我生平似乎第一次突然感受到了这个昔日曾为东方巨龙的帝国的国家的浩大,它的壮阔,磅礴,厚重与庄严。而帝国这个词对我来说,好像也头一次变得如此具体,形象而实在。我想,作为一个帝国,不仅仅因为它有奢华的外表,炫目的衣饰,更重要的,也是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它有深远的腹地,坚实的肌腱和粗大的血脉。
其实我并不是头一回闻知有这一片土地存在,我父亲年轻时作为一名铁道兵,曾参与建设过川黔之间的铁路,他过去也曾与我无数次地谈论绵延其间的这一片壮丽而森严的国土,但遗憾的是,以前我只把它当成是一个老人可有可无的回忆中的小小的摆设,而从未像今天一样深深地体味到它的那种存在的分量以及它的意义。
黑格尔曾言,事物在空间形式上的量的叠加和无限,如体积的巨大,面积的广博,常让人产生崇高之感。我猜,当初我父亲在这片山川之间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撼,就是这种崇高的意识,尽管天长地久之后,这种震撼业已在他心中化为温馨的记忆。但是今天,这相同的感觉却把对我来说模糊的记忆还原为那种崇高的意识。
而又有谁能想象,酿造了如此醇厚的美酒的茅台小镇,竟会潜隐在这万千深山和川谷之中。这或许正是帝国之所以为帝国的一个原因,因为,在我看来,作为帝国的一眼甘泉,茅台就应该深藏于这群峰与丘壑之间。
如果茅台酒产于上海或者江浙,我们从中能感觉到,最多不过是上海的现代、俊俏,或者是江南的明媚、婉约,但我们却感觉不到中国曾作为帝国的那种厚重和博大,而厚重和博大,这当然和酒的品质有关,但却又不完全相关。我相信,即使这产于江南的茅台让它拥有和茅台本地的产品一样的口感和实质,它也无法让我们领会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厚重与博大。因为那通往帝国腹地的漫长的旅程,所经过的博大的原野,厚重的山脉,同样必不可少。
这或许就是无论哪个国家,都把酿酒和饮酒当成一种文化,而反过来,又把自己的文化浓缩为酒的原因。
而茅台的醇厚、温润又绵长的风格,无疑让人时时想起我们中国,或者中国文化的特点。
实际上,文化从来就是具体的东西,它是有形的,可感的,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只是因为是日用,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这就像我们通过豪饮伏特加来认识俄罗斯,轻嗅葡萄酒来揣摩法兰西一样,我觉得,要真正了解中国,也一样要从品味茅台开始。
茅台归来
郜元宝
跟着一群文坛先生、同年以及后生去茅台跑了一圈,回到上海,转瞬二十多天了。印象如新,但拿来作文,材料仍嫌不足。毕竟只是跑了一圈而已,所以尽管玉成好事的《人民文学》再三催逼,仍旧白卷一张。
中间上了趟北京,本拟一晤在茅台结识的二三酒友,彼此交流“酒后感”,抛砖引玉,或能醉中偷得佳句。不料碰到教育部大肆进行“教学评估”,只好赶紧回来。这次东西南北教书匠们皆栗栗自危,生怕被“抽查”,仿佛真有什么过错,又仿佛教了十几年书,一旦“评估”起来,就都不会教了。这种心态,用“杯弓蛇影”、“瓜田李下”之类的成语恐怕尚不足以解释其中奥妙。
这才后悔在贵州时,拿腔作调,没大灌特灌。否则,纵无李后主“酒恶时拈花蕊嗅”的风雅,俪生所谓“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的豪壮总能沾点边,区区“评估”,其奈我何?
其实不然。尽管拿腔作调,还是喝了不少。若单论茅台,有生以来加起来也没那几天喝得多。何况绝对正宗,又何况在茅台而饮茅台?但不济就是不济。
使阿Q饮酒,无论绍兴花雕还是贵州茅台,见了赵太爷,也都白搭。“酒能壮胆”?一句需要大打折扣的中国式的“豪语”罢了。
据说复旦某狂生有次喝酒,醉到人事不省的地步,接二连三摸出人民币,叫大家听那撕锦裂帛的好音。及至摸出一张百元大钞,却突然缩手,改打醉拳了。酒后丑态多多,这一例可进《无双谱》了。至于刚在茅台潇洒,很快就遇“评估”而狼狈,还不够格罢。
到茅台的第一次晚宴,董事长、自称喝了两吨半茅台而身强体壮、鹤发童颜的季克良先生正欲致辞,刚从上海交大转会到同济大学的小说家张生就冲上去向他敬酒,激动地说:“季总,我来茅台,最大的收获就是见了您。您是我的崇拜者!”
这种颠倒主语宾语的“酒话”,其实大家并不在意,但被遵义作协赵主席及时纠正后,还是让张生大感受挫,为之不欢者累日。隔天,季总又出现了,大家一致建议再给张生一次拨乱反正的机会,上去敬酒,把颠倒的再颠倒过来。张生也很珍惜这机会,但显然太珍惜了,又紧张起来:“季总,我前天激动过度,本来想说‘您是我的崇拜者’,结果说成‘我是您的崇拜者’了”。
张生是我既爱又厌的朋友兼邻居。爱他滑稽多智,言辞便给,往往能口吐狂言,打破平庸时代的寂寞;厌他老是自以为滑稽多智,言辞便给,所以并非经常能够口吐狂言。而且因为他在口才上确有异禀,一旦唠叨起废话来,就尤其令人不堪忍受,愈感平庸的寂寞的可怕。从重庆到茅台,一路上我们照例没少打口水战。不料到了茅台,我们这一行还是以他为代表,接连两次在言语上闹了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