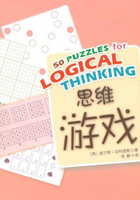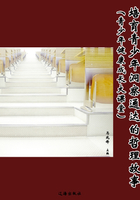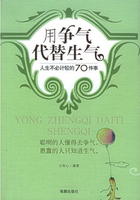“咔嚓”一声脆响,半边手臂火辣辣地痛了起来。
我痛得咝咝抽着冷气,颤微微地睁了眼,一丝一缕的光线缓缓漏入眼底,恍惚间流光飞舞,耀眼地紧,渐渐地,一张文秀的面容映入眼帘,清晰了——
原是个年轻男子。
他薄唇轻抿,眼角含着分清浅笑意,分不出是欢喜,还是嘲讽。
一盏青花陶瓷的茶被送到我面前,我一愣,分不出他这动作到底是故意还是无意,忍不住张口嚅嗫道,“您眼神不好吗,原应看见我手脚不麻利,接不稳。”
他眼波一闪,收回茶盏,笑,“只是小伤,不碍事。你醒来倒也省事,免得燕知天天挂念,反复念叨,就怕你和我置气,倒是生了什么闪失。如今看来,你还是老模样,断是吃不得半点苦头。”
真是窦娥都没我冤枉!
这床冰得人打斗,谁乐意在上面睡,谁去睡,总之,我不愿躺着!
另外,燕知是谁,听他口气,这个燕知和我挺熟,而且很护我。醒来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心头涌上说不出的恐慌,忽然听到这么句话,直觉有抓住救命稻草的感觉,默默把这个名字搁在心头。
努力再想了想,发现一切依旧陌生得紧。
他五官生得虽然清秀,却也寻常,可笑起来却仿佛清光潋滟,俊秀不可方物,我一闪神,忍不住张口蹦出个十分困扰的问题。
“我们很熟吗?”
他又是一笑,伸手扶了我一把,刚才骨折的地方,仿佛在极寒极阴的地方,忽然被人用热水熨帖过,说不出的舒服,恍惚的空儿,竟也不痛了。
这是甚的医术?
好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