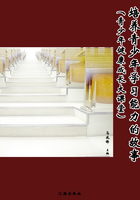布帘之内,护士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婶,估计是察看了伤情,嗓门虽然很大却是怜惜的语气。
“我说丫头,你怎么弄得这屁股红得这么厉害呢?唉哟,你说这细皮嫩肉的,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呢?痛死了吧?”
这种话,无疑是在控诉着宁希唯的暴行,在外面的男人只感觉坐在这急诊室里的椅子上如坐针毡,听着里面细微的抽气声,他腾地一下站起来,仿佛痛的是他的似的。
“呃,那个……那个……这路途遥远,我坐车来的时候,这路又太颠簸,一路上磕磕碰磁,坐久了,我这自然就受罪了!”
宁之允的声音弱弱地传出来,妹妹这样掩饰事实倒让宁希唯更加地自责。
“唉哟,丫头呀,你坐车也不能省那么点小钱,要坐软卧屁股就不用遭这种罪了。”
护士不疑有他,只当年轻丫头不知轻重,为了省丁点钱而平白受了这罪。
“丫头,我帮你涂了些消炎的药膏,你好好躺一会,等这药膏完全吸收了,才起床。幸好没有外伤,晚上再来上一次药,估计明天就没啥大碍了。”
护士吩咐完便从另一边绕了出来,笑着对宁希唯说。
“宁副师长,你这妹子真是漂亮,你得好好待人家,下回让她坐软卧来,别为了省那点小钱去坐那种座位硬邦邦的长途客车。”
宁希唯不好说真实的原因,关于软卧的事就支吾着,听这护士的语气,显然又误会了两人的关系,便重复着这一路来已经说了N次的话。
“护士长,她真的是我亲生妹妹!”
他虽然不屑去解释这种小事,但这军营里的人性子率直,个个那张嘴都像刀子般又利又薄,那些露骨的话估计会让脸皮极薄的妹妹因被误解而难为情,于是又不厌其烦地解释着。
四十多岁的护士长摆摆手,笑嘻嘻地说:“得了得了,这妹子和亲生妹妹都是一样得用心的疼着!”这话说的,显然是不相信两人是兄妹之说。
宁希唯无奈,也不再作解释。坐急诊室等着这当口,才想起自己刚才怒火攻心,完全忘了要打个电话回家报个平安。于是就在急诊室拔了个电话回家。
“爸,允儿那捣蛋丫头现正在基地里,你们不用担心。其他的事,我回头再跟你们解释。”
宁希唯搂着宁之允的纤腰半搀着她步出医院大门,见她走起路来没什么异样,心里却是放心不下,便小心地带着几分讨好软声问道。
“允儿,痛不痛,要不,哥哥背你?”
说着,抢前一步在宁之允跟前蹲下身子,扭头示意宁之允爬上来。
从招待所来医院的时候,宁希唯是开着车子来的,当时他并不知道她伤得这么严重,给她垫了个软垫子坐着,也不过是三五分钟的车程。
只是刚才他听那护士长一说,加上他私下的联想,估摸妹妹这伤势应该挺严重的,若再像刚才那样坐着应该是蛮痛苦的事儿,心痛着妹妹的宁哥哥,也不顾得这基地来来往往的都是自己的部下,只蹲跪着等妹妹爬上背上。
“哥哥,没有那么严重啦!搽了药膏之后,冰冰凉凉的,好多了!”
宁之允刚才被哥哥黑着脸教训了一之后,也不敢抱怨哥哥下手重。一路上只是闷声不吭地低头认认真真反省起来。自己这牛脾气一上来就不计后果,当时确实没想太多,被老爸说了那么决绝的话,背着背囊只想着投奔最疼自己的哥哥。也没想过她这一声不吭地离家出走五天,会给家里带来怎么样的骚乱。
刚才在急诊室时床上趴着的时候,想到哥哥说家里这五天都给她闹得鸡犬不宁,还出动了警方四处寻找她的下落,她才开始害怕,怕回家不知又会被父母如何的痛骂,也怕哥哥会即刻将自己强行遣送回家。
现在见哥哥扭过头,墨黑的眸子满是宠溺地哄着她,她却不太敢造次,摇着头摆着手拒绝着哥哥的好意,完全没了平时那股粘腻劲。
宁希唯被她这突然的墨迹弄得头大,只是这人是他给弄伤的,先不说自己伤人的理由充不充分,原本不过是想给她个小惩诫却不料这手重得将她打得上了医院,他此时算是真正体会到,打在她身上痛在自己心上这话的真实用意。
“允儿,乖!是哥哥不对,不该下手这么重,很痛是吧,哥哥给你赔不是了!你就别生哥哥气了,让我背你回去吧!”
宁希唯软下声哄着,这情形让他想起她八岁那年,明明说好放学后一起回家,小丫头却贪玩和几个死党去逛街游乐去了。那一次,也将十二岁的宁希唯吓得半死,保镖在校园找了个遍,最终也弄得宁家上下人仰马翻,那丫头,却是一直玩到太阳下山,才施施然从公共汽车上走下来,背着一书包的战利品,哼着歌儿回了家。
十二岁的宁希唯,当时也没忍得住,硬是按着这个平时自己捧着护着的宝贝,打了她几下,结果,那小豆丁晚饭也不吃一古脑就跑林子里,爬樱花树上坐着,那丫头坐树上困得直打盹,却死抱着树干不肯下来。
那时的宁希唯,不得已作了很多承诺,哄了好久,才将这丫头哄下来。
想不到这十多年后的今天,这历史又再重演!
这驻基地的医院虽然不大,但基地的士兵每天都进行着超负荷的训练,常在丛林里摸爬滚打难免就会弄伤,所以医院门前并不冷清,来来往往的都是些穿着军装的士兵。
宁之允伫着哥哥背后坚持的时间,已经有好几个经过的士兵远远地行着军礼,大概在这个空军基地也没谁不认识他宁希唯。对士兵们的行礼,宁希唯只是点点头,并没有站起来回礼,看来,他是豁出去了,非要让宁之允趴他背上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