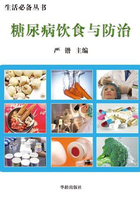舒安夏莞尔,不同于顾瑞辰的霸道,燕离歌总是用各种方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包括这身上的香气。然而,越是他这种隐忍和减少的存在感,却越总能让人心疼。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舒安夏刚要起身,那只修长好看的手,便盖上了她的侧肩,“别动!”。燕离歌的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半俯下身,修长的手指执起梳妆柜上的眉笔,晶亮的黑瞳中,满是柔情,“我给你画。”
舒安夏怔了一下,凝眸深深望着他,良久轻轻地点了点头。轻柔呵护的感觉从眉间袭来,一点点,细细的柔柔的,让人不得不迷醉。舒安夏轻轻地吸了吸鼻子,曾几何时,也有个对她细心呵护的男人,为她画眉,为她遮风挡雨,只不过……
不自觉地苦笑了一下,舒安夏不知不觉地对上了燕离歌那双温柔的明眸。他的眸中,清晰的是她的倒影。
这时,舒安夏想起了什么,眨眨眼,身体移开了稍许,手指伸向镜后。
忽地,她的脑中浮现出另一张脸,那张邪魅却几次救她于水火的脸。如果她把虎符给了燕离歌,会不会……
轻轻地摇了摇头,其实很多事情本就没什么对和错,随即,她心一横,直接从镜子的夹层中,抽出那只发簪。
燕离歌定睛看着她,眼底是愧疚、是感激,还带着浓浓的复杂。
舒安夏云淡风轻一笑,“物归原主。”
燕离歌轻轻地接过,半咬住唇,脸上闪过一抹痛苦之色,“上月母亲来提过亲。”
“我知道。”
“她逼我娶舒天香!”这是燕离歌离开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整个一个下午,舒安夏都心神不宁,不知道因为燕离歌的话,还是因为那只发簪可能个顾瑞辰或者顾家带来的后果,她向来有仇必报,有情必还,然而细数跟燕离歌和顾瑞辰相识以来,似乎一直都是顾瑞辰帮她解围,而她维护燕离歌。这种三角关系很可笑,但同样和很无奈。
“六姑娘——”惠人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她缓缓抬起头,只见惠人用手帕包了一包东西。
“果真被您猜中了,陈妈妈趁着今日出门买小厨房的食物,就去了‘保和堂’抓药,我已经找掌柜要了她抓的药,您看看!”说着惠人就把手帕包着的东西递了过来。
舒安夏打开了手帕,轻轻一闻,立即蹙眉,这是一种慢性药,要踢掉陈妈妈,得速战速决。
想到这里,舒安夏心里努定了一个主意。
从怀中拿出了一个淡绿色的瓷瓶,递给惠人,轻声吩咐。
夜幕刚刚降临,“夏园”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舒安夏晚饭过后就上吐下泻,昏厥了几次,舒浔易赶忙请来了陈太医。
陈太医的手指轻轻附上了舒安夏的脉,眉头越皱越深。
这时,舒安夏的小手忽然握成拳,陈太医一愣,视线上移,只见那张“苍白”的小脸上一直紧闭的眼忽然睁开,对着他迅速眨了眨,然后又立即闭上,他的手里多了条手帕。
陈太医快速地扫了一眼手帕上的内容,然后将手帕攥紧,捋了捋胡子起身。
“六姑娘不是生病,而是中毒!”
陈太医话音一落,舒浔易脸色一沉,拧起眉,“怎么会中毒?”说着,冷冽的眼神扫过“夏园”的下人。
以惠人为首的婢女们纷纷跪地。
“这种毒药叫”沉香“,无色无味儿,极其珍贵,只需一滴,便可让人吐泻不止,只需三日,就会让人脱水而亡。所以,下毒之人,手里必定还留有此药。”陈太医继续道。
舒浔易屏住气,眯起眼,“搜,立即给我搜!”
站在一旁的陈妈妈冷哼一声,这六姑娘平时得罪人得罪多了,她还没出手,就有人帮了她的忙,得意地扬起嘴角,心里暗暗祈祷,最好别抓出来这个人,三日之后,那便永久可以解决舒安夏这个大麻烦了。
惠人看着陈妈妈老脸上流露的那抹幸灾乐祸的阴狠表情,嗤之以鼻,不知道等会她还能不能笑的出来。
这时忽然有个婢女站出来,说今日的餐饭,是陈妈妈亲自送来了,没有经过他人之手。
陈妈妈嘴角抽搐,赶忙辩解,“是惠人叫老奴过来,说六姑娘找老奴有事。”
“奴婢没有叫过!”跪着的惠人赶忙反驳。
舒浔易冷冷地扫了一眼惠人,又扫了一眼陈妈妈。
陈妈妈心里咯噔一下,冷汗涔涔,一种浓浓的疑惑浮上心头。
果真,不出一会儿,一个小厮就拿着那个淡绿色的瓷瓶过来交差,“启禀侯爷,在陈妈妈房间里搜到了这个。”
陈妈妈一听,老脸一变,手指就指了过去,“你这个奴才,嘴巴放干净点!”
陈太医接了过去,打开瓶盖,一闻,冷冷地瞪着陈妈妈,“就是它”。
陈妈妈扑通一下跪地,“侯爷明鉴,老奴没做过,这是栽赃!”
“你一直负责‘夏园’的饮食,现在夏儿中毒,你还敢说自己冤枉?”
“老奴真是冤枉的,是六姑娘想除掉老奴,侯爷明鉴!”陈妈妈反应还算快,已经瞬间明白事情的始末,义正言辞。
陈妈妈话音一落,室内登时安静下来,落针可闻。
跪着的惠人轻轻弯起嘴角,六姑娘果然厉害,猜到了陈妈妈会这么说。今时今日的场合,即使陈妈妈是冤枉的,说了这种话,也就完了,这等于当着陈太医的面,狠狠扇了侯爷的嘴巴,侯爷会放过她吗?更何况,六姑娘安排的好戏,还有更精彩的部分呢,想到这里,惠人的眼睛闪了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