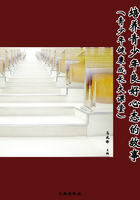西方建筑史的讨论课,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面积很小的独立书店中进行。那一天窗外飘着鹅毛大雪,更衬托屋子里的暖和安逸。参加的人数不多,正如夏海所说,这个讨论课,更多地像是一场在欧洲各国留学的时差党们的照片展。
即便如此,没有接受过学院专业教育的我,却还是听得津津有味。热烈的讨论冲淡了时间,课程结束后已经接近午夜。
“你没有开车?”夏海问。
“嗯。”我朝外面看,似乎坐出租车也很困难。
“先戴上这个。”他把他的棒球帽戴在我头上,打量着我,端正了一下帽子的角度。
“像不像变态杀手?”我问。
“哪有这么可爱的变态杀手。”他边说边帮我整理头发。
漫天飞雪,像白色羽毛般飘洒着。与其他人告别后,我与夏海朝最近的公交车站走去。
“你在前排记笔记的样子真的”夏海突然开始很开心地笑起来,他露出洁白好看的牙齿,声音稍稍沙哑,带点小性感。
“有什么可笑的?我上了年纪脑子不好嘛!一定要记下来才行啊!”我说。“话说回来,你照的那些照片,我真的很喜欢。”
“是吗?是很久以前的了。现在大概不会再有那种心境。”他说。
“你是怎么知道我对这个很感兴趣的?”我好奇。
“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美的东西,你都会喜欢。”衣袋里的他的手,轻轻捏了一下我的手。
我无意识地点着头,慢慢前行。
“你的小动作真的很多。”
“啊?”仍然沉浸在那些图片中的我,有些茫然地看着他。
夏海停下脚步,面对着我,用手指帮我擦去落在脸上的雪片。雪是冷的,他的手却是那么暖。
他看着我,朝我微笑,“表情那么丰富。”说着,捏捏我的面颊。然后继续朝前走。
我的心脏不规则地跳了一下。用手去摸他刚刚捏过的地方。
“高迪的圣家族教堂,那幅夜景的照片真的很震撼。”我说。
“你喜欢?我就知道你会喜欢。他的建筑是活的。欧洲中世纪时期有一阶段的建筑被称为‘燃烧的哥特式’,与高迪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改天我拿照片给你看。”夏海说,我发现他大多数的话语都没有惊叹号。我不明白是因为他内心一直很平静,抑或他真的很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只可惜没能亲眼见到。”我惋惜。
“去过欧洲?”夏海问。
“嗯。”我简单回答,去欧洲旅行,那是不是上辈子的事了?现在想来,一切为何都变得如此飘渺。
“那些雕塑多少看起来多少有些恐怖,夜晚更是。”我说。
“你该亲眼看看,感受会不一样。”
“这个时候若是还有末班车,应该是往我学校的方向,离你家还有很远。”夏海说着,握住我的手,放进他的衣袋里。
“没关系,只要能到市中心,出租车就会多一些。”我浑身上下哆哆嗦嗦地,声音也在不停打颤。
身后有车灯闪过,回头看,那辆末班车正以不快不慢的速度朝这边驶过来,看样子会比我们先到达车站。
“怎么办?”夏海问。
“跑!”我只说了一个字。
我已经忘记奔跑的感觉了。寒风呼呼地吹上脸颊再吹过耳边,身体有些僵硬,但是却瞬间暖和起来,夏海一直牵着我的手,两个人的脚步扬起飞雪,我们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狂奔。
只有短短几百米的距离。心情不知为何,竟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成长让我们付出代价,包括在街上奔跑渐渐变为不可能。如果你真的看见一个大人在马路上飞奔,那么你大致会想,这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
我们很难学会抛弃,所以我们的担子越来越重,最后我们再也无法奔跑。
终于赶上了末班车,我们大口喘着,彼此相视而笑。
本来只需要四十分钟的路程,因为恶劣天气,足足开了近两个小时。一路上,我一直不停地发抖。夏海解开棉衣的扣子,将我裹进怀里紧紧抱着,距离近到可以听见他的心跳声。
下了公交车,雪仍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市区内所有车辆都在街道上举步维艰,出租车少得可怜且都满员。我在寒风中站着,感觉身体正在慢慢失去知觉。
“走!先去学校我的公寓,这样你会冻坏的。”陪我等车的夏海最终提议。
“我怎么进去?我又没有学生证。”
“反正我也没想从正门进去。”夏海说。
两米多高的围栏,夏海轻易就翻了过去。方式也奇特的很,登上最高点后,他用手撑住栏杆以固定身体,然后用了一个前空翻,双脚完美地落在地面上。
看得我目瞪口呆。
“过来,心屿,别怕,我会保护你。”他说,在围墙的另一面朝我伸出双手。
我尝试活动一下冻僵的手脚以使它们不会在弯曲的时候突然折断,刚刚将一只脚抬起,已经费了我一半的力气。
“上大学时也没这样干过,我可一直是乖学生。”我一边爬一边抱怨着,夏海只是笑,担心地看着我。
“如果我现在扭头跑掉,你肯定追不上我!”我说。
“你肯定忘记我跑的有多快了。”夏海说。
夏海将双手放在我的腰上,将我举起并安然地放在地面,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们沿着没有路灯的小路悄悄地朝公寓的方向走着,由于做坏事而产生的兴奋感让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突然觉得整件事很荒唐。
我第一次走进他的房间,简单又整洁的摆设。床、书桌、电脑、唱片、书和吉他,和所有男孩子的房间没有两样,只是墙上多了很多摄影作品。蓝绿色条纹的被子和枕头,温暖的空气与灯光,我喝下一大杯热巧克力之后,靠在夏海的单人床的床头上,觉得自己终于从严寒中获救了。
夏海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衣服在走路是相互摩擦的声音听起来让人觉得安心。他忙着开空调把屋子弄得更暖和,厨房里乒乒乓乓地传出响声,片刻香甜的气息飘遍了整间屋子。收音机里传出一首英文歌的乐声,反复地唱着一句歌词:“Youhavestolenmyheart.Youhavestolenmyheart.”
丛极冷到极暖,疲倦感让我昏昏欲睡,我的意识有些恍惚,觉得仿佛是什么电影里的场景。这是个梦境吗?还是个相当不错的梦境呢!
夏海端一杯热巧克力走进来,盘起双腿坐在床上我的对面。
“喝吧!”
我接过来,先深深地吸了一口甜美的香气。
“别生病。”他说。
“不会,我很少生病。”
“小时候你经常生病。”
“你怎会记得?那时你不知道多小。”
我低下头,小口小口啜饮被子里的温热液体,它们沿着食道流进胃里,继而温暖了全身。
“留下来吧!外面很难坐到出租车,我担心你会感冒。明早我会送你上班。”夏海说。
“嗯。”我无意识地回答。收音机里已经开始播放下一首歌,可是刚刚那句朗朗上口的歌词仍然在我脑中徘徊。
“刚刚那首歌很好听。”我说。
“嗯。歌里写着一个男孩单恋一个女孩,却没有结果,有点伤感。”
“真的?”我问,大部分的歌词我都没有听清楚。
“嗯。”
夏海用微弱的声音说话,这完美的安静像是很怕被打扰似的。他向前靠近我一些,用手碰触我额前不太听话的头发。
“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会相信。”他问。
我看着他,很想伸手去触摸一下他的脸颊和刚刚长出的胡渣。
“夏海。”我叫他的名字。
“嗯。”
“在机场,你问我为什么?那么多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是想说没恨过你。”我说,“我没有恨过你。”
他脸上现出略略惊讶的表情。
“那个人我是说,爸爸,他”
这么长时间过去,我仍然无法顺利喊出这两个简单的字,“曾经有一次,我问他,最想做的事是什么?他回答我说,旅行,长途旅行。”
“昏迷的时候表情一直很平静,离开时看起来也没有太多痛苦。我想他是去旅行了,就像他一直盼望的那样。”
怎么回事?气氛竟会如此安详!曾经的我何尝想过,这些痛苦的回忆竟有一天会被时间慢慢抚平;曾经的我何尝想过,心中波涛汹涌的水面,如今竟连涟漪也难得一见了。
夏海与我对望着,我知道他此刻可以读懂我,哪怕只有此刻,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和谐地融为一体,这里没有地域、语言和种族的限制,他能看见我的思绪,安静祥和地舒展着,正如我能体会他此时此刻,正在把心中的重担完全卸下。
“我想说嗯能再见到你,我很高兴,我的意思是说”
他吻了我的嘴唇。
没有任何情欲的成分,甚至,那是连里面所包含的情感内容都极为淡薄的一个吻。
“怎么?是什么新式的打招呼的方式?”又来了,胡言乱语的毛病。
夏海出声地笑了,只是笑的有些寂寞。
他贴近我,将我抱在怀里,用下巴抵着我的头,深深呼吸,亲了亲我的头发。他身上的味道。我该怎么形容呢?
“对不起。我应该一直守在你身边。对不起。”他的声音渐渐低不可闻。
我很安心地闭上眼睛,睡意几乎立刻就袭来。那一整晚,我都睡在夏海的怀抱里。我们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他从后面抱住我,深沉的呼吸就吹过我的头顶,他握着我的手不肯放开。我脑中的思想就像是下课之后黑板上的粉笔字,一瞬间被擦得干干净净,什么也想不起来,好像在洁白柔软的棉花堆里,我一夜睡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