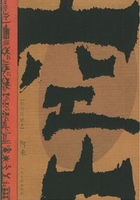一
革命就是考验,共产党员一切都是组织的,哪顾得了自己石板路旁,几株梅花,暗渡清香。
那是1929年早春,14岁的彭国涛一早起来,挑着一担茶水,跟随当教师的父亲,去迎接一支长途奔袭而来的队伍。父亲彭澎,明里是教师,暗里担任中共宁都县委军事部长。他告诉她:这支队伍叫红军,打仗非常厉害,其首领叫“猪毛(朱毛)”。
红军真的红眉绿眼?彭国涛有点害怕,她久闻红军青面獠牙,生食人肉。听说红军要来,国民党宁都县的县长赖世琮,早已望风而逃。
在县城南边十余里的石榴排,彭国涛见到了红军,却是些普通的人,有些失望。口干舌燥的红军队伍,似一条吸水的大龙,把满满两担茶水喝得精光。这支队伍被引进县城。当天,红军首领“朱毛”、陈毅等人,在城西温屋接见了他们。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处处受敌,疲于奔命,疲惫不堪。
“朱毛”告诉彭澎:红军很需要银元、粮食,以及各种日用物品。
需要多少钱呢?
红军说了个数目:最好能筹集5000块大洋。
要这么多钱呀?
从没接触过钱的她,以为那是个天文数字。由此,她第一次学做群众工作,在父亲的带领下,向四邻八乡的老表们宣传共产党、红军闹革命的宗旨。没想到,竟然很快筹集到银元5500块、土布300匹、草鞋和袜子各7000双……
“朱毛”这名字响彻湘赣,其实是两个人,一个是军长朱德,一个是政治委员毛泽东。红军得到如愿的支援,军容大整,毛泽东说彭澎工作能力很强。接下来,发动群众,创办学习班,在县城上西门温家屋召开会议,成立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亲自任命彭澎为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是苏区宁都红色政权的第一任县长。
彭澎的“县长”,只执政十几天。5月上旬当选任命,5月中旬,红军离开宁都,彭澎便兼任宁都县游击队队长,带领县游击队转移到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翌年7月,彭澎被捕。
彭国涛过早地介入革命,也过早地介入了痛苦。初阅人世,有两件事情系着两条命,令她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1929年初冬,骤冷的气温使人难以适应,彭国涛的弟弟彭寿平,突然不吃不喝,患了“哑口症”(白喉)。这在缺医少药的当时,就是大病。她与母亲陈氏苦守,巴望父亲归来。
那天,是12月8日。宁都县革命史上,一个著名的日子。彭澎与游击队副队长肖大鹏(后任红20军代理军长)等人带领游击队打进县城。当时,游击队有300多人,160多支枪,经周密布置,游击队一举捣毁县衙门,营救出关押在监狱的王俊的夫人及其他战友。
黑暗如墨的夜,三双眼睛似三对磷火,微弱地闪烁着,父亲一天一夜未归,弟弟的双眼,便在与妈妈、姐姐的对望中,永远闭上了。
彭澎回家,母亲抱着弟弟的尸体,泼命大哭,怨声不止。抚着独子尸体,彭澎愧疚不已,却并不悔错,哽声说:“这就是考验,我是共产党员,一切都是组织的,哪顾得了自己!”考验,考验!面对生死,这两个字,彭国涛记了一辈子。
接下来的还是考验,更让她永生不忘,那是眼见父亲绑赴刑场,壮烈牺牲。
游击战争,风餐露宿,彭澎积劳成疾,左腿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战斗中时常发作,翌年7月的一天,队伍转战湛田乡李家坊,与大股敌人交火。彭澎行走不便,被敌人抓获,押送期间,却被会同区的群众抢救回来。
白军知其腿脚不便,行走不远,派兵轮番搜索一周,仍无结果。遂将会同区桐口、腰田、桃枝等村村民,集中于桐口村真君庙前,声言再不交出彭澎,烧毁全部房屋,枪毙所有村民……这时,彭澎突然从真君庙神座下挺身而出,大吼:“彭澎在这里!”重新入狱,历经十几种酷刑,身残伤重的彭澎以死抗敌,他脱下身上唯一的毛衣,请送饭的牢卒换一包砒霜。毛衣是贵重物品,牢卒贪图毛衣,又惧怕死人,给他一包掺假的砒霜,彭澎服用后只落得个半死不活,被转押入县城大狱。
4个月毒刑。彭澎拒绝利诱,坚贞不屈。
为了儆戒民众,处决政治犯时,当政者喜欢搞公审大会。那年11月16日,一乘滑杆竹轿,抬着已经气息奄奄的彭澎,进入人群云集的县城体育场。
体育场北面司令台,台下,彭国涛用破衣遮头,隐在攒动的人群中,咬着嘴唇目睹父亲的惨死。
县清乡委员会主任邱伦才,站在台上,口沫飞溅,历数彭澎的革命“恶迹”,然后,煽动地大声吆喝:“大家说,像这样的坏人,要不要杀掉呀?”一些事先组织好的人,大声应答:“要杀掉!”混乱中,也有人喊:“不要杀掉!”邱伦才又吆喝:“大家都说要杀掉,是不是?”一位老者就说:“杀他做什么,他现在已经被打成毁人了,还是不要杀!”询问大家,只是个形式,杀肯定要杀的。邱伦才命令刽子手用刑。
刽子手名叫刘炳南,得了36块银元杀人费。为了避邪,他穿一身白纺绸褂子,持一柄三尺长的鬼头大刀上了台。刘炳南是有名的刽子手,力气很大,但这次的活计却不利索,他挥刀猛砍,连续7刀,竟然没有把人杀死。
32岁的彭澎,脖子几处血水怒溅,射到旁人身上脸上,嘴里仍叽哩咕噜地叫喊:“这,就是考验——”彭国涛昏倒在地。
刽子手的手发软,有些慌,台下有人帮忙,嘶喊:“是他背上的标挡住了,要拔掉他背上的标,要拔标!”刽子手慌里慌张拔标,再砍,第8刀就把头砍下来了。
白军把彭澎的尸体拖去喂狗,将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门上展览,7日后,头颅突然不见了,从此,尸骨无寻。
在仕途与良心之间,她经受考验选择了后者斩草除根,搜捕在继续进行,考验在顺序延伸。母亲被捕入狱,15岁的彭国涛成为孤儿,四处漂零,躲藏到大山深处,过着野人般的生活。1931年,红军在荒无人迹的破庙里,找到了“野人”彭国涛。
中共宁都第一任县委书记,牵着这位烈士遗孤,在弹痕累累的红旗下宣誓。
那年,她16岁,加入“共青团”,被派往父亲战斗过的会同区,就任会同区苏维埃妇女部长。她的工作范围涉及几十个村,十几里方圆。
动员和组织妇女拥军、支前、打草鞋、慰问红军、护理伤兵……踏着父亲的足迹,彭国涛积极性特别高,似有两条生命,风风火火地工作。很快,会同区苏维埃成为白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3年仲夏,一个月黑风高夜,乘苏区边缘空虚之机,白军的大刀会摸进区苏维埃,见人就杀。恶狠的大刀把门板剁烂之际,彭国涛翻身跳出围墙,仗着身子灵巧,逃得一条性命。慢她一脚的区苏维埃老文书,命丧黄泉。
为了阻挡白军入侵,为了报仇,就要有强大的红军。
此后,扩红成为她最重要的工作。上级说:苏区能否生存、巩固,就在于红军的多寡。必须不断地扩红,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苏维埃就胜利了。
彭国涛扩红扩了一百多人,她不知道一百万是多大的数目,只是走村串户,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一个人一个人地动员。不知是不是因为没有扩大到一百万红军,红色政权没有很快取得胜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驮上马背,撤离了中央苏区,她扩红的一百多人也跟随离开。
一走,就走得很远很远,一走就走了十几年。
白色恐怖四处弥漫,她又成为当局追捕重点,似一条孤魂,在大山间飘泊,又过上了野人的生活。
时光在游荡中消失,每每生活苦到不堪忍受,人就会想到死,想到死时她就0会想到“考验”,既然是考验,那就要活着,即使是为了考验。
敌人对她的追捕松懈下来,她的年龄也已长了上去。一般人家的女子,十六七岁嫁人,她二十岁仍找不到婆家。因为,彭澎太出名了,彭澎的女儿也跟着“出名”。
在亲属的撮合下,四处流浪的她,嫁了个国民党33旅的大兵。姓黄,名叫黄国文,一个老实巴交的壮丁。
本想寻一棵小树庇荫,没料到,却是找到“蒺藜丛下躲雨”。
夫家原本家徒四壁,被她一“高攀”,虽无治罪,却受株连,立即销差,扒掉军服,取消俸禄,沦为苦力。
这对苦难夫妻,新婚期间便为生计所困,一个帮人挑水,一个帮人洗衣。这是最辛苦、廉价的劳动,一担水才卖一分钱,洗小孩的衣裳月薪4毛,洗大人的衣裳月薪5毛。即是如此,也没有多少衣裳来洗,他们得不停地揽活做。除了挑水,黄国文砍柴卖、帮人挑担、打猪印,彭国涛则帮人裁剪衣服、做扣子、帮人站柜台。
望眼欲穿。1949年7月,当年的红军终于回来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她重新参加工作,担任了会同区南当乡妇女主任。在攻克翠微峰的系列战斗中,她积极支前,担任了负责检查、处理女俘的工作。由于工作出色,1950年,她调任梅江区(城关镇)妇女部长兼优抚主任,驻第四街街政府协助工作。她没日没夜,忘我工作,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发展,风风火火地奔走。
1951年,作为革命烈士子弟的代表,她随南方老革命根据地代表团,受邀前往北京中南海,参加了在怀仁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天安门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北京逗留期间,朱德听说老熟人彭澎的遗孤来了,还特别发出邀请,她应邀来到朱德总司令家里做客,叙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数十年后,朱德的女儿朱敏,重访老区宁都,还特意找到她长聊。
女人的荣耀,可能是男人的“灾难”。黄国文,成为家庭中一个尴尬的角色。国民党大兵的历史,使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1951年早春,几匹来自北方的大洋马,急促的脚步把鹅卵石巷道击得直冒火星,马群嘶叫,直奔米市巷彭国涛家。
“砰砰砰—”门被敲得很响。黄国文从门缝瞧见,大洋马后面,威风凛凛,有3个身着军装,荷枪实弹的人。他被吓坏了,估摸这伙解放军是来捉自己的,想溜,腿脚抖得像筛糠,拼命使劲就是迈不开步子。
来者,是解放军某部的刘师长,衣锦还乡。当年,是彭国涛爬山涉水,去那个人迹罕至的山村,从牛背上把他拽下来,扩了他的红。他把手中的竹鞭一扔,拖着两条大鼻涕,两脚泥水,走上一条光辉的战斗之路。饮水思源,刘师长不忘自己革命的引路人,特意来寻源谢恩。破屋里,看到还很没有“进步”的恩人彭国涛,刘师长带她去走访了专署专员、县委书记、县长。
临别,刘师长悄悄地但却明确地劝她离婚:“一个红军干部、烈士子弟,与一个白军搅在一块,会冲淡颜色哩!”县里也有意,要让她担任县委妇联主任,可是,她还不是党员,红光灼灼的县委妇联主任,背后立着个白军大兵,那政治影响肯定不好。
蕴意婉转而明确,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政治难题,也是一个人生考验呀。结婚之日起,木讷的老公就在思想、经济、生活上,日愈处于从属地位,连她生育的儿女也统统随母姓彭。解放后,他成为一名菜农,与她的干部身份拉大了距离。迟钝的丈夫,也屡屡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别扭,多次提出:会妨碍她的前途,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