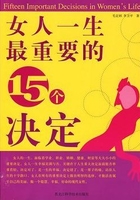病房里很安静。
诡异的静,呼吸轻缓。
蔡冰雅站在窗户边,身子明显一僵。
没几秒钟的时间,纪念开口:“妈,那是路钧笙的妈妈,这些年不在洛临市,你认识她吗?”
“当,当然认识。”蔡冰雅有些仓惶,笑容机械的涂抹在脸上。
“快二十年过去了,难为你还记得。”段雨烟勾唇一笑。
“路夫人风华绝代,真让人过目不忘。”
段雨烟将手中的礼品搁下,睐了她一眼,冷笑,“东西太好了总让贼给惦念着,并不是件可喜可贺的事,纪夫人,你说呢?”
她此刻的心汹涌着滔天巨浪。本以为随着时间沙漏般的流逝,那种背叛的痛苦会从心底慢慢冲刷走。直到今天真相遇,才知道,那深深根入骨髓的刺早已在心房腐朽成血肉的一部分,如若要拔除,只能挫骨扬灰。
呼吸被堵住,蔡冰雅认不是,不认也不行。但,很快从初见的失常中恢复过来,撇撇嘴,“好东西,当然每个人都会想着分一羹。”
“能分到固然好,就怕肠胃消化不了。”
“吃……”
“妈。”纪念声音很大,清亮,对话被打断,所有人的视线汇集到她身上。她心里此刻是矛盾的,一面,母亲曾经害得路钧笙一家母子分离,父子不亲,她打心底感到愤怒,另一方面,这个本应该社会共讨伐的角色是自己的母亲,生养的恩德不是可以随便抹去的。
人呢,在做旁观者的时候,永远可以快速做出最果断的决定,但一旦涉及自身,再简单的纠缠都能拧成麻花。
“我觉得路伯母的话很对。像最近我都没闻过肉的味道,你现在要给我上一盅油腻的扣肉,我肯定想吐。”纪念眼珠骨碌转,蹙起一弯月眉,一手拉拉路钧笙的衣袖,一手揉着肚子,“路钧笙,我醒来这么久了,你还没给饭吃的。”
她撅起嘴,琉璃色的瞳仁里,委屈丰腴。
路钧笙墨曜般的眸,幽深漆黑,盯得她快要泄功了,才捏捏她的鼻子,轻哼,“是,我家小猪要进食了。”
滞停的空气微微流动。
段雨烟看着两人,淡淡一笑,上辈子的恩怨,倘若将下一代牵扯进来,只会将痛苦放大。她的儿子已经在因她任性留下的苦海里荡涤了近二十年的光阴,她不能图一时的痛快,让另一个快乐善良的孩子跌进来,何况这个女孩将是与儿子渡过一生的人。
她没有理由反对这桩婚事,这是她丈夫欠下的债。
疼,麻痹。
段雨烟开口,“我还有些事需要去处理,先走一步了。纪念,你好好养病,将身体调理好。婚礼的一些事,我会找人来打理。”
“好。”
“纪念,我去送送我妈,你要吃什么?”
她报了几个菜名,生辣冻的一律全被路钧笙一票否决。望着消失在门口的身影,纪念心底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