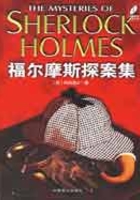父亲说:“为了爱情,为了自由,到那边去!”
“在裕盛客店那一夜我们俩都没合眼。说来奇怪,她在门外掀动帘子的一刹那我心里动了一下,就觉得是她来了。刚转过身就挨了一巴掌。她的眼睛像要喷火似的,脸上淌着泪水,浑身湿漉漉的,发林向下滴水,两腿溅满了黄泥。一盏麻油灯在桌上晃悠,我和她面对面站在灯影里。我很想上去拉着她、抱住她,可我的腿像失去了知觉一样抬不起来。我不知道对她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怎样把她让到了桌边的椅子里。拿起茶杯想起暖壶里没水,我掀开帘子朝楼下喊伙计送开水,这才想起问,你还没吃饭吧?说过这句话我觉得很蠢,看她的样子还用问?
“我从书箱里找出一身干净衣服,端起脸盆往外走。她堵在门口说,干啥?我说,打点热水。你在屋里洗,我给你弄饭吃。
“她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先给我要个房间!
“你没看今晚客店都住满了?没房间了。
“那我自己到街上找旅社去。
“算了,你……将就点好吗?待会儿我到前边马棚里睡。
“其实她也没到外面找旅社,我也没到马棚去睡。我把热水给她打上楼,然后到下面去让客店老板做饭。等我跟着伙计把饭弄到楼上,她已经换好了衣服。她披散着湿发,穿着我的衣服,像穿了一件睡袍,人显得更妩媚。看着她这副样子我抑不住内心的冲动,很想抱着她对她说,我爱你。店伙计把托盘里的饭菜摆放到桌上,她用怨恨的目光盯着我。我不饿,我坐会儿就走。
“她的眼神弄得我很胆怯,说话也有点结巴。外面……还下着雨呢……
“她很干脆地说,我能冒雨来,就能冒雨走!
“店伙计的脚步声沿着楼梯往下响。我们俩互相看着。我说,小如,你这是何必呀?
“她的眼睛里又开始闪出火花,你说我何必?!
“我冲过去把她搂在怀里,她扭动身子挣扎。我不顾一切地搂紧她,嘴唇贴着她的脸颊发疯似的说,我爱你,小如!我爱你!
“眼泪从她眼里淌下来,眼泪也模糊了我的眼睛。她贴着我的胸脯流泪,我用下颏蹭着她的眉毛。那会儿我的心像碎了一样,喉咙口像堵了棉花,什么话也说不出。我抚着她的后背,不知该怎样安慰她。泪水流过我的下巴,打湿了她的眼窝。
“连声招呼也不打就走了,还说什么爱?
“我把她的下颏挑起来,看着她泪水模糊的眼睛,小如,我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林春生走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会像我二哥一样照顾我,每星期来看我,可现在……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你们谁也不管我了!
“她像受伤的小鸟一样偎在我胸前哽咽,我用手抚摩她的肩背,嘴里轻声叫着,小如!小如!……
“你们男人为什么都这么自私?
“我真的……我不知道……”
我相信父亲和母亲的初吻就发生在这一刻。父亲双手捧着母亲的两腮,用发烫的嘴唇安慰她的责备,母亲的泪水在父亲的亲吻中涌流。两人相拥着站在那儿,一边亲吻一边诉说各自的委屈。后来父亲松开双臂说,你饿了吧?饭菜都凉了。
母亲坐在桌边吃饭,父亲满怀怜惜地看着她。“她淋雨走了那么远路,连顿热饭也没吃上。”然而那桌冷透的饭菜也许是母亲一生中最难忘的晚餐。
父亲挤坐在母亲身边,身体紧挨着她,时不时伸出胳臂想去搂她。母亲眨起白眼,拿筷子敲他的脑门,别捣乱!
最终他还是把手搭在她腰间,脑袋搁在她肩上,侧过脸轻吻着她的面颊。母亲生气地放下碗筷说,我不吃了!
她一站起身,父亲又开始感到紧张。屋檐上的雨水发出滴滴沥沥的声音,她走到窗边听着外面的雨声,父亲小小心心看着她的脸。扭过身的时候,她眼里现出怨怼的目光,仿佛她被雨夜阻隔在客栈里全是他的过错。
“要不……我到马棚去吧?
“她把眼睛翻了翻。要是别人知道,这算咋回事?
“我咧了一下嘴,谁会知道?
“赵达知道。是他对我说你在这儿。
“赵达不会知道,谁也不会知道。
“我再次向她伸出胳臂,她把脸沉下来。你最好离我远点,家里有媳妇的人还有脸跟别人谈情说爱?
“我涨红了脸,冲她大声嚷,谁说我有媳妇?我啥时候承认过她是我媳妇?
“跟你拜过堂,办过喜事,明媒正娶,你不承认就算没这回事?她寸步不让地瞪着我。我张口结舌,气得大口大口喘气。
“好吧,明天我登报!
“我气呼呼地在书箱里翻找纸笔,当着她的面写声明。
“她把我写好的声明拿起来默看了一遍,抬起头说,马昌,别忘了,我也是有主儿的人!”
父亲的聪明睿智突然觉醒,头脑也变得敏捷,“你也登报!我登报离婚,你登报退婚,然后咱们再一起登个订婚启事。”
“你想得太简单了,马昌!林春长来了。——我知道她说的是她大哥。知道吗?他到了西安,住在金钟烟厂办事处,这两天就要来接我回家。
“咱们到那边去!找林春生去。昨天在赵达那儿我见了一个人,是那边派来招干部的。内地迁来的学校有不少老师和学生都想到那边去,近几天就要走一批。你愿意的话,咱们一起走。你大哥总不能到延安去找你吧?
“再有半年我就拿到毕业文凭了,现在走,不是白读了两年多?
“一张文凭有那么重要?比爱情更可贵?比自由价更高?为了爱情,为了自由,咱们必须到那边去!只有推翻这个封建专制政权,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咱们才会有幸福。”
那一刻,父亲庆幸他从二舅那儿读到的小册子。那些纸张粗糙、印刷模糊的小书成为他征服母亲的有力武器。革命理论能给人激情,让他在母亲面前战胜怯懦,发挥出雄辩的才能。
黎明时分雨停了,院里传来早起客人咳嗽、走动的声音。父亲把灯吹熄,窗纸上立刻透出灰白的亮光。
“黎明的曙光穿破客栈的黑暗,穿破我和小如心头的迷雾。经过彻夜长谈,我不再犹豫,她也不再彷徨,我们决心一起到延安去。林春生一直没消息,我和春如都相信,到了延安就能找到他。”
母亲回学校清理东西,父亲在县城等她。他忍受着初恋情人离别的煎熬,在客栈里躺一会儿,坐一会儿,懵懵怔怔,没法从那一晚的甜蜜中醒来。对于初恋的人,幸福是一种无时无刻的思念,是一种揪心的感觉。时间成了一种折磨。他沉浸在欢乐的痛苦中,有时想唱,有时想哭,有时想到城外去奔跑。母亲用过的毛巾、牙刷、茶杯,不经意间丢弃的纸团、粉屑,都让他久久凝思,眷恋不舍。他把床枕上的一根长发捡起来,对着亮光细细察看,然后小心地夹进书页,仿佛嗅到了她蓬松的乌发里散发出的撩人魂魄的气息,禁不住心情激荡。
从第二天起,父亲吃过午饭就出城,站在大路口向道路尽头眺望。大路白白的,弯弯的,空空的。陈官营离县城五十八里,即使起早动身,走到县城太阳也该西斜了。阳光迷离,风息云驻,偶尔有老乡赶着车从塬头那边走过来,野腔野调地唱信天游。这悠远苍凉的歌声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山岭如一堆黄褐色的云在晚霞里起伏,渐渐失去光亮,沉入苍茫……等不到母亲的影子,他心烦意乱,猜测着究竟出了什么事,也许她正摸着夜色赶路?也许她病了?也许她遇上了什么麻烦?他在路口走来走去,直到星光满天才怏怏往回走。晚饭也懒得吃,灯也懒得点,躺在床上抽着烟,一次次忽然站起来,走到门口,听着楼下动静,探头向院里张望。
第三天黄昏,他决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见不到她,就一直走到陈官营,走到学校。
“今天我必须看到她。一定要找到她。”
处暑已过,秋风乍起,秋虫的鸣声透出几分凄清。父亲敞开衣襟,让夜风吹拂他的胸膛。独自走在高原的夜路上,他一路走一路放开嗓子唱,“想你想得心花乱,手掰着算盘算时间。……麦苗苗青格整整想到今,谷子儿黄想你到下雪天……”
走了大半夜,黑黝黝的天空才现出一弯月亮。下过一场雨,脱脚河的河面宽了,水也比原来深。
“走上崖畔,看见那排窑洞,我的心像要跳出来似的,张大嘴喘不上气来。场院静悄悄的,一半月色一半暗影,窑洞高处有两只狗跑跳着吠叫,一种恍恍惚惚的预感压迫着我的胸口。
“我不敢走近,就在崖边的树影里坐下来。汗水溻湿的衣服经风一吹,凉凉硬硬地贴在后背上。
“月亮慢慢暗下来,塬头上的天空越来越黑。天快明时困乏难挡,我把头搁在胳膊上混混沌沌打盹。一阵哗啷哗啷的铃声把我惊醒,睁开眼,看见校工摇着铃在窑洞之间的路上走。
“天大亮了,学生宿舍里响起乱糟糟的声音。我站起身,盯着她的宿舍。
“窑门打开,两个女生端着脸盆走出来。有人在窑洞里洗脸,有人到场坪上刷牙。我仔细看着出出进进的人,看到了冯敏,却没看见她的影子。我的心慢慢往下沉。
“冯敏看见我时的样子加重了我心里的阴影。她左右看了一下,好像不想让别人看见。
“我闪到崖后,站在场坪下等她走过来。
“见到我,她说出的第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林春如的大哥来了。
“她大哥到这儿来了?
“她前天晚上收拾了行李要往县城去,下到谷底被她大哥追上,两人在河滩里吵了一架。
“现在呢?……现在她在哪儿?
“林春长把校长请来,给她办了肄业证,带她一起到西安去了。
“已经走了?
“昨天下午走的。
“刹那间我失去了意识,好像一下子坠进了深渊。
“他们走垭口街,出陈官营往东北……
“雇车了吗?
“雇了一辆车。
“我什么也没想,拔腿就往垭口奔。”
父亲赶到垭口,天上已经升起一弯月牙儿。他一天一夜没吃饭,没喝水。“不知道饿,也不知道累,就是口渴。嗓子里冒火,两片嘴唇粘在一起,动一下像揭一层皮似的疼。
“镇子很小,店铺都已关门,旅店也就一家。黑乎乎的小街上只有客店门前的灯笼幽幽地亮着。
“我走过去,在两扇破旧的大门上拍一阵,里面传出几声狗叫,然后有人问,谁?我大声说:住店的。
“走进客栈,我用眼睛抡了一圈,看到院里停了一辆车,马棚里有几头牲口在槽边拱着吃草,我的心狂跳了一阵。
“店伙计给我弄了一碗面。我一边吃一边和他聊。堆尖一碗臊子面,挑了几筷子就吃完了,我不知道它是怎样下肚的。
“从伙计那儿弄清楚了,车是从陈官营来的。一男一女一个车夫,明天到西安去。我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