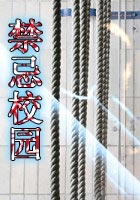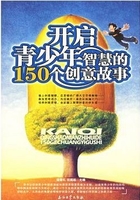现在我们都习惯把报纸称为垃圾,人们漫不经心地把它翻阅一遍,然后随手扔进废纸堆里,甚至连标题都懒得一一浏览。然而这些发黄的报纸和过眼即逝的文字,在年深久远之后深深吸引着我,为我打开一扇想象的大门,引我穿越时空,走进另一个世界。竖排的加了边框的版面,旧式的铅字字型,粗糙的印刷……每一行都勾起我对岁月的遐想,人生的感叹,使我心驰神往。报纸其实就是历史。如果报纸是垃圾,历史当然也是垃圾。
“我刚吃过午饭,回到房间打算躺一会儿,店伙计走进来说,外面有人找。
“我走出来,看见街边停着一辆黄包车。春如坐在车上,身边装着她的行李、书箱和提琴。
“你把房间退掉,马上跟我走。
“看我愣在那儿,她说,我大哥到车站去提货了,咱们赶快走。
“她从挂兜里掏出一张《震旦报》递给我,手指在报纸上敲了两下。我抖开报纸,眼睛在版面上寻找。在第四版最下边,我看见‘马文昌与肖芝兰的离婚声明’。我把它读了一遍,没来及抬头说话,一转眼,‘林春如与孙鹏举解除婚约的声明’闯进眼帘。两条声明相隔不远,登在同一个专栏里。字体、格式差不多,没加花边,没做装饰,只用几个断续的星点分隔开,周围是一大堆杂乱的启事。某某人丢失了某某学校的介绍信;某某人宣布自己的商号开业;某人声明在得月楼举办婚宴,等等等等,把我们俩的声明混在这堆乱七八糟的启事里,我看了心里很不舒服。
“他们怎能这样登啊?
“她把嘴唇抿了一下。你叫他怎么登?
“这不像是开玩笑吗?
“开不开玩笑全在自己。反正报已经登过了。
“她嘴上说等我的声明,实际上没等,这让我有点惊喜,我也就不再介意把神圣的宣言混在一堆乱七八糟的广告里。她说得对,反正登过报了,现在我们俩都是自由人了。
“你还是快去退房间吧,咱们赶快走。
“我把房钱结了,叫了一辆车把我的东西装上。
“两辆三轮在街上拐来拐去,最后钻进一条胡同,停在一个小杂院门口。”
在一座古老城市的一条古老的小巷里,母亲把她的行李和父亲的行李放在了同一个小屋里的同一张床上。
这便是万年历上父亲用红笔圈着的那一天。
“土坯垒的炕,打扫干净之后显得宽敞、舒适。放上被褥,摆上枕头,立刻就有温暖的气息。”
这是个市民聚居的小巷,带着西北城市的特点。由于黏土胶泥的缘故,高低错杂的房顶交混着赭黄和灰白,房屋呈现出白色基调。一棵老槐树挤在房角边,枝丫伸在屋檐上。树叶稀疏,枝干苍老。屋檐下有条砖砌的流水沟,淌着几家人泼出的脏水。
父亲和母亲的炕紧挨前窗,炕边有一个当小桌使用的矮柜。抽屉上缀着铜拉环,柜脚镶着花饰,雕花柜门上垂着两个树叶形的铜拉手。
“你母亲把衣服放进柜子,书籍摆在柜头,笔和杂物放进抽斗,提琴放在炕头上。尽管我早已向往着这一天,心里勾画过这样的情景,可是走进小屋,看着这个一脸严肃的女孩像过家家似的动手收拾整理这个小窝,我心里还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事情来得太突然,超出了我的想象,一切都像做梦。一盏十瓦的电灯泡吊在房梁上,把屋里照得恍恍惚惚。卖酿皮子、饸饹面的吆喝声不知从哪儿传过来。房东大娘在关紧的风门后呼噜呼噜抽水烟,不知她会怎样猜测我们这一对年轻人。
“她在小屋里转着身子收拾东西。
“订婚启事用不着登了,省下五百块钱够咱们吃一礼拜。
“我惊奇地看着她,林春如怎么一下子变得这样会精打细算了?”
父亲发现他已经变成长安城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好像他一直生活在这条小巷里。他试着像院里的邻居那样料理自己的生活。虽然有点陌生,但很新鲜。他在屋檐外狭小的空地上把一堆煤泼上水,和均匀了,从房东那儿借来一把奇妙而简单的工具,把它夹成扁圆形的煤球,在一片能够见到太阳的空地上,把它们排列成花瓣似的队形。晒干后的煤球像池塘里捞出的螺蛳。在小煤炉里填上燃烧的木柴,放进几个黑螺蛳,用一把破扇子使劲扇。满院弥漫起呛人的烟雾,父亲鼻洼里添了两点黑墨,手脸蒙上一层烟色,使他那张脸和周围的环境更加谐调。他会做煤球、生火了。两个人合伙做了第一顿饭。从小长到这么大,他还没做过这种事。这让他感到既新鲜又自豪。
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父亲的档案里都没有记载,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当然也不会被人提起。然而这一年这一月这一天的八天之后的一天,却是父亲履历表中绝对不容忽视的日子。虽然他没在万年历上做出任何标记,可在父亲逝世后,为父亲写悼词时,这一天的重要,不亚于他的生日。
“1945年9月14日,经赵达、吴江天介绍,进入西北地质调查短训班学习,从此参加革命。”
多亏父亲当初写自传时没忽略这行文字,他的人生价值才有了确切的证据,在最倒霉的时候,他和家人们的自尊也能得以维系。不管他生前犯过多少错误,遭遇过多少挫折,有了这行文字,父亲遗体上覆盖的镰刀、斧头旗子便会让人觉得货真价实,我心中无法拂去的优越感也更感到踏实。在父亲一生的许多时刻,平静的时候,激愤的时候,高兴的时候,感叹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算不上长征老红军,可1945年我就参加了革命!”
这一行字,也是他和母亲在长安城里八天浪漫生活的结束。
“进短训班之后,我们又在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才跟房东结算房钱,雇了一辆车把东西拉到马王寨。
“短训班设在一座大院里,据说从前是戏班子的科班营地。一座草泥顶的大房子,男生在东头,女生在西头,中间是木隔板夹壁。廊檐下放着脸盆、饭碗。东屋是两间厨房,支两口大锅,一个长案子,放着笼屉。大房子拐角的小房子里住着指导员老徐。拐角深处是厕所。
“一走进大院,登时就有自由解放的感觉。就像歌儿里唱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俩像从地窖里走出来见了天日,那兴奋轻松劲儿简直没法说。大家都很开明、开朗,相爱的人可以大大方方在一起,同来同往,不用遮遮掩掩。她站在男生门口喊马文昌,我就答应着走出来,跟她一起拿着碗筷到厨房去打饭,和大伙说说笑笑蹲在院里吃。吃完饭一前一后到装满清水的木桶那儿去洗碗。然后走到廊檐下把碗筷放好。学习的时候一同坐在长凳上。讨论的时候围在一起讨论。朝夕相处,心里暖洋洋的。
“因为是在敌占区,我们听课的时候只准听,不准往本子上记。实在忍不住,就用我们俩的英语单词简写法把想要记忆的要点记下来,然后私下里交换。在这期训练班的一二十人里,我们俩是最惹人羡慕的一对儿。
“其实那个短训班跟地质没一点关系。我懂什么地质?它是西安地下党开办的西北军政干校转送站。参加训练班的人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个把星期,就会分期分批转移到那边去。到陕北的军政干校里再受半年几个月的训练,就被派到军队或解放区去,成了革命干部。”
父亲在那儿学习了一星期。这一星期不但是他一生骄傲的资本,还使他有一批可资夸耀的战友,如同古时候的同榜进士,无论何时说起来都能为父亲增添荣耀。现在某人做了省委书记、某人做了市委秘书长……当初他们刚到训练班来时可是一副傻唧唧的样子,抠脚趾、擤鼻涕、打呼噜、穿错鞋子……某某在班里讨好吴雪,想跟她搞对象,大家不断拿他开玩笑;某某爱出风头,大伙都不怎么喜欢他……在父亲的故事中出现过的人,只有一位刘伯伯在危难关头曾经帮过他一把,其余人物父亲好像并不看重,他们也不大和父亲来往,有时候我不免怀疑他讲述的这些逸闻轶事会不会被添油加醋、张冠李戴?当然,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写小说的素材,反正小说少不了虚构。也许父亲的虚构比我的虚构更令人信服,容易为史家采信。
“这天的课结束得很早,我问指导员讨论不讨论?指导员说不讨论。我正觉得奇怪,看见司务长老贾担着挑子从外面回来。一头是肉、青菜,另一头装着梨子、苹果、柿子,还有一个很大的纸包。老徐笑眯眯地说,下午不上课,中午改善生活,晚上开娱乐晚会。
“老贾把纸包打开,里面是码成几摞的月饼。我眼睛一亮,大声说,都忘了!今天是中秋节?
“从老徐说话的神态我猜测也许过罢节就会往那边转移。
“我转过身去找春如,看见她和吴雪一起往宿舍走。我站在女生宿舍门口喊,林春如,林春如——
“她一边答应,一边在屋里摸索。屋里的女生都在叽叽喳喳报节目,有人喊着让她扭秧歌。她应声说我拉提琴吧,我没红绫子。
“等她走出来,我看见她和吴雪都换了衣服。我打量着她俩,你们这是打算上街吧?
“我出去买点东西。
“她俩向指导员请了假往大门外走,我跟在身后问,你买啥?
“吴雪说,你们男生别问我们女生的事儿。
“我尴尬地退回来。
“她出去时间不长就回来了,好像并没走出多远。吴雪把手里的石榴递给我,瞧,这是林春如给你买的。
“我盯着春如的脸,觉得她的脸色不怎么好。
“她没抬眼看我,也没跟我说话,把挂兜交给吴雪就到小屋那儿去找老徐。
“她怎么了?她在街上……
“刚才在门口碰上个人,说是她大哥厂里的伙计。那人拦着她在路边说了一会儿话,林春如的脸色就变了。
“我走到小屋外,看见她正向指导员汇报。我不好进去,就站在院里等她。指导员把她送出门外,脸上带着笑安慰她,然后把老贾叫进去。老贾既是我们的司务长、采买,又是我们训练班的排长。
“她闷头往宿舍走,我跟在她身后。一直走到伙房门口,她说,咱们到屋后去。
“我跟她到伙房屋后。
“我碰上毛三了。
“毛三是谁?
“金钟烟厂跑外埠的伙计。
“怎么会这么巧?
“恐怕是林春长派出来的。毛三是驻西安的坐庄客,平汉线沦陷后一直驻西安,在这儿很熟,结交的人很广。
“你大哥,他……
“我大哥这人特别看重名誉,他怕回家没法跟孙家交代。
“毛三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我大哥很生气,说我是受人哄骗被拐了。毛三劝我赶快回去,要不,林春长会找巡警局的人追查。
“我从鼻子里嗤了一下,哄骗你?把你拐了?我把你拐了?亏他想得出!
“你不能怪他,出了这样的事,你让他怎么想?
“是的,是的!一个西南联大高才生,老子又是商会会长,能遮风挡雨当靠山,这么一桩称心如意的婚姻让我给打散了……他不恨我恨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