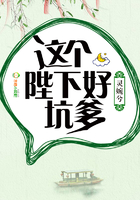[一]
原以为时间是一条长长的直线,贯穿脚下伫立的地方,向前急驰而去。直到很久以后才发觉真相并非如此。
365天4小时58分56秒。地球绕太阳一周。
27天7小时43分11秒。月球绕地球一周。
23小时56分4秒。地球自转一周。
日复一日,从180度经线回到180度经线,循环中划出完满的弧度——
时间是圆形的。
[二]
甬道将至尽头,可能性只剩下一种,应该就是最后那间教室。
开学第一天,四处喧嚣得像口滚着沸水的锅。
教室后门溢出笑闹声,其中一个夏树觉得熟悉。但时间洇成雾气笼罩记忆,最关键的线头匿在其中,理不出。
经过时,向门里匆匆瞥去一眼。
大片白光从对面窗外奔涌过来迷了眼,什么也没看清。
年级组长兼班主任终于停下来,回转身面向夏树:“你在这儿等一下。”
“这儿”的所指,红色的教室门上嵌着金色班牌——
二年(A)班。
夏树乖巧地点点头,倚墙而立。老师推门进去,吵嚷的室内顿时静了不少。女生把书包的部分重量分给墙壁,一边勾着头神游外太空,一边无意识地用脚后跟蹭着墙根。
面前一个人经过,影子在夏树脸上晃了一晃。
近在耳畔的女声喊着“报告”。
教室里传来老师“进来吧”的应答。
等她抬起头看,视野被墙壁切去大半,留在教室外的只剩下对方被气流扬起的发尾。
声音,谈不上甜美,却有种独特魅力,尾音比一般人拖长半拍,又不过分发嗲。
头发,应该很长,浅浅的琥珀色。
那瞬间从门边飘出的气息,非常的,恬淡清新。
从小到大,几乎每个班都有那么一两个班花级的人物,相貌未必是殊色,偏是有种气质,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笑容异常温暖,也足够和悦、开朗,却给人下一秒就会落泪的感觉,说不出好在哪里,却使每个和她相处的人感到舒心。
无论如何,最终这种女生总会成为全班甚至全年级大部分男生的梦中情人。
夏树一心想着刚才喊报告的女生,以至于教室里再次传来老师 “……给大家介绍一位转学来的新同学” 的引荐词时,没能立刻反应过来走进去。
独自在门外发了呆,意外造成“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登场,但并没有什么惊艳效果。
夏树,瘦脸颊,寡薄嘴唇,齐着下颏的短发。
毫无让人眼前一亮的特质。
自我介绍也稀松平常:“我叫夏树。夏天的夏,树木的树。以后将和大家一起学习……”说话和呼吸两件事不好协调。声音重心不稳地悬浮半空上下打颤。
这还不止,话说了一半,突然像录音放送卡了带,下文凭空消失。
结巴了吗?少数人有点好奇地再次看向她。
怪事。
瞳孔里像猛地亮起一盏灯,有种惊讶的辉芒喷薄而出。
静了两秒,连班主任也察觉到夏树自我介绍的戛然而止。
老师诧异地转头看看她,又循着她直愣愣的目光往教室后面望,却被更为动态的东西转移了注意。
也许是空调作用,教室里气流微动,某个座位下无声又缓慢地滚出一只篮球。
中年女老师威严地皱起眉,仍然慢吞吞却厉声地说:“程司,跟你说过多少遍,不要把篮球带进教室。”的确,自从某次大扫除时为了清除墙上的球印不得不大费周章地把墙壁重新粉刷了一遍之后,她就明确制定过这条班规。
不过男生们还总是明知故犯。
名叫程司的男生低头看看从自己脚边滚向过道的篮球,吐了吐舌头,嬉皮笑脸地把篮球拨回座位下。
班主任点点他:“再让我看见就直接没收了。现在你将功补过,帮新同学去物业部搬一套新的课桌椅回来。”但其实语气并没有那么认真,不是责备是嗔怪。
男生仗着老师的溺爱毫无悔悟意思,反倒还搞怪敬个礼:“遵命!”
绚烂的盛夏一点一滴在眼前铺展。
谁的视线落定在谁身上,谁的泪泛在眼眶。
谁的目光失去焦点,谁的微笑和谁重叠。
谁看不见谁灼热的眼神,听不见谁嬉笑的声音,全心全意只在乎你。
珍惜的过去和憧憬的未来,在这个瞬间,这个狭窄的空间,模糊了界线。许多年后,已经长大的你能不能明白,现在的我是以怎样的心情站在这里。
[三]
“真巧哈,没想到你转来和我同班了。”男生下楼的动作幅度大,每跨一步就三四个台阶。等他跳下楼梯转过身,女生还在半层楼以上,于是他仰头说。
对方主动搭讪,让夏树从深思中回过神。
“是呢。没想到。”
说完才反应过来。哦,竟然又碰见了这个人。无端地高兴了。
少女情怀是什么样?顾不得利弊得失,像一大群鸟儿扑腾翅膀齐声啾鸣,刹那间沸反盈天。
伫立于楼下的男生,日光把那张年轻朝气的脸寸寸打亮。周围教学楼散发着涂料新鲜气息的白色外墙将他卷进云淡风轻的纯净世界里。
视界里草坪的碧色、花的绯色、砖面的浅灰色、学校标志物的金色,他在其中。
无色的风把他的制服衬衫灌满。
心脏突然有了重量,陡然下沉,明明满眼都是明媚景象,却没来由地鼻子发酸。原本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校园终于在此刻让人有点想亲近想融入。
相隔仅仅四天的再遇见,稍微折损了巧合的魅力。
夏树刚到上海的那一天。虽然是炎热的夏季,但因为厚重的云层低低地罩在头顶,太阳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
清晨是湿冷湿冷的。
夏树慢吞吞地拖着大包小包从火车上爬下来,行动迟缓,终于阻塞了交通。
站在门口的列车员眉头微蹙,嘴里用上海话嘟嘟囔囔:“乡下人怎么这么多,烦也烦死了。”尽管明知被鄙视的人听不懂,依然底气不足声音小到无法辨别。
却还是像一把小刀插进了女生的耳廓。
偏偏,什么都听得懂。
女生头一低,耳根潮红,赌气似的猛一用劲,最大的一个箱子突然脱了手。
“啊!”幸好手在关键时刻扯住了身后的铁质扶手,人才没有失去重心一起跌下去。定下神抬起头,箱子已经擦过前面刚下车的那位乘客的脊背重重地摔在地上,晃了两下,终于躺着安分了。
女生微怔。等彻底回过神来,忍无可忍的列车员已经三下五除二帮她把所有行李拽下了车,躺在面前一小块水泥空地上的笨重大箱子,也被旁边突然伸来的一只手帮忙竖了起来。
是差点被砸到的那位乘客。
“对不起对不起……谢谢谢谢……”女生语无伦次地跳到前面去。终于交通顺畅,列车员松了口气。
“你——有人接吗?”好听的、年轻男生的声音。
诧异地抬头。
刚想说什么,就听见奶奶越来越近的“阿树、阿树”的叫声。慌忙中去拖箱子,却发现对方的手还一直搭在箱子上。
视线从指尖沿手背上凛冽的骨架蜿蜒,落定在手腕处一圈别致的木质手环上。
“哈!带了这么多东西呵!奶奶来拎。”又颤颤巍巍伸出一只苍老的手,使先前搭在箱子上犹豫着的那两只茫然地悬在了半空。
“还需要帮忙么?”
是问她的,女生回过神,慌忙回答:“哦,不用不用。”
女生清晰地听见那句“那么,再见了”,迟疑了两秒才抬头,却发现对方已经混入漫涌的人潮中,再也辨别不出。她只能定定地望着左手方向,尽最大努力从远远近近的灰黑色块中企图层析出与众不同的亮彩。
“认识吗?”奶奶的目光也被牵去了与孙女相同的方向。
“欸?”惊醒后回头,女士迷茫地把目光从漫无边际的远收向咫尺之内的近。
“和那个孩子认识吗?”
“哦。不认识呢!是同车的乘客,帮忙扶了扶箱子。”记得当时是这么定义的。
发生在十七岁夏天的最初相遇。
原以为只是与十三亿分之一的人碰巧擦肩而过,转身就会相忘于人海。却没想到日后的交集会像盛夏的爬山虎一般肆意蔓延开来,成为维系,成为羁绊。
平淡无奇的同车经历,因为之后又遇见谁而变得不同寻常。
夏树的生活从来不缺少奇迹。
幸福的,不幸的,都是无力抗争的奇迹。
悠扬的下课铃回荡在校园上空。应该是早自修结束了。当一声大喊劈头盖脸而下,出神的夏树结结实实地被吓了一大跳。
“阿司,帮我和小静去快客超市带两根绿豆冰!”
阿司是谁?小静又是谁?夏树有点发怵地抬起头,阔脸的女生形象倒是和之前的惊人嗓门相匹配。
这时,临窗又有几个学生探出身来追加点单:“我也要!”
同行的男生停住脚步朝上喊道:“到底几根?你们统计清楚嘛!”
隔了一会儿,阔脸女生报出准确数字:“12根!钱等下上来再给你。”
“知道了!”男生说着继续往前走,在注意到夏树愣在身后时立刻又停下。
夏树跟上来:“你叫阿司?”
“程司,方程的程,司是同学的同去掉第一笔那个‘司’。”
“同学……那不就是司机的司么?”有谁会绕那么大一个弯扯上同学的同啊?
男生好像想到什么,兀自笑出声,朝夏树猛摆手:“那个啊,因为被人反问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斯基么’,所以后来我就彻底放弃本身会引起歧义的词了。”
“立刻就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本身也是怪胎吧?”夏树是这么认为的。
“嗳……反正,平时大家都叫我‘阿司’。”
“阿司!”立刻就付诸实行。
程司有点意外地侧头看她。
女生弯起了眼睛,淡淡地说:“开玩笑呢。”
“真叫也没问题啊。”
可是,还不太熟吧……
虽然夏树只有一个人,但圣华中学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的课桌,只有两人同桌的长条课桌。
料想程司一个人搬张桌子就够吃力,夏树才会跟来自己搬椅子,但眼下女生却只需拎着帮同学带的一塑料袋棒冰。
程司不费吹灰之力就随便抓了个别班的男生帮忙搬椅子。
人缘挺好。
夏树在心里暗下定义。
……那么,就慢慢了解下去,直到熟悉。
[四]
课桌直接被摆在最后一排,与程司隔着两个座位。
因为没有同桌,所以离得最近的是相隔一条过道的那位男生。上课总在睡觉,对自己爱理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