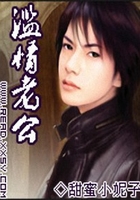说时迟,那时快,安迪在危急之中侧身一让,那人的匕首斜斜地落下,在他手臂之上划下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如泉水般涌出,顷刻之间染红了一条手臂。
梅飞飞“啊”的一声惊呼,却见安迪只是闷哼一声,一转身,用没有受伤的手,一拳打落了匕首。
这时,后面的保安已经挥着电棍追过来。三个小混混以三敌一,却明显还是处了下风,何况已有人来,这时赶紧连滚带爬地跑了。大雨之中路滑,有一人还摔了个狗啃泥,艰难地爬起来继续跑。另两人也不管他,一眨眼跑了个不知所踪。
梅飞飞扶住安迪,只见他脸色雪白,一条手臂全被鲜血染尽,也不知究竟伤得如何,一时急得说不出话。
倒是安迪关切地看了她一眼,问道:“你没事吧?”
梅飞飞摇摇头,不知说什么好。
保安走过来看了一眼,大声道:“赶紧上医院吧!”
医院急诊科。
安迪躺在车床上,衣袖已经剪开,伤口经过初步清洗,已经清楚地显露出来。从上臂直至前臂,约有三十公分的一道伤口,张牙舞爪地狰狞着。
现在正等进一步清创缝合,梅飞飞在一旁焦急地守着。
安迪失血过多的脸色十分苍白,却仍然对她微笑道:“别紧张,就是皮外伤而已。没事的。”
梅飞飞叹了口气,问道:“你,怎么会在那里?”
安迪一笑:“傻瓜,你周六时总喜欢去那儿闲坐。以前是有我陪着,如今你孤身一人,还弄得这么晚才回来,叫人怎么放心?”
梅飞飞听了半晌无语。她原本不想再与他有任何一点干系,却想不到他仍然这样执着。可是,他这些作为,现在又该让她如何面对?
“你别往心里去,我所作的这一切,只是我自己想做的,无论你接受与否,与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还是一如从前,一眼就看透她的想法。
只是,他这样说,只能令她更加为难。今后,只怕再无法对他视若无睹了吧!
医生过来道:“可以进行缝合手术了,病人要进手术室去。”
梅飞飞点点头,怔怔地看着他被推进去。
“飞飞!”好久没听他这样喊她的名,她看着他在手术室门口示意医生停下,然后抬起头来对她说,“快去把湿衣服换了,会着凉的!”不等她反应,说完这话就进去了。
梅飞飞愣了半天,才知道“哦”了一声。
梅飞飞一直等到手术结束。
安迪被推出来的时候,脸色更显苍白,连口唇也血色尽失。他静静地躺在车床上,梅飞飞以为他睡着了。不料,他忽然微微睁开眼,见她临时换了一套干爽的病号服,唇边露出一个极浅的笑意,又疲倦地闭上眼。
梅飞飞看着他被推进病房,立即转头问医生:“他怎么样?”
医生看了她一眼,反问道:“你是他什么人?家属吗?”
“呃,是朋友。”
医生点点头:“伤口比较大,但没有伤到骨头,只是……”
“怎么?”梅飞飞有点紧张。
“尺神经被划伤了。”
“尺神经?这个,要紧吗?”
“怎么说呢。”医生皱了皱眉,“神经的修复不同于骨骼和肌肉,所需的时间会比较长。在完全修复之前,可能会有一定的功能上的影响。”
“什么影响?”
“例如说,手指使不上劲。”
“那,要需要多久才能恢复?能完全恢复吗?”
“以他目前的状况来看,大概需要半年左右才能恢复。至于能不能完全恢复。”医生歉意一笑,“这个我可没法给你百分百的保证。”
梅飞飞怔住:“万一恢复不了,那他这手……”
“啊,这个你可以放心!”医生又道,“所幸只是划伤,并未完全断裂,完全恢复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即使不能百分之百恢复,但日常的生理功能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的。”
“日常的生理功能……那么,能弹钢琴吗?”
“钢琴?”医生愣了愣,随即歉意一笑,“只怕不能。”
一种极为歉疚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使她半晌不能言语。医生见她没有什么再问,告了个歉便走开了。
愣了一会儿,她轻轻推开病房门进去。安迪手臂上缠着厚厚的纱布,此时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梅飞飞百般不是滋味地在他床边坐下。
不过几个月时间,换成了他躺在病床上。一只手换一只脚,这是天意么?
“飞飞,飞飞……”有人轻轻地摇她肩膀,同时小声喊她名字。
梅飞飞茫然睁眼,入目是一片雪白,眨眨眼,这才想起自己是在医院,而自己是趴在病床上睡着了。立刻抬头看向病床上的人,只见安迪仍在熟睡,脸色好看了些,右手臂的纱布也未见渗血,于是放下了心,这才看向喊醒她的人。原来是江玉容,身边还站着钟灿华。
江玉容见她醒了,正要开口说话,梅急忙在嘴边竖起食指,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即起身,拉着他俩出了病房。
“他怎么样?”江玉容一出门便急急地问。今天一大早就接到梅打回来的电话,她只能匆匆和班长打了个招呼就跑来了。钟灿华一向和安迪相熟,所以梅飞飞也通知了他。
梅飞飞看了一眼病房,叹息道:“伤了手臂,已经做了缝合手术,不过昨晚发了一夜高烧,这会儿应该没事了。”
江玉容和钟灿华同时吁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