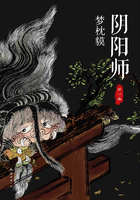别看莫眉见过许许多多的狗,但是这种价值五十万美金一只的名贵狗,她还是第一次见到。流浪狗大多数是常见品种,一说养狗要申请狗牌,也就是要花一笔钱,许多丑陋的中国人就把自己的宠物赶到了大街上,跨区域地乱丢。歌星、影星的狗也不过是大丹、牧羊犬、白熊、吉娃娃之类,这么稀有的藏獒,她也只看过图片。
她忍不住俯下身去,并不敢触及那条狗的一丝一毫,“这狗叫什么名字?”
“来福。”牵狗的人是一个举止儒雅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他却一直在注视着莫眉。
他对剧虎说道:“来福不太吃东西……这是我儿子的心肝宝贝,他出差了,让我临时照看,搞得我压力很大。”
剧虎把来福带到检查室去了。
陌生人突然对莫眉说道:“你是莫眉女士吧?”
莫眉感到相当诧异,这才算是认真地打量了陌生人一眼,他中等身材,体形偏瘦,戴一副无边眼镜,头发虽然灰白,但仍相当浓厚,是那种学养和风度同时兼备的男人。
“我看过你演的一个日本话剧,《 她的一生 》,我看了三遍。”
“那个戏就只演了三场,因为没有什么人要看。”
“你演得很好,太令人难忘了。”
“谢谢,你是……”
“我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主要是翻译日本文学,我关注的日本作家也不畅销。”他自嘲地笑笑。
看到他灰白的头发,莫眉真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悲从中来,可是不是这把年纪的人,有谁还会认出她来呢?莫眉不觉叹道:“我早就不演戏了,在爱心驿站工作。”
陌生人也递给她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彭树。
杜党生也是一个单身母亲,当初她跟彭树结婚,可以说是一个误会。
那时候,彭树还在某大学任教,杜党生作为工宣队的一员,认识了彭树,对他的印象还不错,并没有其他什么杂念。当时彭树有一个对象,是搞英美文学的,两个人看上去十分般配。
不久,杜党生就撤离了学校。几年之后,党又号召: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要注意帮助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有人觉得杜党生也老大不小了,便给她张罗着介绍对象,并说,反正你出身好,找个成分高的也没啥,关键是那个人挺不错的。仔细一打听,原来就是彭树。
杜党生说,他不是有对象吗?介绍人说,他跟他那个对象出身都不怎么样,一个是城市贫民,一个是小业主,全都没有什么革命性。那个小业主出身的女的,后来找了一个祖祖辈辈都是贫农的军官,两个月之内就结婚了。彭树受了刺激,也要找个出身好的。他听说杜师傅不仅是贫农出身,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那她不仅是党的女儿,而且是党的化身,表示愿意在杜师傅的帮助下,更快地进步。
既然人家这么需要自己,杜党生也就被感动了。
并不是性格爱好完全相左的人就没法生活在一起,至少在色彩单调的年代,这样一个家庭,可以说是彭树的寂静港湾。儿子女儿相继出世了,有时候彭树也很怀疑,假如他跟小业主的女儿结了婚,暂短的甜蜜之后会是什么局面?有可能是没完没了的学习和改造,被人轻视,永远得不到重用和赏识,或者干脆一块发配到偏远的农村参加劳动或当民办教师,渐渐地被人们遗忘。
这样的铁例不是没有。
日子像书一样翻了过去,到了改革开放的这些年,他们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
彭树对官场上的事没有兴趣,但他觉得杜党生却乐此不疲,她喜欢抓权,而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身上不仅有了官气,还有了几分霸气,就是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情。凝思的时候眼睛会像雄鹰一样阴冷而深邃。她盯上谁,那人的下场就好不了。
其实,彭家的卓童和卓晴,如果身上还有那么几分人见人爱的潇洒和文艺,也都是源自彭树的遗传。这两个孩子深知母亲的能干,却都喜欢亲近父亲。因为母亲在家也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女干部,而父亲却和他们玩闹在一起,父亲是个有趣的人,包括他严肃的时候,也是亲切可感的。即便是他在译稿子,一手执笔,另一只手仍可抱着卓童,年幼的卓童骑坐在他的腿上,用毛笔在他一本正经的脸上乱抹乱画。总之,对孩子而言,他们家是严母慈父。
有时,彭树偶得佳句,翻译出洗练并且几近透明的文字,他会忍不住声情并茂地读给杜党生听:……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默默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
杜党生说,完了?彭树说,完了。
杜党生毫无感觉地说,全世界怎么可能同时下雨呢?!
有人曾对彭树说,你老婆是官场上的天才加奇兵。彭树真是不谙此道,他说,有那么神吗?!
他们是彼此对牛弹琴。
然而,无论有多少不和谐的生活琐事,也不足以让一对夫妻离异。问题还是出在小业主的女儿身上,当初,她放弃了专业,一心一意地照顾老公的生活,本以为她的军官丈夫还可以步步高升,自己这辈子也就做个专职官太太算了。虽然一事无成,但求风平浪静。
但是军队上的事也不好说,她的行伍出身的丈夫不仅原地踏步了这么多年,而且还过早地得了脑溢血偏瘫,她等于一直在做他的保健护士,一边换着小保姆一边支撑着这个家。
有一天她去新华书店给孩子买参考书,无意之中发现了彭树新出的翻译作品,当时她的眼泪哗的一下就出来了,真是百感交集。在这之前,她一直以为自己已经把彭树忘记了,其实有些事情是终其一生都无法忘怀的。她通过出版社得到了彭树的电话,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有一种倾诉的冲动。她活得实在是太压抑了,她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
照理说她应该被生活折磨得苍老、憔悴,皱纹一抓一大把。可是她毕竟还是养尊处优的,或许是善于保养吧,她看上去比同龄人还是年轻,身材也保持得不错。她给彭树打电话,彭树当然也很想见她,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两个人约在咖啡厅见面,在古典音乐的旋律中又回到了从前。本来,彭树觉得自己生活得还不错,不妨与前任女友作一番畅谈。但是前任女友一伤心流泪,他好像也感到自己生活得并不如意,内心中深深的寂寞无法抑制地涌现出来。
本来这种见面,久久的来一次也是平淡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大家都是过来人,都不可能改变什么,也没有必要作什么改变。老实说,再见面也已经没有爱了,至少彭树想不通自己当年怎么会这么如痴如狂,还用婚姻来赌气。
可是女人控制自我的能力天生就差。小业主的女儿太依赖这种见面了,而且她觉得也只有彭树知道她,了解她,说出来的话让她入心入肺。她频繁地要求见面,这就很让彭树为难。
彭树深知,杜党生的世界里是没有中间色的,这种事让她知道,是黄泥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可他是个相当自尊的人,不愿意让前任女友认为他怕老婆,也不会大吐苦水说杜党生的坏话,因为从头至尾杜党生也不是一个坏人,她有相当优秀、果敢、重情的一面,何况他也是沾了人家光的。总之,彭树开始推搪前任女友,尽可能地减少见面。
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中午,前任女友突然跑到彭树家里来了,起因好像是她老公久病之后心情暴躁,把整个饭盆子扔到她脸上了。过去也只是骂骂咧咧,发火生气是家常便饭,现在愈演愈烈,简直叫人无法容忍。见到彭树,她特别悲愤地哭诉,突然,她一把抱住彭树,带着哭腔说,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她还没来得及说下去,门就被推开了,杜党生回家拿一份材料,恰恰撞上了这一幕,简直惊呆了。这两个人的事,杜党生当工宣队副队长的时候就知道,现在他们哭得梨花带雨,如果不是续上了情缘怎么可能这样?!
杜党生是搞阶级斗争出身的,什么事情也不会轻描淡写。女方走了以后,她对彭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明知是徒劳,彭树还是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
从此,平静的生活变得暗流涌动。杜党生是什么人?!她的眼里是不容沙子的,而且她也决不会去找另一个女人算账或彻夜长谈。生活中有这样的事,最后以理解万岁告终,三个当事人还成了好朋友。真他妈的荒唐,这根本不是杜党生的风格。
无论如何,杜党生没法平息心中的怒火,但又不知该不该提出分手。她的顾虑是,如果彭树同意分手,说明这件事是真的,分手反而成全了彭树,对于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她怎么能顺这口气?!如果彭树坚持不离,她又觉得他是格外看重她现在的身份和地位,却又在家庭之外搞情感走私。这就更让她无法容忍。所以表面上,杜党生似乎是再也不提这件事了,但她经常会在上班时间突然回家。当然她很忙,这种举动就由捞仔或她的秘书代替,开始还找点借口,拿外衣、文件什么的,后来干脆进屋后就东张西望,还看看门后和洗手间。这种举动终于把彭树给激火了。
有一天,在捞仔离开的时候,彭树板着面孔紧随其后,并上了他的车。捞仔犹豫了一下,刚要开口,彭树对他大喝一声:开车!
彭树像一只发疯的狮子闯进杜党生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对她说: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们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