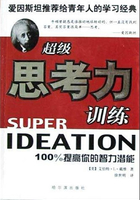爸去得早,和妈相依为命的这段臼子,仿佛燕子失巢,风雨总来得格外急躁。自小我便看惯了妈妈的操劳,从不曾向她要过额外的花费。可是,这次是不同的,因为朱樱。
可是该怎么向妈开口呢?最近这几年,妈的厂子效益一直不好,我还记得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为了筹措学费,妈的鬓边急速地漫上了星星白发。
滚烫的汤哽咽在我喉间,我反复思量着,室内满满的全是我喝汤的声音。
妈坐在对面,静静看我,忽然说:“前两天,厂里开了会,说一批人要下岗。”
我猛抬头,嘴里的排骨“当”的一声直坠进碗里,油汤四溅,我恍若未觉,失声道: “妈,你下岗了?”我霍然站起,惊恐地盯着妈的脸。
妈一愣,然后笑了,笑容里是无限的疼惜与爱怜:“看你吓的,我说一批人要下岗,又不是说我,妈干得好好的呢!”她端过我的碗,“我再给你盛一碗汤来。”她瘦削的手背上青筋略略暴起。
我至此才松了一口气。咬咬嘴唇一口气说出来:“妈,下学期要实习,学校要交200元材料费。”
妈“啊”了一声,有明显的失望意味:“又要交钱……”
我不敢看妈的眼睛,“要不然,我跟老师说……”妈已经转过身,拉开了抽屉:“我给你两张一百的,路上好拿。”
妈找了半天,也只找出一张一百的,一张五十的,其余都是十元的。她把每一张钱的纸角都压平,仔细地数了好几遍,才关上抽屉,把钱理好,折了四折,叠成了一个四方块给我。
我心中狂喜,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接过来漫不经心地往裤兜里一塞。
妈瞪我一眼:“你这孩子,钱怎么能这么放。”又给我拿出来,小心地塞进我书包的夹层里,把双层拉链拉好,送我出门的时候还反复叮咛:“车上小心,现在小偷多。”
我“嗯嗯”地答应着,却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飞奔着越跑越急,想立刻飞到朱樱的身旁。
圣诞节的黄昏,下了雪。麦当劳里人山人海。我们等了好久,才有一桌人起身,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抢到座位。朱樱伸手招呼:“小姐,清一下台子。”
一个女服务员疾步走过来,远远地,只见她单薄的身影,走路时上身稍稍地前倾,竟是十分熟悉。她走到我们面前,我在顷刻间呆住了:妈!
然而,妈啥也没说,只是低下头去,利索地开始收拾桌上的残杯剩盘。
我想喊她妈,可也许是因为震惊,也许是因为周围喧嚣的人流,也许只是因为朱樱,我竟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是愣愣地看着她。
妈再没看我一眼,径直到邻台清理。双手各擎着一叠托盘,穿行在人群里,不时给衣着鲜丽、喜气洋洋的人们让路。把废物倒进垃圾桶时,她停一停,伸手擦一擦额头,当她再一次从我身边走过时,在她的手臂上,那烙痕一样清晰的,分明是一道泪痕……
妈消失在人群里,我的眼前渐渐模糊,任我怎样寻觅,都无法从那么多相似的红条衬衣里辨识出她的身影。而在整个麦当劳的店堂里,竟有那么多中年妇女在清理、擦地,我一张张读着那红帽红衣下沧桑的脸孔:她们是不是也都是母亲?也都有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那个周末的晚上,妈是不是本来准备告诉我她下岗的消息?是什么让她改了口,是不忍心看到我那一刻的紧张与焦灼吗?于是她决定将一切的痛苦咬碎了吞下,然后独自去面对生命中所有不能回避的关口。
我紧紧地握住袋中的纸币,第一次知道了钱的分量。不过薄薄的几张纸币,柜台小姐唱歌似得报出数目,就可以轻易地交付。然而妈要清多少张台子才能赚来?临睡前一盆泡脚的热水便可以平复她周身的酸痛吗?然而,又要做什么,才能拭去那一抹烙在妈手臂上的长长的泪痕?
我会永远记得,有一个晚上,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互相欺骗:母亲是为了给儿子一片无忧的天空,让儿子可以自如地成长;而儿子只是为了得到一夕狂欢,却成了母亲心上最痛的一刀。
在成长中,我记得的事,像旋风一样涌上来又翻下去,我竟不能止住自己的泪。泪光里我看见朱樱,她文静的眉眼、精美的黑皮衣衬出她的玲珑腰身,忽然知道:对于我来说,爱情是太奢侈的游戏……
大二的时候,我把一叠钱放在妈妈的面前,说:“有我的奖学金,也有我当家教、打工的钱,妈,下个学期的学费我自己付,你以后不要那么辛苦了。”
妈妈久久地看着那些钱,双手突然蒙住了脸。她,哭了。
人生感悟
我们的成长见证了母亲青春的流逝,母亲的光阴犹如渐短的影子映衬着我们的未来。如同这个故事演绎的一般,我们在拥抱辉煌,母亲却在积累沧桑。也许我们已经忽略了一年中的364天,那么请在今天,向母亲表达自己的感激和敬仰。
母亲的眼泪
文/谢琴琴
我走着,这条田埂小路,像母亲龟裂的双手;这条清澈小溪,像母亲慈爱的双眼;这条拱形小桥,像母亲沉重的脊背。
我驻足了,我为何还要去为难我的母亲?抬头仰望着天空,它还是那么深邃而又神秘。而天空中的那片晚霞已跃入我的眼帘,橘红色的晚霞像一片片熊熊燃烧着的火焰。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同它一样美丽的梦想。
向往着我美丽的梦想,在通往偏僻贫瘠的小山村的那条坑洼不平的小路上,我徘徊了三个下午,最终还是迈着沉沉的脚步向前走了……
回到家,门同往常一样紧关着。我径直走向山顶那几方充满希望的田地,因为在那里,我总能找到母亲的身影。母亲正在种豆。
“妈。”
“琴儿,你回来了呀!又是要报考费吧!”母亲的脸色暗了下来。
我点了点头。我不想抬头,怕看见母亲无奈的神色。简短的对话后,我和母亲都陷入了沉默。田地里只有锄头啃着硬泥块的声音,母亲的汗滴不时地坠落,亲吻着干瘪的田地。
母亲打破了沉默。“琴儿,这事本不该告诉你,怕影响你学习。你奶奶前天因心脏病发作进了医院,昨天你爸爸在外婆家借了一大笔钱给奶奶治病,你那几位叔叔手头也紧……为了供你们三姐妹读书,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了。这钱别的同学都交了吗?能不能再拖一拖……”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对母亲的伤害才最小,于是一声不吭地站在田头。
母亲看着痴痴站立的我,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她放下锄头走向正在田里劳作的几位村邻。我在远处,只看见他们一个个都摇头。
母亲走了过来,额上一条条被无情岁月刻下的皱纹显得更深了,似乎充满着无限悲伤与无奈。母亲望着那被群山环绕的小村庄,自言自语地说:“哪家不巴望崽女有出息,有这心没这力啊!”
母亲拿起了锄头,锄了几下。忽然她转过身来,拉住我的手,一颗豆大的泪珠滴落在我的手心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含辛茹苦的母亲把她这几十年深埋在内心的愁与苦谱写在脸颊上;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泪顺着她饱经风霜的面孔淌下;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如冰一样冷的母亲的泪流进我的心田。我的心碎了,是的,我该让我的梦离我远去,我不能再如此折磨我的母亲了。
我毅然走近母亲,说:“妈,我不想念书了,我想出去打工,我再也不能增加您的负担了。”
妈一听我的话,猛然一愣,快速地用手拭去残留的眼泪,定了定神,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别犯傻了,瞧你没出息的,妈啥时候退缩过?妈虽没文化,但也知道‘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的理,没有趟不过的河,没有迈不过的坎,妈会想办法的,千万莫打‘退堂鼓’,用心读书……”
最后,母亲串了很多门,才从一位回娘家探亲的人那里借到了钱。在母亲的目送下我又踏上了那条回校的小路。一路上,母亲的殷切话语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母亲的坚忍、宽厚,让我为自己的懦弱、退缩感到羞愧,母亲那质朴的言语中透露出的对生活的勇气与信心,给我以强烈的震撼。是啊!我有什么理由在困难面前望而却步呢?
看着路边小溪里的水,我似乎看见了母亲。母亲就像那溪流,不知穿越了多少山,多少峰,多少谷才走了出来。而此刻在她中央有一块石头使溪水飞溅到了空中,接着又一颗颗珍珠般地洒落下来,这大概是母亲的泪珠吧,而我就是这块让母亲流泪的顽石。我这块顽石不仅得到了母亲的呵护,更得到了母亲的洗礼。我相信自己会变得坚强、勇敢起来,努力去拼搏,执著追求我那如雨后彩虹般美丽的梦想。我坚信,终有一天,母亲的眼泪将不再是酸楚的,而会化为幸福的泉流!
人生感悟
母亲总是令人骄傲的,她不仅给了我们无尽的呵护与关爱,还用她在苦难面前永不低头、永不退缩的人格魅力,给了我们精神上的洗礼,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母亲用她的眼泪和汗水,浇开了我们如雨后彩虹般绚烂的梦想之花。
最温暖的母爱
文/张了格
去年的深秋,我和朋友一起沿着川藏线进入藏区,奔赴四川阿坝自治州的小金县,我们这次要攀登的是那座耸立在高原之上的四姑娘山。
我们坐飞机来到成都,然后搭上小金县的班车前往日隆镇。这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程,汽车需要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盘旋一天的时间,越过那海拔4500多米的巴朗山脉,那里空气稀薄,冰雪覆盖,恶劣的高原环境等待着我们一车人。
汽车驶入巴朗山脉的时候,就开始有乘客感觉身体不适了,因为公路总是弯弯转转,搅翻了大家的胃,有人开始呕吐了。特别是我身旁坐着的那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她身体似乎难受得厉害,以至于司机不得不停下车来让她休息一下。她却强忍着难受,请司机继续前行。于是,我们的汽车就继续前进了。
汽车驶到巴朗山山腰的时候,老人已经呼吸急促,头昏眼花了,我知道这是高原反应,于是立即掏出红景天给她喝了一小瓶,她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声谢谢,似乎已经连大声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汽车继续前行,慢慢地向山顶进发,老人的呼吸越发急促起来,高原反应越来越重,我们不得不请司机停下车来。司机这次走过来一看她,就马上紧张地问道: “您有哮喘病?”
老人点着头,已经不能说话了,司机慌忙拿来小液体氧气罐给她吸氧,她吸着氧气才慢慢平静下来。但是我们的路途还很遥远,山还很高,于是我们开始趁老人清醒的时候,劝她下车搭便车回去。因为一旦进入偏僻的藏区,如果身体过于不适,那将是很危险的事情。
但是老人强装微笑地说,没关系,翻过这座山,我一定能挺过去的老人就这样昏睡着,与我们一道穿过了巴朗山,终于来到了日隆。
到达日隆的时候,前来接待的小旅店老板拥了上来,请我们去住他们的家庭旅馆。当一位藏民妇人一看到老人时,居然惊叫起来,对她说,陈阿妈,你今年怎么又来了!
那位老太太疲惫的脸上浮起微笑,说,我来给儿子送件棉衣!我猛然惊诧,原来她的儿子在藏区啊,我们松了一口气,心里踏实了许多。
而那位藏民妇人见到她,像是接到亲人一样,也不再招呼别的客人了,而是搀着老人回去了。
我们选择了另一家家庭旅馆住下,准备明天的登山行动,我们这次准备征服四姑娘山中的幺姑娘山,那是一座我们一直渴望征服的大雪第二天清晨,我们就背着装备骑着马向雪山进发了。我们将穿越原始丛林,顺着沟子,经过海子,踏过小草原。我们期待着看到雪山底下一片片新落的白雪……
但是当我们来到雪山底下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和一位牵马的妇人早已经来到山脚下了。
老人见到我们来了,脸上忽然浮起了笑容,她远远地问:是你们啊,你们是登山去吗?我回答说,是啊!我们要登山……
老人的眼角激动得渗出泪花,说,太好了,那请你帮我一个忙,你们给我儿子捎件棉衣好吗?
说着,老人从袋子里抽出一件厚实的棉衣来,递给我。我早已经目瞪口呆了,我完全没有明白过来——因为这雪山之上不可能还有别人在,看上去也不可能有人比我们早。
这时,那位藏民妇人拉着我来到一边,说,小伙子,你也帮忙劝劝这位陈阿妈……她的儿子4年前在这里登山遇难了,可是她忘不了自己的儿子,每年都从北京来这里送棉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