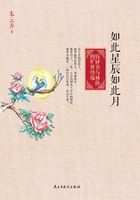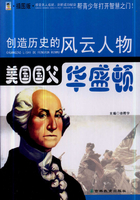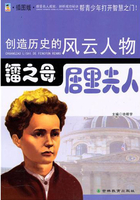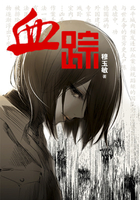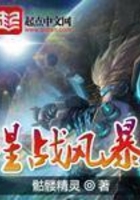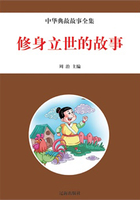从明港回北京的火车上,7连2排的负责人找吴敬琏谈话,宣布他还在“被审查”,只能待在学部大院里,不得回家。整个学部有69个没有解放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正是其中之一。
这时候,与丈夫分别了近3年的周南表现出了她的勇敢。她找到七连的军宣队政委,问:“吴敬琏到底有什么问题,他是‘反革命’吗?如果他是,我可以跟他划清界限,但是你们得拿出证据,如果不是,家里有两个孩子,还要搬家,请你们让他回家。”政委无言以对。第二天,吴敬琏宣布“自我解放”,径自回家去了。军宣队的领导很气愤,在学部的会议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过,政治环境毕竟已经大变,倒也没有人真的去把吴敬琏抓回来。
尽管回到了北京,经济所的正常工作并没有恢复,仍是一地鸡毛。吴敬琏又回到对社会历史的钻研中去,为了补习英语,他开始读英文版《罗马帝国衰亡史》,10卷本,每本500页,每天读50页,雷打不动。
可怜的顾准无家可归,他的子女都与他划清了界限,约定“生不再见,死不相别”。更可悲的是,他的母亲已年过九旬,十余年未见,虽然现在身处同城,近在咫尺,却也还是不得见面。他只能住在学部大院的一个斗室中,每天清晨,背着一只军用书包,内揣两个冷馒头,去北京图书馆读书,黄昏归来,点一盏孤灯继续夜战。他常常剧烈地咳嗽,痰中带血,却也并不在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希腊城邦制度》一书的写作之中。这是一个为抽屉而写的伟大作品,顾准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动力来自于天地间一个冥冥的召唤。他以数十万言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按吴敬琏的看法,晚年顾准在思考“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天问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会经由某一路径转化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
在近当代世界政治史上,这一路径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顾准看来,革命是对现状的破坏,它不可能获得经验性支持,只能通过对未来至善的想象、对乌托邦的渴望进行社会动员,争取群众参加,所以,革命理想主义者“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而对于群众来说,“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这当然是极具感召力的。“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的作用,却是科学的”。在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十月革命中,“终极目的”都是革命动员的强大依据。
然而接下来,顾准发现,作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终极目的”的设定是危险的。因为——“终极目的”是一元的,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承担着“建立天国”的重任,把“终极目的”当做当前最高目的,并为此而拒绝、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把一切中间环节和近期目标都当做手段,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所谓“异端邪说”,肆意破坏日常生活,践踏公民权利,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并不是100%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谁掌握“终极目的”并无客观标准,只能以权力大小来判断,极易导向领袖迷信、个人崇拜,把一个具体的人塑造成领会历史秘密、体现总体意志的神。由这样的逻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终极目的”必然经过手段向目的转化,它被构想出来是为了动员革命、引领群众,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元排他性,在运用的过程中它衍变为真正的目的,革命者走向偏执。
在经历了多年孤独而痛苦的钻研和思考后,顾准坚定地写下了这段文字:“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
日后的研究者们认为,就是在这种充满了辩证、理性的冷峻思考中,顾准终结了所谓的“终极目的”,从而解放出三个原则。首先是科学精神,主旨是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无止境,“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其次,科学精神是多元论的另一种说法,否定了绝对真理,否认有什么“第一因”、“终极目的”,尊重各种思想都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是人类认识的某一方面,从唯物论到唯心论,从经验主义到理想主义,都对改变人类状况有过贡献,但都不是至高的、终极的,它们的命运取决于它们各自在相互交锋和斗争中的结果。第三是政治民主,哲学上的一元论对应与政治上的独断主义、权威主义;多元论对应于民主和自由,它让每个人都有表达意愿的权利。“民主是与不断进步联系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的。”
顾准的这些思考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但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性反思,更是对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的终结性控诉,即便在多年之后,它仍然散发出逼人的光芒。历史学家朱学勤因而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在1949年之后已经渐渐销声匿迹,并且名声扫地。但顾准凭一己之力再次扛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为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挤’出了一道门缝”。这位早年信奉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在历经劫波之后脱胎换骨,回归为一个理性、信奉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者,在一个接一个的昏暗难眠的夜晚,他将毕生的追求和坎坷铸成了一个个带血的文字。顾准不知道的是,几乎就在他埋头工作的同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正在写他批判苏联模式的巨著《短缺经济学》(1980年),而写出过《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正因他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成为西方声名最隆的经济学家,在全球思想界,对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改革已经拉开帷幕。
每隔一两周吴敬琏与顾准见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与见闻,他们的小圈子也悄悄地在扩大,赵人伟、周叔莲和张曙光等都加入了进来。吴敬琏对西方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已拓进到中世纪和近代阶段,古今对照,他越来越感觉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他在口述史中说:“在息县和明港,我们的讨论还比较粗略,主要是关于希腊和罗马制度,以及儒法之争等等,那么回到北京后就现实多了,我们发现,世界近现代社会主要有两大思潮,一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改良主义道路;一是革命专政式的直接民主,后者很容易形成为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到这里,中国问题的解答也就呼之欲出了。可惜后来顾准死了,而我则继续往前走。”
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机会接触到欧美经济学的新发展动向,这要感谢经济所图书馆的馆长宗井滔——一直到30多年后做口述史时,吴敬琏仍能一口报出他的名字。“文革”期间,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同业“鸡犬不相闻”,完全断绝了来往,倒是这个宗管理员,每年用上级分配给他的一点外汇,订阅了国外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譬如《美国经济评论》等等,这好比在铁墙上意外地凿出了一个不起眼儿的小洞洞。20世纪70年代初期,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经济异常波动,学术思想也变化激烈,经济所内一些敏锐的学者从刊物上已经察觉到了这一景象。
据吴敬琏回忆,当时对这一情况最为敏感的是当过副所长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巫宝三,“在当时,凯恩斯主义正受到二战以来最严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遇到了第二次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崭露头角,对这一切,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巫宝三好像是知道的”。巫宝三经常向顾准推荐一些新的书籍和文章,顾就组织吴敬琏、赵人伟等人翻译,其中,吴翻译了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顾则翻译了《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罗宾逊夫人是左翼凯恩斯主义学者,时称“新剑桥学派”,她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以及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一大学派,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来说,她的思想似乎更加容易接受。日后视之,顾准等人的翻译工作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向“反动”的西方经济学招手。
到1974年的秋天,在落叶萧条之中,顾准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在过去的两年多里,他经常咳血,并伴有低烧,但是医生一直把这些症状当做支气管扩张来治疗。10月的一天,吴敬琏陪他去反帝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看痰液培养的结果,化验单和X光片一出来,居然已是肺癌晚期。
因为顾准是戴帽老“右派”,医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顾的新四军老战友,也在经济所工作的骆耕漠得悉了这一消息,十分焦急,这时的他因为青光眼已接近双目失明,而且戴着“叛徒”的帽子,具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份,但他仍然挣扎着摸出家门,沿着墙角赶到医院,找到总部的党委书记杨纯——一个当年在他和顾准手下干过的“红小鬼”,好歹才让顾准搬进了病房。
顾准一开始对病情并不了解,一次,医生查房,用英文说出“癌症”一词,他才自知末日降临。
当时,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他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他还提到正在狱中的孙冶方,说,“我是见不到他了,但是我知道他的为人,他绝不会是汉奸。所以只要没被整死,他就会出来。出来的时候,你帮我向他致意”。
顾准还立下了遗嘱。他把自己的遗稿分为两部分,其中“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家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衣钵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