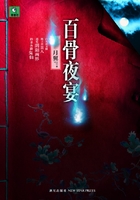白天明的脚在院长办公室的门前遗巡着。他仍旧在盘算见了林子午该说些什么。
他生平最怕见领导。他不知道在领导面前该怎么说话才算得体。每次上级召见,他都提心吊胆。单是领导对他的称谓,就够他思索半天。经验告诉他,倘或领导称他为:“白天明同志”这便意味着一场严肃的谈话,领导准会又向他指出他的一些应当去掉的毛病,或者应当注意加紧改造的问题。倘或称他为“白天明”,那就糟糕,说不定接下去便是一场批判,而他是敌还是友,也需待一段相当的时日才能判定。而倘或竟称他为“老白”,这便是说,领导已经认可他属于地地道道的人民一份子,而且也还有了一些成绩,让领导高兴。再倘或称他为“天明”,这便是他的幸福,足可以让他沉浸在苦涩的快乐里许多许多天。自然,这样惶惶不可终日的岁月已经去而不返,但积习却很难除掉,象是染上沥青的白布,虽经岁月流水的冲刷,也还是保留着旧痕。
这次,听说林子午院长要找他谈谈,他便心跳不已,老是预测着吉凶。他明知林子午不会再勒令他去扫厕所,却还是从头天晚上便不断设想院长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以及自己的最佳答案。现在,到了院长办公室门前,他又犹疑了,在走廊里来回踱步,自己鼓励自己的脚,要勇敢地停在门前,鼓励自己的手去敲响那扇装着毛玻璃的门。
他终于停在门前,深深地呼吸一下,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毫无反应。他又稍稍用力敲了敲门,依旧没有声音。他壮起胆子拧动把手推开门,伸进头去看了一下,见一位秃顶、头边有一圈稀疏白发的老人正坐在沙发上打瞌睡。这一定是林子午院长了,他的头垂在胸前,看不清他的脸,只有那油光铿亮的秃顶在晨光中闪耀,象一只巨大的眼睛盯着门口。白天明的心平静下来了,并且有点同情和可怜这老人了。精力已经如此不济,不如在家里颐养天年。硬撑着身体,在并不舒服的沙发上坐眠,无论如何不会使他解除疲乏。可怜的老人呐。
白天明悄悄走进来,坐在老人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细细地观察他。
林子午大约有七十多岁了,身体虽不臃肿,也称得上肥胖。他两只手交叉地叠在隆起的肚皮上,一道细细的唾沫丝仿佛上等的龙须面条一样,从嘴边垂下来,闪着光在微风里飘荡。
落地电扇在墙角无声地转着,送来一阵阵清凉的风。白天明怕这风对老人不利,轻轻走过去关上开关。这电扇一定是上等货,转动起来轻盈无声,可是开关启合的声音却响似惊雷。林子午恍然醒来,双手在嘴边一抹,擦掉了那根龙须面条,惺松的眼,无神地望着白天明。
“你,你是……”林子午问他。
“白天明。”
“噢噢,请坐请坐。唉,老了,坐下就管不住自己。”
“开着电扇睡觉,您会受风的。”
“你关上电扇了?也好。”林子午站起来,蹒跚地走向办公桌,又说:“你坐嘛,坐嘛。”
至此,他什么称呼也没使用,白天明所预想的一切都白费了。
“嗯,你走了之后,我才来。从新中医院调来,三结合的。”林子午坐在转椅上,叹口气:“什么结合,受罪罢了。你技术很好,是吧?”他拿起一张《光明日报》,“我还看报。这点事还能干。”
他的声音很洪亮,完全不象个老人。
他说:“是郑柏年推荐你,又是他为你到处跑,一定要让你回来。不容易呀,跑了好久好久哟,他没对你说过?他这个人是真正的好人。好医生,好朋友,好干部,好共产党员,不象有的人,只会说。哎,你坐呀。怎么样?打算干哪科?去内科吧,替下安适之同志,你当内科主任。”
“我,我当不了干部,真的。”白天明说。
“谁是当干部的材料?我也不是哟。没办法。”他好象陷入了沉思,胖胖的手拨着桌上的红蓝铅笔。停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地说:
“我已经老了。风烛残年。我这支蜡烛,给别人照亮儿是不行了,可还能当个火种儿,给别人点着他们的蜡。有的人自己的蜡,总也没点着,上我这儿借个火儿,我就让他们借,把那些个该点着的蜡都点着。这与我也没什么妨碍——这是我的比喻,你懂吗?''
白天明没有全懂,可他下意识地点点头。
“这就是发现人才,举荐贤能啊!”林子午说,“凡是自己或别人认为是有才能的,而且是忠诚老实的,需要借助我的力量发点儿火和热的,我都为他们说话,贡献给他们我这个蜡烛头儿。我只有这点儿力量了……”他又停住不说,呆呆地看着白天明。
白天明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头一回碰上领导跟他这么谈话。他觉得身上有点儿燥热,可又不好再去开电扇,只好掏出手绢擦擦脖子。
林子午却站起来,走到电扇旁边,打开了开关。电风扇摇着浅绿色的头,把舒适的风均匀地送给屋子里的人和家具,一视同仁。
林子午站在落地风扇旁边,轻轻说:“我看了关于你的报道……,,
“那里面有好多夸大其词的地方……”
“听我说。我想了很多很多。我也曾经是个医生,而且自忖业务能力还算得上中常……”
“您是国内外知名的胸外科专家。”
林子午一只手无力地摆了一下,象是赶开白天明这句称赞。他说:“别听那虚名儿。什么专家,只不过拿手术刀的年头儿长点儿罢了。可现在……”他仲出两手,指指整个房间,“扔下了手术刀,拿起了铅笔刀。你看,那笔筒里的铅笔都是我自己削的,怪整齐的,是吧?可有什么用哟,该你们了。该你们大显身手了。我呢,能把你这样的医生调到合适的岗位上,我就算有了点用处。这就是我为什么还坐在这屋子里的原因。”
林子午忽然停住不说,蹒跚着走向桌子,倒了一杯白开水递给白天明。然后,双手撑着桌子,把身体奏近白天明,轻声说:“你和安适之同志是老同学,你对他印象如何?”
白天明没想到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沉吟着:“这,我和他多年不见,说不好。”
“有什么说不好的。就说你的直觉吧!他有能力吗?”
“有,而且很有能力。”白天明说。
“他为人正直吗?公道吗?”
“这个……我,我觉得他好象比别人多一个心房。”白天明说。
“噢?”林子午笑了,“你提的是个生理结构问题,那得靠透视或解剖来断定了。不过,我懂你的意思了。”他又严肃起来,“他是个好医生吗?”
“从技术上说,他是。”
“那还有别的方面?从别的什么方面上说又不是。对吧?”
“林老,我实在说不清。”白天明说。
“哎呀!”林子午拍拍自己的秃顶,“我苦恼哟,你懂吗!我希望你这个同他没有任何私人利害关系的人,说出你对他的直觉,好给我一个判断的参考。”他咽咽唾沫,又说:“是啊,这难为你了。我会骂人,可不是不讲理的人。我常常放炮,有时候乱放,所以魏旭之说我是昏庸老朽。不不,你别替他辩护。我不讨厌他,相反,我喜欢他。可我并不糊涂。我可不会因为第一次见面,你说了别人什么而对你有看法,因为是我逼着你说的。”
“那,好吧。我对您说。几十年来,知识分子中一帆风顺,在各种运动中都没有大坎坷的人,可是不多。他就是其中之一。谁都以为他是个可以做领导的材料,可他却表现得单纯得象个孩子。您认为这样单纯的人,每次运动,每个历史时期都能逢凶化吉,扶摇直上吗?至少,安适之不是他留给别人的印象中的安适之。”
“嗯嗯,很有道理。”林子午说。
“所以,他不是有两颗心,便是比别人多一个心房。”白天明说,“哎呀,林老。我从来没有向生人说过这么多话,也没有在别人面前这样放肆地说别人。可见,您……”
“我也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见了你,我就想把自己的苦闷告诉你,咱俩见过面吗?”
“见过。”
“在哪儿?什么时候?”
“一九六二年,您在医科大讲课,我坐在教室最高最后的那一排。”
“唉,我老了。老是想不好我该怎么办?我应该让别人来借火儿,可又怕糟踏了我这不多的火光儿。不少人说他好,又有人说他不好。我的意见虽不重要,可表态也还有用。我不知道该怎么表态……”他忽然停住不说,坐到椅子上慢慢喝水。
呆了好久,他抬起头,眼睛好象散了神儿,有点儿生气似地说:“你先到外科,当两天医生,上上台,我得看你是不是真有点儿本事。好了,再见。”连手也不伸出来,就埋下头去接着喝他那一大杯白开水。
白天明有点慌神儿,不知道刚才的谈话是不是太超越了常轨,只好揪着心站起来,走向门口。
“听着,”林子午说,“你没有重复刚才谈话内容的义务。”
白天明心里也动了气,刚想回嘴说句什么,房门砰一声被推开了,袁亦方气冲冲走进来。
林子午一见,好象真动了气:“你怎么连门也不敲?”
“啊,架子还不小。”袁亦方说,“敲门就是投诉哇,我今天可是成心闯宫来了。”
“我看象是逼宫!”林子午说。
“怎么说都行。”袁亦方对白天明一挥手,“你出去。”
白天明只好出去。
袁亦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说:“给我倒杯茶。”
“我向来只喝白水。”
“所以你那么胖。该用清茶测测油,每日早晚各服绿茶三大杯,100O CC。这是我的处方。”
“我不信你那套。”
“你信谁的?良药苦口利于病,院长大人,你现在是偏听偏信!”
“是说安适之吧?老家伙,你是他前任岳父,你们有私仇,说好说坏,我都不听。我要听大家的。你知道吗,我想了个法子,也来个民意测验。”林子午站在袁亦方面前,双手捂着肚子得意地望着他。
袁亦方一愣,抬头看着他,“民意测验?怎么个搞法?”
“具体还没想好,反正我要听听全院职工的意见。”他压低声音,“我劝你上青岛去,别在这时候露面,省得人家说,坏话都是从你这儿发源。”
袁亦方霍地站起来:“啊,让我避嫌?!”
“可以这么说。”
“嗨嗨,我不去!不但不去,我还要四处奔走,游说,专说安适之的坏话。”
“哎哎哎,你可别这样儿。”林子午说,“这事儿可不那么简单。干部政策,比你那切脉、舌诊要复杂得多。”
“唬人。德才兼备的人就提拔,多简单。”
“安适之就德才兼备。”林子午说。
“你疯了?还是真的老糊涂了?”袁亦方问道。
“你听啊,第一,安适之忠于党的政策路线,凡有号召,无不雷厉风行,大力贯彻。”
“那十年他是有名的风派!”
“那是因为那时候党也犯了错误,政策往往朝令夕改。他作为执行者,又是个年轻人,难免跟着转来转去。第二,……”
“可是新华医院上上下下谁不对他有看法?”
“改革的闯将,难免会受到各方面的非议。”
袁亦方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林子午的胖脸。
“怎么样?你没说的了吧?”林子午得意地望着袁亦方,“简单?哼!我知道,你和魏旭之他们天天儿骂我昏庸。你不昏庸,你来试试看。”一指那把办公桌前的椅子,“这椅子那么好坐吗?”他忽然不说话,转身走了两步,背朝着袁亦方,不无悲凉地说,“你这个老家伙,昨天是我的生日,你竟然连门也不登,让我一个人对着一桌菜……”
袁亦方什么话也说不出,慢慢走到林子午身边,说:“真的让安适之当院长?”
林子午陡地转过身子大声嚷嚷:“没定,没定,还没定呢!你让我清静会儿好不好?”
袁亦方笑了:“瞧你,跟部下发什么脾气。今天晚上我和魏旭之请你,为你祝寿。”
“不要魏旭之,我受不了他那张嘴。”
“其实他可是真心疼你。”
“什么心疼,是心狠。恨不得我早死。”
“瞎说,他今天偷偷儿跟我说,安适之当院长还不如让你这老糊涂当几年更合适。”
“真的?”林子午睁大眼睛,“可他让老糊涂来领导,他不是更糊涂?要不是他比我岁数更大,我就请他来,也让他尝尝院长的滋味儿,我也当个顾问清闲清闲。”
“啊,顾问是闲差呀?当初你怎么哄我?说我有职有权……”
“你权还小吗?闯进来就骂我?”林子午坐在椅子上,一挥手,“好了,今晚上有鲜鱼吗?”
“还没去买呐。”袁亦方笑着说,“可是有鳝鱼。”
“那让我自己动手,你这个北方佬做不好。”林子午拍拍头顶:“唉,又忘了,今天查房。都是你,耽误了时间。”
袁亦方看看表,整九点。笑着说:“正合适。”
“跟我走。一起去,中西医结合嘛。”林子午站起来,从衣架上拿下白大褂,说,“真的,这医院不改革真的不行啊,我没有那能力,咱们需要年轻有为、懂医疗行政,又光明磊落的人呐。”
“郑柏年嘛!”
“你呀,真是不怕人说闲话,他是你的学生!”林子午说着,把白大褂朝身上一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