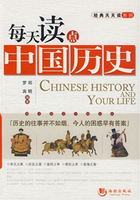去探访奉子成婚的新娘可不是什么好主意。一从郊区回来,倒霉事就轮番拜访了这几个曼哈顿姑娘。
从格林威治回来的第二天一大早,姑娘们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彼此的电话——凌晨四点,萨拉玩轮滑的时候崴了脚;米兰达和一个派对上刚认识的男人在壁橱里搞上了,而且没用安全套;凯莉干了件荒唐透顶的事,以至于她觉得她和比格先生要玩完了;还有,贝拉不见了。
大胆的家伙
米兰达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在派对上玩得这么疯——疯狂到简直是“格伦·克劳斯的翻版”——这是她的原话。
“我本来只是打算回家睡个好觉,然后星期日起来接着干活的。”——这就是单身并且没有小孩的潇洒之处。你甚至可以在星期日把工作搞定。
但是萨拉把她拉去了一个派对。“在那儿能认识很多有用的人。”萨拉说。为了她的公关公司,萨拉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猎取“有用的人”——当然,那些“有用的人”最后往往都转化成了“可以约会的人”。
派对在东六十四街一个很老的钻石王老五的别墅里。派对上,几个三十几岁的女人穿着黑色曳地长裙,头发的颜色一模一样——染成同一个色号的金色。这群黑裙女人小分队总是出现在各种有钱老男人的府上,在派对上物色男人,还故意装成像没那么回事一样。
萨拉在人群中一晃就不见了,剩下米兰达孤零零地站在吧台边上。她有一头深色卷发,紧身打底裤扎在靴子里,看起来很惹眼。
两个女孩从她的身边经过。可能酒精让她出现了幻觉——米兰达发誓其中的一个女人说了一句话:“这就是那个女的,米兰达·霍布斯,她绝对是个婊子。”
米兰达立刻大声回击,但根本没有人听见:“没错,我就是婊子——但我宁愿当婊子都不愿意当你,亲爱的!”这时候她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在郊区的这个漫长下午,铺满低脂奶酪的萝卜蛋糕,还有那个小巧的银质叉子——尖头锋利得好像随时都会刺破皮肤。
这时一个男人径直地走向她。他穿着剪裁考究的定制西装。哦,他还不算是真正的男人,因为他看上去还不到三十五岁——这个年纪比起派对里其他那些有权有势的老男人来说简直就是毛头小子,但是他在努力变得和他们一样。
当时米兰达正在让服务生给她来一杯双倍的伏特加汤力。他问她:“你渴了吗?”
“没。我现在只想吃牛排,可以吧?”
“那我就帮你弄一份。”男人用很重的法国口音说。
“我会让你搞清状况的!”她边说边要走开。她受够了格格不入的感觉,不想再和这个派对有任何牵扯了。但她却也不想回家,因为她也受够了孤身一人的寂寞——更何况她现在还有点儿醉了。
“我叫盖伊,”他说,“七十九街上有间画廊是我的。”
她叹了口气说:“嗯,是你的。”
“也许你听说过呢。”
“听着,盖伊……”她说。
“嗯?”他热切地问。
“你的那玩意儿能够到你的屁股吗?”
“当然能,”盖伊神情闪烁地笑着,靠近米兰达,抬手揽过她的肩。
“那你干吗不回家干你自己呢!”
“喂,拜托!”盖伊说,米兰达正纳闷儿他是脑子进水了还是法国人都是这个蠢样子,他已经不由分说地拽着她的手径直地走向楼梯。她跟着上了楼,因为她想一个男人被侮辱成这样后还能如此镇定,那么他应该不是个坏人。他们来到主人的卧室,床上罩着红色的真丝被单。盖伊嗑了些药,然后他们莫名其妙地开始接吻。
陆续有客人来用洗手间,进进出出,于是他们钻进了大衣柜。古旧的松木嵌板,衣架上挂着外套和裤子,羊绒线衣和鞋子放在搁板上。米兰达看了看标签:萨维尔街——真没劲。她转过身来,盖伊就在她的身后紧贴着她。他们在黑暗中爱抚,米兰达的打底裤被脱落到脚下。他疯狂而大胆地索要着她的身体。
“多大?”凯莉在电话里问她。
“巨大!还是法式的!”米兰达说。
结果完事之后,他说:“嘿,亲爱的,最好别让我的女朋友知道。”还没等她说什么,他就用舌头堵住了她的嘴。
于是真相浮出水面——盖伊早就和他的女朋友订婚了,已经同居了两年。他不确定他是不是想结婚,但他和她住在一起,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算是格伦·克劳斯也无计可施。
第二天,盖伊问到了米兰达的电话号码,打给她说还想见她。“那你必须作出选择了。”米兰达说。
担心的纽伯特
中午的时候,贝拉的丈夫纽伯特打给凯莉,问她有没有见到贝拉。
“要是她死了,我会知道的。”凯莉说。
溜旱冰的天真女
然后就是萨拉了。据米兰达说,她在凌晨四点醉醺醺地跑到楼下滑旱冰。一个已经三十八岁高龄的老女人居然还在扮少女,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倒胃口的吗?
可萨拉还能怎么样呢?她三十八岁,未婚,想找个人在一起。然而就像你从这本书里学会的那样,男人只喜欢年轻的姑娘。甚至新娘送礼会上的那些女人,虽然她们现在比萨拉老得多,但她们在三十八岁之前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而现在,可能结婚这个选项已经不再属于她了。于是她深更半夜和一个二十五岁的男孩一起滑旱冰,而不是和他上床。他倒是想要她,可她怕他嫌弃自己的身体。
下午,凯莉打给萨拉。“嗨!嗨嗨嗨!”萨拉接起电话。她正直直地躺在沙发上。萨拉的公寓位于西二街的一幢高层里,一室一厅,房间虽小但很精致。“哦,我很……好。很难以置信是吧?”她那故作轻松的语气听起来颇不自然。“不就是脚踝骨折嘛,急诊室的医生可是迷死人了。卢克也一直都陪着我呢。”
“卢克?”
“其实是卢卡斯。他最可爱了,我的小朋友。”她哧哧地笑着,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你从哪儿搞来的轮滑鞋啊?”
“哦,他滑着去的,去那个派对。是不是很可爱?”
这场闹剧在六个星期后终于结束了。在这期间,萨拉一瘸一拐地努力打理着她的公关公司。她没买意外保险,公司的经费也变得很吃紧。
和那些住在郊区的已婚贵妇们比起来,这到底是好是坏?
谁知道呢。
贝拉在卡莱尔
贝拉从卡莱尔打来电话,说起了迈阿密海豚队的一个什么外接手,也顺带着提到了她丈夫纽伯特,还有意大利面酱之类的事情。“我做了超好吃的意大利面酱,”她说,“我是一个贤妻吧。”凯莉附和着她。
贝拉从新娘送礼会回来后和纽伯特大吵了一架,气得离家出走,自己跑到了弗雷德里克夜店。那个外接手也在那儿。他一直和贝拉说她的老公不够爱她。“他是爱我的,你根本就不了解,”她解释着。“那我会比他更爱你,”他说。她只是笑了笑,离开了那里,自己在卡莱尔酒店订了一个豪华套间。她说:“他们会把鸡尾酒送到我的房间,就现在。”
她说她觉得纽伯特之所以心情不好,可能是因为他刚把他的小说寄出去,也可能是因为她说她不想要孩子——至少在他的小说卖出去之前不想要。等到她怀孕的时候,现在这种生活就得结束了。
所以为什么不趁现在好好地享受一把呢!
条条大路通酒吧
新娘送礼会之后,凯莉在电话里和比格先生报备了一下,就去了波威里酒吧。萨曼莎·琼斯正在那儿。她大约四十岁,是一个电影制片人,也是凯莉的闺蜜之一——有时候是。
巴克利,那个二十五岁的艺术家兼模特狂,不请自到地赖在萨曼莎那桌不走。
“你要是能来我的公寓里坐坐,我会很高兴的。”巴克利一边说一边捋了捋他的金发。
萨曼莎正在抽古巴雪茄。她弹了弹烟灰,直直地对着巴克利的脸吐了一大口烟雾。“你当然会很高兴,但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对你的那些破画感兴趣呢。”
“你当然不必对我的画感兴趣,”巴克利说,“你只要对我感兴趣就足够了。”
萨曼莎坏笑着说:“我从来不碰三十五岁以下的男人。经验太不足了,不合我的口味。”
“试试看吧。”巴克利说,“或者至少请我喝一杯。”
“我们要走了,”萨曼莎说,“我们得找个新聚点了。”
她们的新据点就是曼哈顿下城的洋娃娃酒吧。她们说不过巴克利,只好让他跟着来了。那个酒吧里的大多数人都半裸着身子,有个男人跟着或许可能会好一些,何况他还刚抽过大麻——他们刚刚在出租车里一起吸的。
到酒吧门口的时候,萨曼莎突然拽住凯莉的手臂(她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举动),说:“跟我说说比格先生吧。我想知道他是不是适合你。”
凯莉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告诉她。因为她总是这样,每次凯莉高高兴兴地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时,她都会跳出来横插一杠,质疑她的选择。想了一会儿,她还是老实地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令我疯狂。”
萨曼莎又问:“但他知道你有多好吗?就像我这样,知道你的所有优点?”
凯莉想:“有一天,我可能会和她一起跟同一个男人上床,但绝对不是今晚。”
这儿的调酒师是个女人。“在这儿看见一个女人可真不容易。”她边说边给他们倒了一杯免费的酒。酒精每次都是导火索。巴克利一直在喋喋不休地抱怨他多么想当一个导演,而且所有的艺术家最后都跑去当导演了什么的——那他干吗不赶紧行动,还当什么艺术家呢?
两个女孩正在舞台上跳舞。确切地说,是女人——大屁股,乳房又小又下垂。巴克利已经克制不住地开始狂吼了:“至少我比大卫·萨利强多了!我他妈的绝对是个天才!”
“哟,是吗?谁说的?”萨曼莎吼了回去。
“我们都他妈的是天才!”凯莉说,然后去了洗手间。
她穿过两个舞台中间的狭窄过道,然后下楼。洗手间的灰色木门关不上,地上的瓷砖也又脏又破。她想起格林威治、婚姻,还有小孩。
“我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些。”她暗暗地想。
她回到楼上,脱掉衣服,跳上高台开始跳舞。萨曼莎盯着她大笑,但最后酒保走过来委婉地让凯莉下去的时候,她看见萨曼莎在沉默。
第二天早上八点,比格先生打来电话。他正要去打高尔夫。“你昨天几点到家的?”他听起来很严肃,“都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她说,“去了波威里,然后又转场去了洋娃娃。”
“是吗?在那儿干什么特别的事了吗?”
“喝了很多、很多、很多酒。”她笑着说。
“没别的想告诉我?”
“没有啊,没什么特别的啊。”凯莉用小女孩的声音撒娇地说道,想要讨好他,“你呢?”
“早上有人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说看到你在洋娃娃里疯狂地跳舞,连内衣都没有穿。”
“哦,是吗?”她说,“他们怎么知道那是我?”
“他们知道。”
“你生气了?”
“你为什么不自己告诉我呢?”他问。
“你生气了吗?”
“我确实很生气,因为你不告诉我。要是你连诚实都做不到,我们要怎么维系感情?”
“但我怎么知道你值得信任?”她问。
“相信我好吗?”他说,“我就是那个你可以依靠的人。”
说完他就挂掉了电话。
凯莉找出他们一起去牙买加的照片。那时候的他们看起来那么快乐,每时每刻都沉浸在了解彼此的喜悦之中。她小心翼翼地拣出所有比格先生抽雪茄的单人照。她控制不住地想起在他怀里睡着的情景。她习惯从后面抱着他,身体紧紧地贴着他的后背。
她想把这些照片全都贴在一张大纸上,写上“比格先生和他的雪茄”。在顶端写上“我想念你”,下面画上很多、很多的亲吻。
她拿着那些照片看了很久、很久,但她最终什么也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