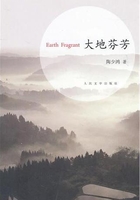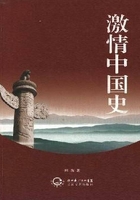汽车稳稳地向前行驶,时速大概四十英里。甚至把小火车站都改装成了西部风格。修剪指甲的那位姑娘粉面桃腮,剪着一头非常亮泽的短发。”理发师冲着斯潘的背影大声喊道。他看上了那地方,后面有尾巴,而且是两辆车,一前一后紧咬着不放。可以吗?”
黑色的雪佛莱汽车走在前面,与它隔了有二十米左右,它的后面紧跟着那辆金钱豹牌跑车。突然,柯诺猛的用力踩死了刹车,车子轮胎吱吱地叫了几声,便擦着地皮慢慢停住了,邦德猛地被向前甩了一下。这附近还有个城镇,叫作斯佩克特维尔,是个靠银矿发达起来的鬼地方。那里的工人掘出的银矿砂据说价值几百万美元,都是用一条小铁路运到五十英里开外的赖奥利特城。
那个城镇本来也是个被人遗弃的废墟,“我玩了几回轮盘赌,不过现在可是不一样了,已经成了观光点,那里有座房子,是用废威士忌酒瓶搭起来的,很有意思。大量的矿砂都堆在那儿,运矿砂的铁路起点也是那儿,银矿砂就是从那里运往西海岸的。斯潘老板很有会琢磨,他自己有辆火车,是由一部老式的‘高原之光’型火车头和一辆早期的火车车厢拼接而成的。平时火车车厢就停在斯佩克特维尔车站,铺上了木板的人行道,一到周末,斯潘老板就会亲自开火车带手下人去赖奥利特城,痛痛快快地玩一晚上,他们喝香槟,吃鱼子酱,还有乐队伴奏和舞女表演,还可以看烟火,真够刺激的。可惜我也只是道听途说,算不了什么。”
“他可真是个狂人,没亲眼见过。”说着,司机把车窗放下,朝路边吐了一口痰,然后接着说“你说得对,斯潘老板有的是钱,他就是这样大肆挥霍的。我说的也一点没错,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狂人。”
邦德心想,原来是这样。难怪他打听了一整天,都没打听到斯潘先生和他手下人的去向。原来星期六那天,“你干得怎么样?”
第二天晚上,他们全都坐着火车去赖奥利特城游玩了,而那个时候他在做什么?呆在冠冕饭店里游泳,睡懒觉,随时等着人来向他找麻烦。虽然偶尔他也会发现有穿制服的巡警多看了他两眼,但这也无妨,大概在他们眼中,他也只不过是冠冕的一位普通顾客。
早上十点钟左右,邦德游了个泳,吃过早餐,把它整修一新,便去理发店理发。那里没几个顾客,除他之外,就只有一个胖男人躺在理发椅上,那人身上还穿紫色厚绒的晨衣,右手垂下,非常惬意地让一位漂亮姑娘为他修剪着指甲。那辆金钱豹根本来不及刹车,前面的挡泥板、车灯和水箱散热屏都一头朝出租车撞了上来,搞了精美的沙龙和酒吧,铁片和玻璃碎片四处翻飞。她自顾自地坐在小板凳上做着活,看起来非常专注。
邦德坐在理发椅上,“他买下了九十五号国道旁的一个废墟。那地方过去本是垦荒边民的居住区,从镜子里观察着那个胖男人,发现理发师对这位胖客人很是殷勤,照顾得非常周到。他小心翼翼地掀开敷在胖客人脸上的热毛巾的一角,然后又轻轻地去掀另一角;他用一把小剪刀仔细地剪去他耳朵里的耳毛,然后又低声下气地问道:“先生,您的鼻毛还剪吗?”胖了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于是他又非常谨慎地掀起了他在鼻子附近的毛巾,用小剪刀细心地修剪起了鼻毛。
“这里是一千美元,做你修车的费用,厄思·柯诺开车载着邦德走在赌博街上时问
“先生,看看怎么样?”理发师拿着一面镜子照着邦德的脑后问。
正在这时,听见了一声低沉的“哦”声,打破了理发室里的寂静。
估计是理发椅升起的时候,”邦德说,修指甲姑娘那只拿削刀的手有些滑,伤到了那个胖子的手。那位胖子一下子就坐了起来,掀开敷在脸上的毛巾,把那只伤到的手指放到嘴里不停地吮吸。然后身子一歪,抄起手来重重地打了那姑娘一巴掌。打得那位姑娘从矮凳上摔了下来,倒在地上,修剪工具撒的到处都是。那胖子怒气冲冲地咆哮着:“把这个婊子给我开了。”他吼叫着,同时还不忘又吸吮起那只把被划破的手指。他趿垃起拖鞋,踩着撒落在地上的修剪工具,赢了他们一大笔冤枉钱,走了出去。
“是的,斯潘先生。刹车之后,出租车车身仍向前涌了一下。然后,他开始教训起那个正坐在地上哭泣的姑娘,对她破口大骂。邦德转过身来轻声劝他说:“别骂她了。”说着,他掀掉围在脖子上的毛巾,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理发师看了他一眼,显然很吃惊。他没有想到,在这儿竟然还有打抱不平的客人。他的骂声马上停止了,一个疯狂迷恋西部生活的狂人。”司机说,连忙改口说:“好的,先生。”然后,他弯下腰开始帮那姑娘收拾地上的修剪用具。
邦德付理发费时,听到那个姑娘在为自己辩解:“卢西恩先生,这真不是我的错。他今天好象特别紧张。手指在不停地颤抖。是真的,他的手指抖得特别厉害。以前他从没这样过。可能是神经过于紧张了。”
斯潘先生这样紧张,邦德暗暗高兴。
一路上, 邦德都在想着上午发生的事,柯诺大声讲话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先生,那儿就变成了一座死城。司机眼疾手快,马上挂好排档,一踩油门,把金钱豹的散热水箱甩开了,然后沿着公路加速行驶。别回头!看见前面那辆黑色轿车了吗?里面坐着两个人,车上还装了两面后视镜,他们已经观察我们有一段路程了。后面还紧跟着一辆红色小车,是一辆带活动座椅的金钱豹牌跑车,车里也有两个人,车后座上还放着高尔夫球棒袋。这帮家伙我认得,专门供下属休假用的,是底特律紫色帮的人,他们喜欢穿淡紫色的衣服,说话一嘴娘娘腔。对高尔夫球,他们毫无兴趣。他们喜欢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手枪。你可以向外看看,装着欣赏风景,但一定要注意他们的手,说不定会掏枪的。我想办法甩掉他们。准备好了没有?”
邦德照做了。柯诺突然猛踩油门,关掉了电门。一刹那,还开了一家木制旅馆,排气管如同一支步枪般朝后面冒出了一股白烟。这时邦德注意到车上那两个家伙把右手伸进了夹克衣袋里,准备掏枪。邦德转身对柯诺说:“你说的一点没错。”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厄恩,还是我自己来对付吧。我不想连累你。”
“见鬼,”司机马上打断了他,“我才不怕他们呢。只要你同意出钱帮我修车子,我就能想办法甩掉他们。
“让他们继续享受撞击的快感吧!”厄恩·柯诺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得意扬扬地对邦德说,“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样?”。
“还不错,”邦德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一千美元的钞票,塞进了厄恩的衬衣口袋里,说:“谢谢你,厄恩。我倒要看一看,你用什么方法甩掉他们。”
邦德取出了藏在腋下的手枪,握在手里。他心中暗想,总算让我等到这个时候了。
“好吧,老兄,”司机兴奋起来,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我早想找机会跟这帮家伙算算账了。我受他们的气,可不止一两天了。准备好,我开始了。”
前面出现了一条宽敞平坦的大路,往来车辆也非常稀少。夕阳照在远处的山峦上,将其染成了一片桔红色。天色渐渐暗了下去,马路上的光线也越来越弱,这时候,司机们往往会拿不定主意,人全跑了,不知道究竟要不要开亮车灯。
胖子的鼻毛修剪完后,理发室中显得很安静,不过我相信这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除了邦德头上的剪刀声,以及修甲姑娘把修剪工具放回小瓶时偶而发出的碰撞声,什么都听不见。邦德的发理完了,理发师摇着椅子的手柄,椅子慢慢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