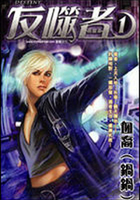“暂时还没什么动静,乘务员替我盯着他呢。车到终点,这个乘务员就是铁路公司里最富有的人了。为了戈德法布的证件,我给了他五百美元,这以后每天又加一百美元,直到旅途结束,到时候一起结帐。”克里姆笑了起来,“我还告诉他,这次他为土耳其出了不少力,将来还可以得到一枚奖章呢。他还以为我们在追查一帮走私犯。那些毒品贩子总是利用这趟车把土耳其的大烟运往巴黎。所以他一点都不奇怪,只是一下子得到这么多报酬,乐得合不拢嘴了。喂,从你那位俄国公主身上发现什么新情况?不过,说真的,我一直放心不下,总觉得现在太风平浪静了。也许塔吉妮娜说的是对的,那两个被我们弄下了车的家伙的确是到柏林去的。那个叫本兹的笨蛋一天到晚蹲在屋里不出来,大概是给我们弄怕了。现在真是一切顺利,可是……”克里姆摇摇头,“这些苏联人都是象棋高手,事情不会那么简单的,他们想实施一项阴谋前,肯定会精心策划,详细研究敌方情况,然后伺机反扑。我有一种预感,”克里姆的脸上愁云惨淡,“觉得我们三个人像是一个巨大棋盘上的小卒子。我们之所以现在还能够自由行动,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威胁到他们的计划。”
“但如果是阴谋,阴谋的最终目标是什么?”邦德看着窗外无边的黑暗,说着自己的看法,“他们究竟想得到什么?我们总是在这个话题上打转。当然,我们都嗅到了某种阴谋的气味,连塔吉妮娜也不知道自己已被卷了过去。我知道,她对我们肯定隐瞒了不少关键的事情,只是自己还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她保证,到了伦敦后就把一切全都告诉我。一切?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再三叫我相信她,说没什么可担心的。达科,我们得承认,”邦德抬起头来看着克里姆那冷峻、精明的眼睛,“她是守约的。”
克里姆眼里没有感情,他也没说什么。
邦德耸了耸肩,继续说:“我承认,我是爱上了她。但我不是个傻瓜,达科。我一直在留心观察,想发现点什么证据来证实我们的怀疑。你要知道,彼此之间的戒备一旦消除,往往可以看出许多问题来。现在我和她之间的栅栏正慢慢消除,我知道她讲的都是实话。至少,百分之九十是实话。我知道,至于没有讲出来的,她一定是觉得无关紧要。如果她在撒谎,那也是因为她自己也被蒙在鼓里了。按照你的棋路分析,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是那样的话又回到了先前的问题‘他们的目的’上面来了。”邦德的语气越来越坚定,“现在如果要弄它个水落石出,唯一的办法那就只有跟他们下完这盘棋。”
看着邦德脸上那副认真倔强的神情,克里姆不禁大笑。“老弟,换作是我,我就带上机器,在萨洛尼卡下车。当然还可以带着这位佳人。实际上带不带她并不怎么重要。下了车,再乘出租车到雅典,乘飞机回伦敦。只可惜我不是‘棋手’。”克里姆自嘲地说,“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棋赛,而是一项严肃的任务。当然对你们来讲就不同了。你是个赌徒,M局长也是一样。他更是一个大赌徒,否则就不会这样放手让你来冒险了。他也想知道谜底是什么。就这样造成了目前这种局面。但是,我宁愿求安稳,尽量不轻举妄动。顺其自然,也许你觉得现在不是一切正常吗?形势不是一片大好吗?事情绝不可能那么简单。
”克里姆转过身来,面对着邦德,他的语气变得坚定,“听着,老弟,”他拍了拍邦德的肩膀继续说道,“有些事情难以预料。就拿打台球作个比方吧!你明明看见自己的白球已直直地朝红球滚去,以为这下红球该滚入网中,一切按规律在进行。谁知道,这时一架失事的飞机朝着台球房冲下来;或者煤气管发生了意外爆炸;或者雷电突然击中了房子。总之,整个台球府垮了下来。白球肯定能击中红球,但红球就一定能滚进网中吗?白球能击中红球是按照台球桌上的规律来运动的。这仅仅只是诸多规律的一个规律!还要考虑其它的规律。在这个列车上也一样,主宰它运行的并不只有一个。而还有一些你没考虑进去。你看着,我们这次旅行也许会碰上同样的情况。”
克里姆停下了,他终于结束了他的宏篇大论。他耸耸肩膀,抱歉地说,“你都知道这些事情的,我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说了这么多,我也渴了。你去把塔吉妮娜叫来,咱们一起去吃饭吧。你可千万留着点神儿。” 他在他衣服中间划了个十字,“我不能在我心脏这里划十字,因为这里太重要了,但是我可以在我的肚子上划个十字,因为它是属于我的一个重要的誓言。我们这两种祈祷的方式看起来有点奇怪。那个吉卜赛头人曾让我们千万要当心,现在我又要重复这话了。我们尽可以打台球下象棋,但我们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指指自己的鼻子说:“它时时都在提醒着我。”
克里姆的肚子这时发出一声愤慨的叫声,就像一个在打电话的人在咒骂那个忘了接电话的人,“你们看,”他开玩笑地说道,“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们必须要吃饭!”
吃完晚饭时,列车已驶进了毫无特征的萨洛尼卡枢纽站。邦德还带着那个沉重的箱子。在他们分手时,克里姆提醒他们。“过一会儿,又会有人来找麻烦。一点钟左右过国境线。希腊人倒成不了麻烦,倒是那些南斯拉夫人老爱把熟睡的人吵醒。要是他们真要找你们麻烦,就赶紧来叫我。在这个国家我还认得几个管事儿的人。我在下一节车厢的第二个包厢,我一个人住。我想明天搬到我们的朋友戈德法布的12号包厢来。那时候,头等车厢就很稳定了。今天晚上就只好在那里凑合了。”
明月高照。列车费力地爬行在瓦尔达尔山谷里,向南斯拉夫驶去。邦德不失警觉地打着瞌睡,塔吉妮娜又枕着他的腿睡着了。他一直在琢磨着克里姆刚才讲的那番话,心想,等顺利到达贝尔格莱德后,是不是该让克里姆回伊斯坦布尔了?为了这次任务把他拖进来横跨欧洲冒风险实在不公平。这已出了他的领地范围了。再者,他已经怀疑他被塔吉妮娜的爱情冲昏了头脑,看不清自己所处的环境了。克里姆认为“当局者迷,局外者清”也不无道理。能离开列车通过其它途径回国的确要安全多了,但这果真是个阴谋,他承认自己是不能忍受临阵逃脱的耻辱,不能忍受好奇心的驱使。但退一步来说,如果并没什么阴谋的话,岂不是要白白浪费与塔吉妮娜呆在一起的三天时间吗?M局长也授权让他全权处理,克里姆说得很对,M局长也很好奇这场阴谋,他也想知道这整个阴谋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这样呆在车上不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吗?邦德不愿再想了。至今为止,旅途上一帆风顺,干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呢?
列车到达了希腊国境线上的伊多门尼车站后停了下来。十分钟后,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塔吉妮娜被惊醒了。邦德挪开她躺在自己腿上的头,站起身来,把耳朵贴在门边,问了声,“是谁?”
“先生,我是乘务员,不好了,你的朋友克里姆先生出事了!”
“等一等。”邦德大声喊道。他拿上了枪,套上了外衣,打开了门。
“怎么回事?”
乘务员的脸在走廊灯光下显得枯黄。“你随我来。”说着,他沿着过道跑向头等车厢。邦德嘱咐了塔吉妮娜一句,急忙跟了上去。
第二间包厢的门打开着。门口站了一大堆官员,呆滞地站在那儿看着包厢里面。
乘务员在为邦德拨开人群,分出一条路。邦德走上前去,挤到门边,朝门里望去。
他惊呆了!面前的惨相令人目不忍睹。右边的铺位上躺着两具尸体。尸体已经僵硬了。他们紧紧搂抱在一起。看来这里发生了一场只有电影里才有的生死搏斗。
克里姆被压在下面。他双膝弯曲,可能想挣扎着站起身来。一把匕首插在他脖子上,靠近颈动脉。他头向后仰着,眼珠无神地直盯着窗外的夜空,嘴巴扭曲着,脖子下淌着一滩血。
那个叫本兹的人半个身体压在克里姆身上。克里姆的左手卡在他的脖子上,邦德能看到他那斯大林式的胡子和一边黑色的脸。克里姆的右手挂在他的背上,手里握着刀柄,手下方的衣服上有大片的已经快凝固了的血迹。
邦德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景。就像在看电影,克里姆已熟睡了。那个家伙悄悄地打开了门,钻进包厢,向前跨了两大步,举起手中的刀,向克里姆的颈动脉刺去,而这个濒临死亡的人毫不迟疑地伸出手臂,用尽最后力气挣扎着拔出刀,一手卡住刺客的脖子,一手将匕首刺向他的第五肋。
这高大威武的克里姆向来吉星高照。但这次他却无声无息地走了。邦德再也听不到他的欢声笑语了,再也见不着他那幽默和玩皮的面孔了。
邦德难过地转过身来,黯然离开了这个为他而死的英雄。
现在他必须独自地认真考虑克里姆斯提出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