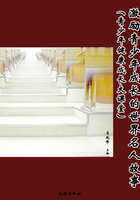打开门,里面是一间宽敞而豪华的会客厅,与纽约那些穷奢极侈的百万富翁们的私人办公室相比,一点儿都不逊色。屋里的各种物什的布局也显得十分协调,大约有二十英尺见方的面积,墙壁和天花板是浅灰色的,地板上则铺着绯红色的地毯,墙上挂着几组彩色板画,整个屋子无论怎么看,都显得富丽堂皇。一个暗绿色的吊灯从天花板上吊下来,使得整个屋子笼罩在典雅而温馨的灯光氛围中。
靠近屋子的右边,有一张桃花木做成的写字台,看起来很古朴,上面铺着绿色的台布,台布之上放了一部电话机和几件精美而别致的文具。房间的左侧摆了一张餐桌,餐桌的旁边是两把磨得发亮的椅子,看得出来,这里常常是贵客盈门。写字台和餐桌上各放了一只花瓶,里面插着刚刚采摘下来的鲜花,一副垂艳欲滴的样子。屋子中很凉爽,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在飘散,在弥漫。
房间里有两个女人。一位正坐在写字台旁边,手里握着一只钢笔,面前放着一张打印好的表格,似乎有什么内容等着要填。她看上去像个具有东方血统的姑娘,一头短短的黑发,整齐的刘海下面架着一副角质镜架的眼镜。她的嘴角有些微微的上翘,眉梢里流露出一种甜美的喜悦,看上去让人觉得既亲切又热情。
另外一个也是一个东方女人,不胖也不瘦,大约四十五岁左右。她过来替邦德他们打开了门。等邦德等人走到房屋中间时,她才轻轻地关上门。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热情而好客的家庭主妇,同样让人感到温暖和亲切。
两个人从头到脚穿着一身洁白素衣,皮肤光滑而细腻,脸色却很苍白,好像从未在阳光下晒过一样,像极了美国高级饭店里的招待员。
邦德向四周望了望,以期有什么发现。那个中年妇女则一直不厌其烦地在旁边唠叨个没完。听那语气,就好像邦德他们不是被俘虏的囚犯,而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赶上宴会的客人。
“你们这些可怜虫,现在才来。要知道,我们已经等你们很久了。先是听说你们昨天下午到,结果我们准备好了点心,后来又准备了晚饭,但都浪费了。半小时前,又听说你们要来这里吃早饭。你们是不是迷路了,所以才耽误了这么久?好在现在你们终于来了。要是没有其他事的话,你们去帮罗斯小姐把表填好。我马上就去给你们铺床,你们肯定累坏了。”
说完,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把他们领到写字台前,并挪了挪椅子,请他们坐下。“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我叫莉莉,站在旁边的这位是罗斯小姐,她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们。噢,对了,你们抽烟吗?”说着,她从桌子上拿过来了一个精制的盒子,打开后放在邦德面前。盒子里放置着三种不同牌子的香烟。她用手指指着香烟,挨个介绍:“这种是美国烟;这种是玩偶牌的;这种是土耳其制造。”接着,她打燃了一只精致的打火机。
邦德抬了抬手铐,从盒子里取出了一支土耳其香烟。
莉莉好像很吃惊地样子:“哎,他们怎么能这样!”感觉得出,她有点儿不好意思。“罗斯小姐,快把钥匙给我拿来,快!我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病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她的声音显得有些急促不安,“外面那帮人老是充耳不闻,简直是耳边风,非得好好说说他们才行。”
罗斯小姐遵照她的吩咐,拉开了抽屉,把放在里面的钥匙拿了出来,递给她。莉莉接过钥匙,挨个打开了戴在他们手上的手铐。接着她走到写字台旁边,抬手把手铐扔进了废纸箱,就像扔掉一块旧绷带一样,毫不可惜。
“谢谢!”邦德不明就里地说了一声,猜不透她们到底搞什么名堂。他重新把烟拿起来点燃了,然后转过头看了看海妮,发现她很恐慌,两只手正死死地抓着椅子的扶手,一点儿都不敢放松。邦德故作轻松地向她笑了一下。
“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该完成这个表格了。我会尽量快一点!”罗斯小姐摊开她那已经准备好了的长长的表格,严肃地说道,“请回答几个问题。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布顿斯,约翰·布顿斯。”
她快速地写着。一边写一边继续发问。
“通讯地址呢?”
“英国伦敦摄政公园动物学会。”
“职业?”
“鸟类学家。”
“噢,不好意思!”她微微一笑,脸上露出了一对圆圆的酒窝,“能把你名字的字母拼一下吗?”
邦德屏住气,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读出了他刚才报出的名字。
“谢谢。那您这次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鸟!”邦德沉静的回答,“我还是纽约奥杜本协会的代理人,他们有一块租地在这个岛上。”
看得出来,她写字的速度很快。但填完这栏时,不知为什么,她在后面划了一个问号。
“我说的这些全都是事实,我一句都没撒谎。”邦德见到后急忙解释道。
罗斯小姐突然抬起头,盯着海妮,并很有礼貌地向她点了点头。问道:“她是您的妻子?她对鸟类也很感兴趣吧?”
“你的猜测很对,确实是这样。”
“那她叫什么名字?”
“海妮!”
“这名字很好听。”罗斯小姐一边匆匆地写着,一边对她听到的一切做出评价,“还是和刚才一样的那几个问题,请您按顺序讲给我听。”
邦德按照她的要求,挨个儿回答了那些问题。罗斯小姐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一一填在表中,然后说,“好了,布顿斯先生!就这么多了,非常感谢您的配合,希望你们在这里过得很愉快。”
“谢谢你的祝福!很高兴能认识你。我想,我们会感到愉快的。”邦德站起身来,海妮也跟着站了起来。看起来,她的脸上比刚才平静柔和多了。
莉莉在一旁,见他们的表已填完,便说:“好吧,你们跟我来吧。”
她走到了屋子的另一扇门,停下来刚要开门,好像突然间想起了什么,于是回头问道;“噢,罗斯小姐,他们的房号是多少来着?我忘了,能告诉我吗?是那套乳白色的吗,亲爱的?”
“没错,就是那套,他们的房间号分别是14号和15号。”
“谢谢,亲爱的!走,咱们走吧。”她打开门,走了出去,然后又回头叮嘱道,“我在前面领路,这条路还不近呢。”
“这儿太不方便了,应该装部电梯。诺博士早就说过了,可他实在太忙了,你根本想象不到有多少事情每天都在排着队等他处理。” 她边走边说,并轻轻地笑了一下,“他可是个大忙人呀。”
“恩,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邦德很绅士地回答道。
跟在那个女人后面,邦德拉着海妮的手,沉着而冷静。前面是一条长长的小巷,长约一百码,一直向下面延伸,看样子,一直要通到山底下去。邦德估计这也许是一个地下建筑,工程的规模看起来很可观,诺博士一定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越往下走,邦德觉得问题越严重。从眼前所看到的情况来看,要想从这里逃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切反抗都将是徒劳,只能听天由命。尽管前面有个温文尔雅的女人给他们带路,但邦德明白,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运,她的话是不能违背的。显然这一切是事先已经安排好的,属计划之内。
小巷的尽头又出现了一道门。几个人停在门口,莉莉按了下门铃,门打开了。一位姑娘迎了出来,从外表看,又是一位带有东方血统的混血儿。她长得很漂亮,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仿佛永远也笑不完。
莉莉对她说道:“梅小姐,约翰·布顿斯夫妇就住在这儿。你把他们送到房间去,我看他们都累坏了,照看好点儿,他们吃完早饭后得好好睡一觉。”然后又转身对邦德说:“这位是梅小姐。有什么需要就按铃叫她,不要不好意思讲,她对病人从来都是尽心尽责。”
病人?邦德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他第一次从她嘴里听到这个字眼。
邦德没有继续往下想了,他有礼貌地对梅小姐点了点头:“您好,小姐,请问我们的房间在哪里?”
梅小姐虽然第一次跟他们打交道,但看起来很热情:“前面就是,跟我后面,我带你们去。相信你们肯定会对这里感到满意的。另外,你们的早餐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去吃吗?”
说着,她带着他们走向右边的一排房间。细长的走廊显得幽深而静谧。每个房间上都写着门牌号,他们一直走到了最里头的两个房间,看到房牌上分别写着14和15。梅小姐拿出钥匙,打开了14号房门,邦德他们随着她一块儿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布置得非常雅致的双人套间,四周的墙壁都涂成了淡绿色,包括起居室和洗澡间也是如此,光亮的地板上嵌着白条。房间被打扫的很干净,各种各样的设备应有尽有,并且都是现代化的,完全不亚于那些星级宾馆的上等客房。唯一不同的是,房门的里面没有安装插销,屋里面也没有窗户。
梅小姐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似乎在等待他们看有什么要求。
邦德向四周望了望,转过身面向海妮:“这儿看来很优美很舒适,亲爱的,你说是吗?”
海妮低着头,手在下面,把衣角卷来卷去。听到邦德的问话,她略微点了点头,避开了邦德直视过来的目光。
这时,从门外突然间传来了两下轻轻的敲门声,然后,便看见一个和梅小组装扮差不多的姑娘,手上端着一个很大的盘子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她把盘子放在餐桌上,揭开了盖在上面的白布罩,又摆好椅子,才转身走出屋去。原来她是送餐来的,咖啡和烤肉的香味立即弥漫了整个房间。
梅小姐和莉莉准备离去,两人走到门口时莉莉似乎突然想起还有什么需要补充,便回过头来强调道:“记着,若有什么吩咐,需要什么,请按铃,我们24小时都有人值守。开关就在床头,不要太客气。我再次希望你们能感到满意。对了,顺便提一下,衣橱里面有衣服,这些衣服都是昨天晚上专门为你们订做的。不过都是东方式的,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你们请便好了——但愿你们喜欢。诺博士吩咐过,一定要让你们非常满意。他让我转告,白天你们就在这儿休息,晚上如果你们赏脸的话,他想请你们共进晚餐。”她停顿了一下,看了看邦德和海妮,脸上露着神秘跟诡异的微笑,像是在给他们时间要他们好好考虑一下。感觉时间差不多了,她才开口问道:“你们看,我该如何回复诺博士?”
“请转告诺博士,谢谢他的盛情款待,我们非常愿意和他共进晚餐。”邦德说。
“真干脆!我想,他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说完,那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地退出了房间,并随手带上了房门。她们的动作很轻,给人一种极富教养的感觉。
邦德目送她们走出房门后,转过身来盯着海妮。海妮显得极为烦躁,低着头,仍旧不愿直视他的目光。她也许平生第一次走过这样富丽堂皇的房间,并莫名其妙地受到如此殷勤的款待,她有些受宠若惊。她对眼前置身的环境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怖,这种恐怖感要远远超过刚才在外面所受到的一切。她站在那里,脸上布满了泥土,有些不知所措,还有些无助,两手不自觉地用力拉扯着衣襟,一双泥脚来回地在地毯上擦来擦去。
看到此景,邦德忍不住大声笑了起来。瞧她那副倍受惊吓的神态还有那身破烂不堪的衣服,同这里的一切显得多么不着调,太富有讽刺效果了。实际上跟她相比,他也没好到哪儿去,同样是一身泥土。两个穷途末路的人,最终归宿却偏偏是如此优雅的场所,这里面不能不说有很浓厚的喜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