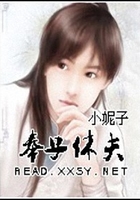“宫主,现在要如何做?”欧阳钰宜来到站在峭壁边缘,迎风而立的玲莜身边,看着身后放着的几个麻袋,不解的问着她。
“从这里把这些可爱的小家伙,给本座扔下去,同时传话给下面的人,叫他们守住每一个出口,逃出来的人千万别杀了他们,本座要他们都活着!”玲莜看着下面山寨的几丝炊烟,抓住一屡迎风飞舞的发丝,媚笑如丝的对身后的人吩咐道。
“是!宫主!”其他人一听到她的话,立刻便把身边蠕动的麻袋推到崖边,小心翼翼的解开麻袋口,用力推下去的瞬间又用剑把麻袋划了开来,瞬间便见空中飞舞着各种各样的蛇。
“你们看,那些掉下来的是什么?”负责山寨巡逻的一些山贼,那日之后,老大便吩咐他们加强戒备,以防有人来找事,可这都过了两天了,也没有什么动静,正无聊着,不经意抬头便看见上面像是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便唤着旁边的同伴一起看。
“啊!蛇,是蛇!”刚抬起头想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就听到有人喊了出来,顿时山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乱了方寸,惨叫声,喊声顿时响了起来,打破这一林的安静。
山贼们四散着躲避起来,有的也拿出剑斩杀着不断从天而降的毒蛇,奈何数量太多,这条被杀,那条又掉了下来,只好放下剑,抱着脑袋逃窜,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天降毒蛇?
“大,大,大哥,不,不不好了?”一个山贼跌跌撞撞的跑到寨子后面的一间屋子外,使劲拍着房门,语不成调的对着屋子里喊着。
“什么事把你吓成这样?像话吗?”不一会儿,房门便从里往外拉了开,开门之人赫然就是这山贼的头目,见面前一脸惨白的小弟,生气的踹了他一脚,对他吼道,原本就狰狞的面孔看起来更加的渗人。
“大,大哥,刚才突然从山崖上掉下来很多毒蛇,兄弟们已经不少被咬伤中毒,现在还有毒蛇不断的从上面掉下来!”那人被山贼头目一踹,倒也冷静了不少,但是想到外面那密密麻麻的东西,还是忍不住打起了颤。
“瞧你这熊样,不就是几条蛇吗?老子去瞧瞧是怎么回事!”那山贼头目说罢便拿着佩剑,往外面走去,来到前厅,看着广场上的情景时,也不禁惊骇,只见到处爬满了各色各样的蛇,他见过的没见过的,爬的到处都是,好多弟兄已经倒在地上,七窍流血而亡。
这林子里怎会有如此多的毒蛇?想到方才小弟说是从天而降,那头目不禁抬起头望向那一处峭壁,但见险峭无比的峭壁顶上站着四个人,三男一女,山贼头目边举剑劈开不断向自己攻击的毒蛇,边观察着他们的动静,这些毒蛇定与他们脱不了干系?
“所有人,点上火把!撤到林子里,小心埋伏!”山贼头子见毒蛇太多,而且每条都是剧毒无比,想必他们先前一直用血腥刺激这些蛇,现在这些蛇才具有这么强的攻击性,眼见又有不少弟兄被毒蛇所咬,想起蛇是冷血动物,怕热,忙对着已经一团乱的其他人喊道,声音里夹杂了一丝内力,见他们取来火把点上,又抬头望了一眼崖顶,那里已经没有了人影。
“是在找本座吗?”山贼头目正准备转身往外走,头顶突然传来一个极媚也极冷的女子声音,抬头一看,便见一个身着火红衣衫,面上戴着面纱的妙龄女子站在屋顶之上,这身影赫然就是先前站在崖顶之人。
“这位姑娘,本寨主与你素不相识,亦无怨无仇,为何毁我山寨?”山贼头子一边应付着不断往自己身边围靠的毒蛇,一边问着立在房顶的玲莜。
“无怨无仇吗?”玲莜听到他的话,声音又冷了一分,轻轻的飘下屋顶,往他的方向走去,边走边说道:“看来你是需要本座提醒提醒你,屠了本座的分堂,你以为不留下任何一点线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随着她莲步轻移,那些毒蛇不但不攻击她,反而往两边散开,给她让出一条道来。
“姑娘莫要含血喷人,本寨主何时曾屠你分堂?”山贼头目惊心与面前的一幕,为何这些毒物会避开她,听完她的话,有些不明所以,他何时有得罪过江湖中人?他一直谨记不去得罪江湖之人,这些年他打劫的也只是一些富庶人家或者过往商旅,要说屠杀?唯有日前那桩,想到这里,山贼头目暗惊,难道……
“怎么?想起来了?”玲莜一直观察着他的神情变化,虽然因他面上那道狰狞的伤疤看的不是很真切,但从他眼神的变化,便可知晓,他想起来了。他这幅样子倒还符合一个悍匪的形象。
“我们劫杀的不过是一般富户而已!姑娘一看便是江湖中人,为何要如此与本寨过不去,你到底是什么人?”山贼头目一边说着一边往寨外退去,看着步步紧逼却不出手的玲莜问道。
“哼!连所杀之人身份都未曾调查清楚,就敢大开杀戒,本座是该说你们太大胆还是太无知?还是仗着有那味毒药,别人奈何不了你们?”玲莜不再往前走,而是站定冷冷的看着他,见他不做声,又说道:“区区山莽草寇竟敢屠我殁鸢宫分堂一百余人,本座看你们是逍遥日子过太久,嫌命太长,想去地狱,本座不介意送你们一程。”语气里的冷意让人忍不住的想颤抖。
“不,怎么会?不可能,无凭无据,怎能肯定就是我们所为?”山贼头目一听到殁鸢宫的名字,心里便凉了个透,面前的女子自称本座,难道是殁鸢宫的宫主?看着她身上围绕着的冰冷气息,脊背上已经是冷汗淋淋,却仍然死鸭子嘴硬的质问着玲莜,心里也一遍一遍的重复着,她没有证据,她没有证据……